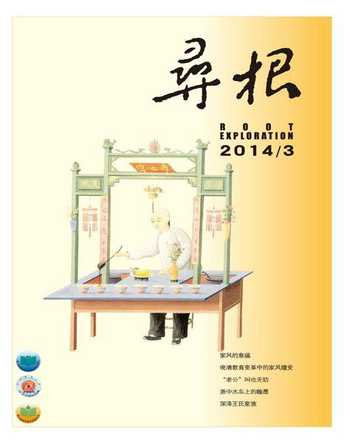深澤王氏家族
王博
河北深澤王氏先祖,于明初永樂年間(1403 -1424年)由山西洪洞縣遷居而來,其中一支輾轉搬遷到縣城西門內定居。明末,王氏的這一支逐漸興起,在清初發展成一方望族和遠近聞名的書香門第,直至民國初年。清代的王植著有《皇極經世書解》《四書參注》《權衡一書》《濂關三書》《道學淵源錄》等書,編撰縣志與州志多部,其著作在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均有收錄。清代的王肇謙,曾任福建漳州知府、延建邵道臺,多次帶兵參加剿匪,最終積勞成疾,以身殉國,皇帝詔贈光祿寺卿,百姓譽為“漳南一柱”。清道光年間(1821-1850年),深澤縣令楊挺曾稱贊王氏家族“人文代起,科第相望,尤邑中之翹楚也”;另一位深澤縣令吳步韓曾為王氏宗祠撰寫對聯:“治譜載棠陰,文苑儒林合傳少;宗風光梓里,鄉賢名宦一家多。”
清末,王氏家族開始創辦新學,鼓勵弟子接受新式教育。民國年間,軍閥混戰、社會動蕩,家族走向衰落和解體,多年累藏的古書典籍被迫寄存到國立北平圖書館(中國國家圖書館前身)。有志青年一部分負笈京津等地,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一大部分則于抗日戰爭爆發后,跟隨呂正操領導的部隊參加了革命,王氏家族也因此被呂正操譽為“抗日之家、革命之家”。新中國成立后,家族成員在不同崗位上為祖國的發展辛勤工作,較知名的有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著名地質古生物學家王鈺,西北工業大學教授王煥初,哈爾濱工業大學教授王鐸,著名中醫師王易門,原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吉林省原副省長王奐如,原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現北京對外經貿大學)副院長、黨委書記王曉樓等。
不同家譜的體例、內容雖然不盡相同,但一般來說世系圖表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是由于家譜是記載家族世系傳承和各代人物事跡等方面情況的歷史書籍,如果把世系傳承看作家族發展的主線,那么世系圖表就是家譜的“綱”。只有把世系理清了,整部家譜才能綱舉目張;只有把世系理清了,家譜也才能具備辨清昭穆、追本溯源、尊祖敬宗、增強宗族乃至民族凝聚力的基本功能。
基于上述原因,在重修或續修家譜時,都要把理清世系作為首要任務。在做這項工作時,如果有原來的老家譜作為依據,只需在原來世系圖表的基礎上作延伸和補充,這相對來說比較容易。但家譜曾作為“四舊”被大量銷毀,許多家族的老家譜由于種種原因而失傳。在沒有原始依據的情況下,知道曾祖父名字的人都很少,僅通過尋訪族人來理清世系,是十分困難的。因此,通過家譜外的其他資料來考證世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王氏家族以耕讀傳家,雖然家譜失傳,但留下了很多其他書籍和資料,據統計,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相關書籍即有27種。這些圖書、資料為王氏家族世系的考證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1.通過方志考證
咸豐《深澤縣志》中,與王氏世系直接相關的主要有兩部分:
一是“選舉志”部分。由于王氏家族科第興盛,自明末至清末,共考中進士2人、舉人17人、各類貢生13人,這些人物在“選舉志”中均有記載,更重要的是,書中對于這些人物之間的關系也加了標注。例如在“進士”欄中,前面已有關于王植的記載,此后關于王械的記載中,就標有“植弟”的字樣,說明王械是王植的弟弟;再如在“舉人”欄中,已有關于王餛的記載,此后關于王理培的記載中,就標有“餛子”的字樣,說明王理培是王焜的兒子。
二是“人物志”部分。在這部分中共有王氏家族12人的傳記,分布在“鄉賢”“仕進”等各節,一些人的傳記對有關的世系傳承交代得非常清楚。例如明代王琦的傳記中記載,“王琦……曾祖一正……祖任賢、父元勛”,一下就交代了王琦以上至其曾祖共四代的世系,而王一正也因此成為現有資料中能考證到的、從世系表中能連續不間斷往上推到的王氏最早的祖先;再如王礦的傳記中有“琦之季子也”的描述,說明他是王琦的第四子;王鐄的傳記中有“無子,以兄子宗洛為后”的記載,這是對封建社會習俗——“過繼”的記載,在世系傳承中也是比較常見的一種現象;王鵬的傳記中記載有“子肇恒、肇謙、肇晉、肇孚”,確切地說明了王鵬四個兒子的名字。
除縣志外,《清史稿》《清史列傳》《清儒學案》《清七百名人傳》《畿輔通志》《大清畿輔先哲傳》《定州志》等史志中也有一些王氏人物的傳記和介紹,對世系考證也有一定的幫助。
2.通過朱卷考證
清代科舉制度規定,參加會試、鄉試的考生用墨筆書寫試卷,叫墨卷,然后再由謄錄人員用朱筆謄寫,使閱卷者不能認識筆跡,稱為朱卷;還有一些新中式的舉人、進士將履歷、科份、試卷等內容刻印成冊,分送師友親朋,也稱為朱卷。朱卷中的履歷部分除本人姓名、字號、排行、出生年月、籍貫等基本信息外,還要寫清本族世系,最簡為三代,大部分是上至始祖下至子女,同族尊長、兄弟、侄輩以及母系、妻系無不載入,凡有科舉功名、官階、封典、著作的全部注明,可以說是除家譜外最為詳細的世系資料。
國家圖書館藏有深澤王氏王錫培參加乾隆庚子科順天鄉試的朱卷,世系上至其五世祖王琦;另有顧廷龍主編的《清代朱卷集成》(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收錄有深澤王氏王肇謙參加道光甲午科順天鄉試的朱卷,世系上至其九世祖王任賢,下至其子侄輩。這兩份朱卷所記載的家族世系資料,上起明萬歷年間,下至清道光年間,為研究深澤王氏家族世系情況提供了重要依據。
3.通過年譜考證
年譜是按年月記載某人生平事跡的著作。目前留傳下來的深澤王氏家族有關人物的年譜主要有三種:一是成書于乾隆年間的王植的《自紀》,收入其文集《崇德堂稿》中,是王植自撰的年譜,記事從其康熙二十四年出生到乾隆十六年辭官歸鄉;二是同治年間王用臣為其父王肇謙所撰的《先府君行略》,收入王氏家刻本《優詔褒忠錄》中,體例也是年譜,在簡要敘述了先世世系的基礎上,記載了從道光三年王肇謙入邑庠到咸豐七年殉國期間的事跡;三是光緒年間王用誥(號筱泉)的兒子王孝箴、王孝銘為其撰的《王筱泉先生年譜》,記事從其道光二十年出生到光緒十九年逝世。在這三部年譜中,涉及了大量的王氏人物關系,對研究世系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王筱泉先生年譜》,成書時間較晚,在晚清時期的資料相對較少的情況下,提供了非常珍貴的信息。
年譜除提供大量的世系信息外,還能夠較為精確地考證人物的生卒年月,除譜主本人外,與其相關的人物也大量涉及。如王植《自紀》中記載“(甲申)十二月,長男炯生”,記載了其長子王炯的出生年月;“庚子七月,祖廣文公卒……壽八十有四歲”,記載了其祖父的卒年和享壽,據此即可推斷出其生年。再如《王筱泉先生年譜》中記載“(光緒)十二年……孫丕祖生”,記載了其孫王丕祖的生年;“(光緒)二年……六月,從堂伯翰舉公卒,子仁壽年七歲”,記載了同族伯父的卒年及其子的生年。
4.通過聯姻家族的家譜等資料考證
封建社會通婚注重門當戶對,這樣既可使婚姻雙方在文化素質、價值觀念和思想認識等方面較為一致,使婚姻具有穩固的基礎;又可使家族之間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上優勢互補,形成越來越強的家族同盟。深澤王氏家族與周邊的一些大家族之間進行了廣泛的聯姻,比較重要的家族有行唐趙氏、正定何氏、無極李氏、晉州楊氏、博野蔣氏、武強賀氏、棗強步氏、饒陽常氏等,這些家族當時也都是當地望族,他們流傳下來的家譜、朱卷等相關資料,也為研究和驗證王氏家族世系關系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民國年間成書的《武強賀氏家譜》,記載了多處與深澤王氏聯姻的信息,例如在賀錫珩的簡介中就有“配王氏,深澤縣西門里附貢生、四川試用府經歷諱肇恒公女”的記載,說明深澤王肇恒有一女嫁于賀錫珩,同時還具體說明了王肇恒的功名、官職;成書于光緒年間的《博野蔣氏族譜》也很有特點,如對蔣士悅子女的記載中就有“女,長適深澤縣城內附貢生王名孝箴……四適深澤縣城內王名仁廙”,說明蔣士悅四個女兒有兩個都嫁到了王家。
武強賀葆真先生的《賀葆真日記》(又稱《收愚齋日記》),時間跨度從1890年到1930年,記載了很多賀氏當時與深澤王氏等家族的交往情況及有關信息,包括王氏家族的住宅、商號、田產、宗祠、家禮、藏書等,對于了解民國初期王氏家族的經濟文化狀況和社會關系也具有重要價值。
5.通過墓表考證
由于墓碑為石制,不易損壞,較之紙質載體更容易流傳下來。深澤王氏姻親無極東侯坊李氏在重修族譜時,其早期的世系信息就是依據一塊留存下來的墓碑而來的。但深澤王氏的幾處墓地在新中國成立后眾所周知的特殊時期早已被平,墓碑無存。只有一篇武強賀濤先生為王肇晉(字榕泉)撰寫的《王榕泉先生墓表》,是在賀氏文集中發現的。雖然只此一篇,但其中也有一些有價值的世系信息,尤其是王肇晉本人的生平信息。
6.通過輩分排字考證
根據族中老人的記憶,深澤王氏家族輩分為“肇用仁丕濟,世傳由先義,希和廣久昌,師爾乃敬備”20個字。但這20字是清道光年間才開始啟用的,到民國初年排到“濟”字輩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