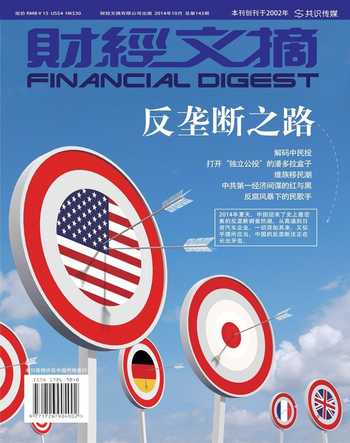戰地行:真相改變世界


“如果你無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
這是一群沒有槍的“士兵”,他們時常出沒在戰亂地區,用筆或者攝像頭記錄著戰爭中的一切,并潛移默化地改變著世人對戰爭的看法。
他們就是戰地記者,貫穿著整個近現代新聞史,也貫穿著200年以來的戰爭史,他們是戰爭中的局外人,但是卻真實地向世人傳遞著戰爭的殘酷,間接地也改變著國際局勢。
赴前線的“瘋子”
光頭、身穿橘黃色囚服,失蹤多日的美國記者詹姆斯·福利(James Foley)終于有了消息,只是了解他消息的來源是ISIS在網絡上公布的斬殺視頻。
在視頻中,福利一臉嚴肅地跪在沙漠中,他身后的ISIS極端分子手持利刃在中東的黃沙中將其斬首。
不到一個月,與福利一起失蹤美國記者史蒂芬·索特洛夫(Steven Sotloff),亦被ISIS斬首。
這就是中東,曾經是古文明的發源地,現在卻留給世人“中東即戰亂”的印象。怒火、殺戮、死亡無處不在,卻也是無數記者的冒險之地。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追逐烽火而來,努力按照內心的聲音傳遞戰亂地區的真實面貌。
福利如此,索特洛夫如此,千千萬萬不惜長眠于此的記者們更是如此。
為什么要追逐戰火?也許如眾多老記者承認的“大新聞帶來的往往比新聞本身更吸引他們”。
那么前仆后繼的報道戰爭以及在戰爭中喪命真的改變世界了嗎?據國際保護記者協會的不完全統計,福利是2014年第33位被殺的記者。在已知36名遇難者中,2/3遇害于中東的敘利亞、加沙地帶、利比亞、巴勒斯坦、黎巴嫩等戰亂區。2012年更是戰地記者遇害最多的年份,共有70名記者確認被殺,還有更多人失蹤。那么對世界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事實上,若非此次ISIS太過殘忍的斬首方式,國際輿論未必會有如此關注中東內戰。國際輿論也集中討論“兩位記者先后被害標志著敘利亞內戰以來暴力記錄再次驟然升級”的聲音。
最終,美國白宮正式宣布,美國與極端組織ISIS處于“戰爭狀態”,但不同于以往派兵干預當地事務,而是再次強調,美國不會派遣地面部隊參戰。
當然,記者在改變戰爭的同時,戰爭也在改變著記者。據傳播學者展江在《戰地記者——媒介時代的英雄》中介紹,1991年的海灣戰爭,因為導彈空襲敵方是這場戰爭的基本戰略,所以記者們不再隨軍行動,而是留在酒店觀察導彈攻擊和飛機轟炸,被稱為“飯店戰士”。
進入21世紀,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減少,國家對組織的戰爭增多,且這些恐怖組織來無影去無蹤,極大地改變著戰地記者的撰寫方式;且由于互聯技術的發展,只要有一部手機就可以隨時為各大刊物寫稿、攝影,成為戰地記者的門檻也極大地降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甘冒危險,前往戰地。
Twitter,Facebook更是成就了一批以自由撰稿為特點的戰地記者。
播下火種
連篇累牘的戰地新聞究竟給世界帶來了什么?也許因詹姆斯·福利、索特洛夫等眾多戰地記者的貢獻,對于烽煙之地的中東來說,戰亂區的公眾形象可能因此變得日益豐富和立體。
事實上,除了戰地記者所說的,“奔赴前線是為了要為歷史留下最真實的戰爭”之外,客觀上眾多的歷史也因此而被改變。正如根據真人真事改編的影片《阿拉伯的勞倫斯》中記者杰克遜·賓利(Jackson Bentley)(原型為美國旅行家兼記者洛維爾·托馬斯)所說的臺詞。
“為什么要采訪勞倫斯?”
“美國需要這樣一個充滿了傳奇和探險精神的英雄人物去激起美國人參戰。”
最終的結果也正是洛維爾·托馬斯所想要的——勞倫斯成為世界聞名的英雄,美國也放棄其“孤立主義”傳統,參加一戰。
事實上,翻開世界新聞史,因為報道改變國際局勢的事例舉不勝舉,而這些記者們的作品也將戰爭的“真相”得以保存。
真正回顧記者們的采訪過程,慢慢體會我們會發現其實他們作品主要想表達的就是:不同的世界、不同形式的革命都有共同的地方,即人性。
記者們前往戰地,也猶如永遠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行動本身就是制造機會的手段。也許他們并不能一夜之間改變戰爭,但他們的行動本身就已經播下了和平的種子——如果這一代看不到和平,那么下一代鼓勵下一代,總有一代會有機會看到和平。
正如加繆所說:“戰爭等同于瘟疫,每個人心里頭都有瘟疫,要與之抗爭。”而對于戰地記者來說,報道也許無法改變現實,但文章會變成一顆種子,把真相帶給讀者,其實已經做了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