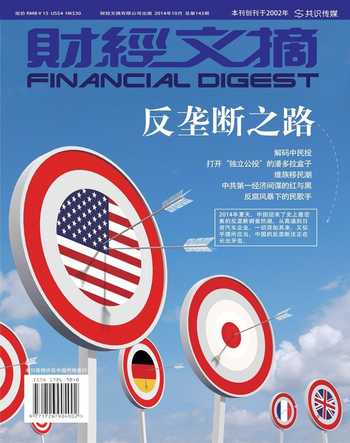跨境污染這筆賬
李俏云


喬安妮最近感覺不大好。
每次戶外活動時,總是感覺好像有一千把刀插入胸腔,尤其是身處喧囂繁忙的都市街頭,這種痛感更為強烈。
八年前,她順利誕下自己的第二個兒子,就在出院后的第四天,因為一次極其嚴重的心臟病發作又回到了醫院,因心臟不能正常供血,醫院決定為其植入一個起搏器。
如今,枯草熱癥狀以從未有過的頻次困擾著她。令她沒想到的是,罪魁禍首竟是空氣污染。
喬安妮的擔憂并非個例,研究表明,空氣中的細顆粒物能增大心臟出現問題的風險,同樣,還能加重已然患有心臟疾病的人的癥狀。
如果喬安妮居住在北京、新德里或是任何其他重度污染的城市,那另當別論。但她居住在英格蘭北部的謝菲爾德,那里曾經是工業革命的中心,現在則和歐洲很多其他工業中心一樣,變成了一個遠比以前更為安靜和清潔的地方。
空氣的跨境污染難辭其咎。
中國成全球公敵?
跨境污染已是老話題。相較于核爆炸、水污染、原油泄漏等事件爆發的偶然性,空氣的跨境污染更具殺傷力。
因為大氣圈是自然界最活躍的組成部分,同樣活躍的還有大氣中的細顆粒物。歐洲環境署數據顯示,至多95%的歐洲城市居民仍生活在細顆粒物濃度超過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導標準的環境里。細顆粒物是危害最大的污染類型之一。雖然距歐洲治理其壓城之霾已過去60年,但這仍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消息。
新興工業化地區的污染正日益成為一個國際問題,因為這種污染飄到了空氣更加潔凈的其他國家。作為新型工業化國家的代表,中國成為眾矢之的。
近兩年,北京的霧霾濃度飆升至令人震驚的水平,嚴重時其PM2.5的濃度達每立方米900微克,36倍于世界衛生組織的可接受水平(日均PM2.5濃度每立方米25微克)。根據中國國家環保部公布的有關74個城市的數據,在2013年,有71個城市的年均濃度超過了35微克/立方米的二級標準,11個城市甚至超過了100微克/立方米。全國平均有35.9個霧霾天,比2012年增加了一倍多。
與之相比,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倫敦的年均PM2.5濃度為每立方米空氣13.5微克,洛杉磯為14.8微克,多倫多則僅為7.1微克。
治霾刻不容緩,早已達成共識,但難度巨大也是共識。在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從農村向城市的人口遷移之后,現在全球70億人口中已有逾一半生活在城市地區,生活在人口1000萬以上的所謂超大型城市的人越來越多。聯合國(UN)預計,今后12年里,超大型城市數量將從23個增長至37個,其中絕大多數將位于亞洲。
城鎮化雖然不是導致空氣污染的直接原因,但隨著人口密集程度增高,細顆粒物濃度極易達到對人體健康構成威脅的程度。就中國而言,未來幾年預計將有2.5億人從農村遷移至城鎮地區。急速涌入城市的人口為治霾帶來不少麻煩,時刻在擴散的PM2.5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在國際上的聲譽。
來自鄰國的焦慮
雖然中國的污染物可飄洋過海,去往加州,去往波羅的海甚至更遠的地方,但最焦慮的莫過于緊鄰中國的日本和韓國。北京到首爾,坐飛機只需兩個小時,到東京,只需三個多小時。從酸雨、沙塵暴再到PM2.5、臭氧,韓國和日本這兩個位于中國大陸下風向的國度一直關注中國的空氣跨境污染,而自近年“灰霾”成為中國焦點以來,這種關切尤甚。
金谷有剛博士是日本環境省的專家會委員,多年來一直致力于PM2.5的研究,他最近的一項關于“越境大氣污染”的報告中指出:從最西邊的九州到中部的東京,日本的PM2.5中,中國的貢獻率分別是61%和39%。
但如果就此認為中國一旦遭遇重污染時,日韓等國就一定會受到影響,未免太過武斷。PM2.5的形成和傳輸過程相當復雜,空氣跨境污染當然取決于大氣的穩定程度和傳輸方向。“當大氣流動速度較快,就會導致比例很高。而當大氣相對靜穩時,當地的影響就尤為突出。所以我們認為東京主要受到當地的影響,而九州的影響主要是來自中國。”金谷說道,在東亞版圖上,九州島是日本距離中國最近的地區。
就貢獻率的數據而言,中日韓學者并未達成一致,卻對空氣質量的改善都持樂觀態度。
據金谷一直以來的計算,中國只需減少20%的排放,就可以提高日本PM2.5的達標率。如果中國的政策朝著減少健康風險的方向執行,跨境污染問題也就隨之消失。
相較霧霾、沙塵暴等跨境影響,更大的難題是臭氧。由于臭氧比PM2.5在大氣中的時間更長,其來源就更為遙遠。一篇論文曾指出,日本2000~2005年春季的臭氧來源中,22%來自日本國內,12%來自中國,6%來自朝鮮半島,7%來自歐洲和北美……因此,區域減排只能帶來很小的受益。針對空氣的跨境污染,切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全面,還需要全球范圍的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