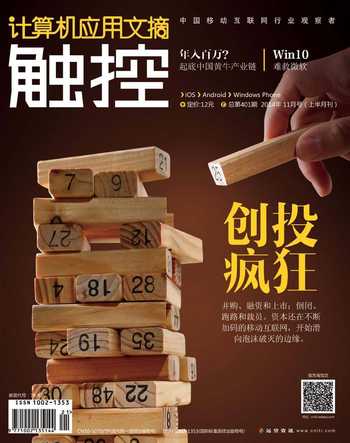手機粉絲們的瘋狂,年輕人孤獨的鏡像
流光逐云
對手機的依賴愈發強烈
一百多年前,勒龐在《烏合之眾》中這樣寫道,“要知道,歷來,在同理性對抗的過程中,感情從來不曾失敗過”。時至今日,我們似乎也很難反駁什么,人們所為之瘋狂的可能是某個人,某種理念,甚至是某款手機。
對于很多人來說,蘋果、小米這樣的手機品牌背后有著太多其他的東西,于是我們看到了無數果粉在門店前徹夜排隊,只為早一分鐘拿到一款新的iPhone;大批米粉在中午狂刷頁面,只為訂一臺不知道什么時候才會發貨的小米手機。一切是那么不正常,但卻又在情理之中。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手機正在像傳播學大師麥克盧漢預言的那樣,成為人的延伸,恐怕我們都很難做到將手機拋在一邊,更何況很多人甚至都會有些強迫癥似地刷一下手機上的社交網絡。手機成為了我們連接外部信息世界,連接虛擬與現實的人際關系網絡的關鍵節點,但這些顯然不是我們為之狂熱的原因。這只是一種依賴,卻不能帶來狂熱。
手機,不再只是那個手機
但隨著智能手機公司們越來越多的營銷,手機本身被賦予了更多的內涵,手機正在成為一種第三人格。當然,這一切的前提是智能手機給予了其在功能上實現更多差異化的可能,從而更容易形成一種俗稱作“逼格”的東西。
這一代在外界眼中看來十分獨立、個性的年輕人,其實從未拒絕過投入群體的懷抱,只不過他們更希望這種群體是虛擬的,是具有象征意義的。因為,某種意義上,獨立也意味著孤獨,意味著他們在無法靠自己的個性尋找到希望得到的存在感時,他們需要依賴群體為自己貼上各種標簽,找到存在感。
正如文章開頭提到的那本書中所講述的,群體往往容易陷入狂熱之中。
當新的手機發布時,他們也會迫不及待地去搶先購入,以讓自己能夠繼續留在這樣一個虛擬概念下的群體當中。即便有時這需要付出極高的溢價,比如過去一個月中,中關村那些動輒兩三萬元的iPhone 6。亦或許,他們只是在身邊人的議論聲中被裹挾著加入了這一行列,一切和《烏合之眾》中描述的場景何其相似。
當然,或許對一些人來說,隨著手機使用頻率和露出率的不斷攀升,它正在像手表、衣服和汽車一樣,被賦予了更多含義。正如十幾年前,有一部手機就已經象征了身份,而如今有一部什么樣的手機影響了別人對你的身份判定。我們身邊從不缺少將iPhone當功能機用的人,打電話、發短信對于他們來說就是手機的“全部功能”。但盡管如此,他們還是熱衷于iPhone,這個大家公認的最牛的手機。
Follow your heart
當然,我并沒有說這樣的狂熱有問題,至少它帶來的是一個行業的繁榮。十年前,一部諾基亞手機可能用上三四年,但現在因為硬件本身迭代的速度和外在的那些因素,這個周期已經被大大縮減。而這一切在鮑德里亞看來,則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這位勒龐的同胞,《消費社會》的作者則曾在書中這樣說過,“人們從來不消費物的本身—人們總是把物用來當作能夠突出你的符號,或讓你加入視為理想的團體,或參考一個地位更高的團體來擺脫本團體。”我相信這樣的總結,或許可以回答上面的那些疑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