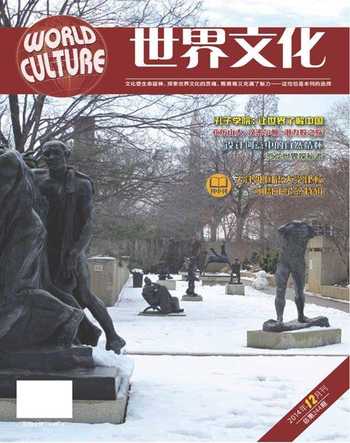游疏芬山金礦遐想
馬洪文
一處活生生的金礦遺存
我們從黃金海岸飛往墨爾本,參觀疏芬山金礦遺址。
這座古老的礦山坐落在墨爾本西北112公里處的巴拉瑞特小鎮。19世紀50年代在布寧永和貧窮角發現了金礦,小鎮沸騰了,不久便涌進4萬余名淘金客。從遙遠的中國,一萬多名農民揣著黃金夢,也不遠萬里來此地闖蕩江湖。美國西部不是有個“舊金山”嘛,疏芬山便成了鼎鼎大名的“新金山”。
走進小鎮,讓人大吃一驚。鎮上的酒館、飯店、銀行、警察局……依然保存著19世紀的風貌。紳士派頭的礦主頤指氣使,挺著大肚子的警察照常巡邏,衣衫襤褸的礦工隨處可見。我們徜徉在坑洼不平的馬路上,正對著兩旁的花花綠綠驚奇不已時,卻被身后粗魯的吆喝聲嚇了一跳,轉過身來才發現,一輛套著兩匹騾子的馬車拉著盛水的大木箱嘰里咕嚕地朝我們輾來。也許是一場惡作劇吧,因為沒有哪位游客在這里遭遇交通事故。
面包房里的面包是用一百五十年以前的秘方烤制的。郵局里使用著兩個世紀以前式樣的明信片,商店里的買賣人用鵝毛管蘸水筆開收據,發票上寫的日期是19世紀某年某日。仔細觀察,你會發現,街上還貼著當年英國政府給殖民地發布的電文;在街角的一家小店里仍掛著當年墨爾本的交通時刻表。
鐵匠爐冒著通紅的火苗;錫器作坊鑄造古老的托盤、燭臺;報館用笨重的印刷機印著外來人的求職廣告;一部大塊頭的照相機旁堆滿了人,他們想留下自己150年前的靚照。
在疏芬山,除了中國游客便是源源不斷的澳大利亞中小學生了。他們來到礦上,親眼目睹19世紀的人們怎樣生活,黃金是被如何開采出來的,通過生動、形象的觀察實踐活動,認識社會,了解歷史,心靈會受到重重敲擊,綜合素質也無疑會得到全面提升。
一幅沉甸甸的辛酸畫圖
輪到我們團下礦了。人們爬上了排滿木頭椅子的軌道車。鈴鐺響了,車飛快地朝著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洞向斜下方滑去。速度在急劇地加快,緊張的驢友們哪兒還敢喘口大氣。我也在想,萬一有一個輪子跑偏……心都嘭嘭作響。漫長的3分鐘過去了,終于望見了昏暗的燈光。
礦坑中蛛網似的小道縱橫交錯,寬不過1.5米,高不過1.85米,可喜的是主巷道都亮著微弱的燈光。人們默默地跟著導游魚貫而行。沒有出聲的,沒有掉隊的,耳邊聽到的只是噼里噗嚕的腳步聲。我們參觀了蝸牛殼般的礦工歇息地,鎬刨锨掘的采金工作面,在一處玻璃墻幕后面,還看到了一塊又一塊碗口大的狗頭金。導游說,礦里的原始蒸汽機還在24小時工作。它每天要吃掉兩噸煤,才保障了游客腳下的坑道不被地下水淹沒。
人們來到一處稍稍寬敞的坑道邊,突然燈滅了,傳來哀婉的樂曲聲,不一會兒,巖壁上出現了影像,一個講述當年淘金人悲慘命運的短片上映了:在中國廣東,一個叫強仔的年輕人,由于天災人禍,一家人赤貧如洗,為了給孩子找一條生路,爹娘忍著淚水把阿強交給了去澳洲淘金的表叔。登上輪船之后,大浪的顛簸,不如豬狗的底艙生活環境,加上一個多月的漂泊,使得許多饑餓的勞工還沒登上大洋洲的海岸,就命喪黃泉了。勉強到達了“新金山”的漢子們很快發現,金礦不是理想中的天堂,這里充滿了壓榨、哄騙、勒索與暴力。他們只能當牛做馬,任人宰割。于是有人逆來順受,有人自甘墮落,有人頑強抗爭。強仔飽受凌辱卻活了下來,但他的表叔和許多老鄉都客死在這片異國的土地上……
礦坑里的燈亮了,人們相對無語,久久地沉默著。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在赴南半球大洋洲的旅途中,竟接受了一場觸目驚心的憶苦思甜教育。從疏芬山中國礦工的悲慘命運,我馬上聯想到當年流落到太平洋彼岸上百萬中國同胞
的命運,因為我曾聽說,美國西部鐵路,每一根鐵軌之下都埋著中國工人的白骨。我還想到數百年前“下南洋”的中國人,不管是馬來西亞半島上摸爬滾打的采錫人,還是印尼熱帶雨林中的割膠工,他們都過著倍受煎熬的日子啊!我更不能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應招去西歐的數十萬中國華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裹挾去日本的難以計數的中國“苦力”……
應該說,這些在國外艱辛勞作的中國人,他們為創建現代文明、繁榮世界經濟曾付出了慘痛代價,更做出了巨大貢獻。期望有才有識的史學家、藝術家能寫出全面反映華工生活的歷史書、歷史劇,因為他們理應彪炳于青史之上,受到祖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敬仰。
一瓶光燦燦的紀念金屑
回到地面,我們奔向淘金池。這里是一片潺潺溪水流過的沙灘。人們拿一個銅盆,只要貓下腰就能舀上半盆泥沙來,經過一遍又一遍的篩洗,泥沙淘盡了,金粒自然顯露出來。
“誰淘的金子誰帶走。”多么誘人的鼓動!上千名游客麇集在池邊,為了一粒粒“從天而降”的寶貝而忙碌著。聽熟悉情況的人“透露”,這塊已經淘了近200年的池塘,哪里還會有什么金沙,只是為了制造轟動效應,在每天清晨,都有工作人員灑上幾粒金屑,這便是淘金池邊不斷傳來震天歡呼的奧秘。
我到售貨亭花了9澳元買了一小瓶紀念金屑。那個小瓶直徑約10毫米,高30毫米。瓶中注滿了甘油,能保證金屑在較長時間內熠熠生輝。小瓶被固定在一張印有澳大利亞地圖的硬紙板側面,圖上還用醒目的符號,標出了疏芬山的地理位置。
說起黃金來,它是一種延展性極強的金屬。明朝的《天工開物》記載:“凡金性又柔,可曲折如柳枝”(見該書“五金第十四”),用“七分金”打造金箔,便“可蓋縱橫三尺” 。把以上的現象,用現代語言表述,就是“一粒綠豆大的金粒(重1克),可以輾成0.6平方米的金箔”。若把它切成50平方毫米的小片,能出1200塊。將這些小片金箔搓捏成屑狀,每瓶裝10片,能裝120瓶之多。
我國的黃金加工技術有著悠久的歷史。遠在夏朝,文獻中就出現了“金”字。殷商時期,我們祖先已經制造出了包金青銅貝;戰國時代的楚國,還鑄出了市場上流通的金幣——郢爰。當今,南京市生產的金箔享譽世界。不論是白宮、克里姆林宮,還是凡爾賽宮、白金漢宮,穹頂上統統貼的是中國金箔。說不定疏芬山賣的紀念品,還是從中國躉來的賺錢手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