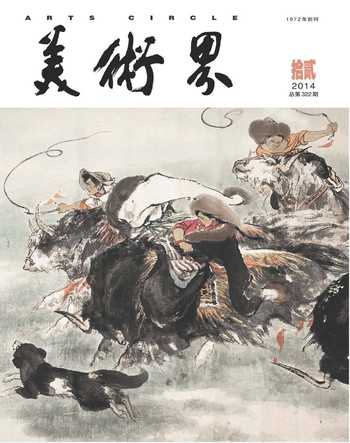畫事隨想



高旭,1977年生,寧夏固原人,2001年畢業于寧夏大學美術系,2010年畢業于西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并獲美術學碩士學位。現任教于寧夏師范學院美術系,講師。寧夏美術家協會會員,寧夏固原市美術家協會會員,作品多次參加全國及區內外各種畫展并獲獎。
作為美術教師,除了教學,就是畫畫了。
我天生嗜好畫畫,加之性情沉靜,又喜好閱詩詞、歌賦,好古董文玩。教學之余,喜獨處于畫室舞文弄墨,樂此不疲地糊涂亂摸,感受筆墨帶給自己的激動和亢奮。
回望教書數十載,業績平平,繪事成就平淡無奇,想來黯然傷神,但欣慰的是繪畫方面也還摸索出了一些門道,繪畫的審美意識也有些增強。近些年,隨著教學的不斷深入,我在繪畫技巧和素養學識方面不斷強化自己,為的是不誤人子弟,教學閑暇之余,專攻國畫之花鳥畫及山水畫技法,潛心研繪,如饑似渴,勞而不覺疲憊,反而覺得是身心俱爽,這是因為心中一直有強烈表現情感的欲望和表達生活理念的渴求,加上我遇事坦然,不急不躁,在經濟利益日益膨脹和意識形態開放激進的今天,慶幸的是自己還能保持一顆單純而不慕名利的心,把意念和精力專一在自己的事業上,竭力做到夢寐以求的人品畫品共榮。
我認為繪畫創作并非易事,一要有學養;二要有天性;三要有毅力。要想成全自己達到以上三者,就需全力而為之。余雖刻苦習畫,小有進益,然常感心性不敏,所以未敢有絲毫懈怠。人常說書畫乃學養、人品之表露,兩者不可偏廢。畫畫的人,要甘于寂寞,不逐浮名物欲,孜孜寄情于書畫之間,或可有成。所以把“寧靜淡泊”作為自己的座右銘,盡量做到心無雜念,筆耕不輟。想著自己還年富力強,繪學之事不能放棄,更應珍惜光陰,銳意進取。
說到我的繪畫,雖花鳥畫、人物畫均有所涉獵,但山水畫可圈可點,較集中的把自己的一些特點表現出來了,這是我近年長期寫生,師法造化的結果。
從我的畫面中不難看出,寫生是我山水畫創作的主要表現方式,因為我的老家在寧夏南部山區,這里干旱貧瘠,既沒有北國那種氣勢雄渾、群峰巍峨的大千氣象,也沒有那種漁舟唱晚、煙雨變幻的江南情調。我竭力想把生我養我的這片熱土那種蒼茫、厚重的地域風光表現出來,這得益于這些年對傳統山水畫的深入研習,感恩傳統學養滋潤我心,相對來講,反觀自己畫作,那種微微帶點苦澀,蒼涼凝重的氣息在自己的畫面有了反映,但抒情之意還是略顯不足。我時常告誡自己,要想表達自己的“心象”,就需不斷地“師古人、師造化”,就必須進入“忘我”“忘法”的境界,使自己的藝術見解和藝術法則盡快與自己的人格融為一體,使它注入到自己的靈魂當中去,使自己的精神意念完全服務于藝術表現,達到筆到意到的“無我”境界。寧夏西海固地區,雖然荒涼貧瘠,但我對其有著深深的摯愛,有了愛就有了表現的欲望,那種蒼涼凄美山巒溝壑成為我樂此不疲的表現對象,它呈現的春之百花、夏之雨水、秋之碩果以及冬之雪景的四季轉換景象,給我帶來了無盡的遐想,這種自然之美又是需要心靈去發現、去感應的。可以想見,山水畫家的繪畫行為是一種精神與性情的游歷活動,需要用心靈去感受大自然給我們提供的創作素材,來開啟我們的創作靈感。
總的說來,當今山水畫無論是在表現形式、繪畫技法、意境營造或是審美情趣方面都呈現出與時俱進的風格特點,為順應現當代的審美習慣和精神價值追求,山水畫家竭盡所能的從內容、風格到表現形式和技法語言等方面不斷豐富、充實自己,試圖創造出有別于博大精深的傳統繪畫新樣式,這種創造意識是無可厚非的,相對來講,要走出傳統山水畫的羈絆,就要提倡“寫生”,就是既要“師古人”,又要“師造化”,這是學習山水畫的最基本的方法,這種方法一方面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畫的思維方式、觀察方式和表現方式,感受大自然,在大自然中發現、尋找創作的內容和靈感,探索繪畫形式和繪畫語言的表現力,尋找內容和形式的最佳結合點。另一方面,通過寫生可以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把握,了解和研究山川、林木的結構和山水畫所有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
藝術的誕生過程其實是發現生活和表現生活的過程,這是考驗畫家生活經驗和生活積累關鍵要素,一個畫家除了技術之外另一個很重要的素養就是對生活有著特殊的洞察力。中國畫講究涵養,其實生活經驗和積累是個人涵養的主要組成部分。現實生活不等于藝術生活,純自然的東西需要加工提煉轉換成藝術語言之后才能儲存,這才是真正的積累。這個過程我常常把它當作釀酒,糧食是經過發酵之后才能變成酒的。畫畫就是把生活原型經過概括提煉變成形式語言之后才能成為藝術品。
每當我在作畫時,面對著一張白紙,想要畫出些什么的時候,我覺得我找到了一種和自然溝通的途徑。春夏秋冬,寒來暑往,自然世界中充滿了詩與畫,這是大自然賦予我們的。“春有百花夏有月,秋有涼風冬有雪”,有了對大自然的情感,才會有感而發產生出創作的激情,這是進行藝術創作的先決條件。大自然賦予了人無限的想象空間,也使人具有了進行藝術創作的動力,如何使人們的主觀感受和客觀世界合而為一,達到和諧,從而創作出更好、更美的藝術作品,古人的“遷想妙得”大概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在繪畫藝術表現上,本人在熟悉傳統繪畫的基礎上做一些哪怕是很小的創新,都使得我欣喜若狂。其實“創新”并不玄妙,它是悟性、靈感與覺悟的一個集合體,它與實踐能夠構成因果關系,覺悟源于實踐,徹悟基于漸悟。每一個畫家都希望有自己的繪畫藝術個性,然而在繪畫藝術上自我個性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既需要“造化”的哺育,同時也要有傳統優秀文化的熏陶,二者不能偏廢,只有這樣才會使畫家的繪畫個性具有普遍意義上的文化品位,其作品也就更加具有藝術魅力,這是一個長時間磨練的過程,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