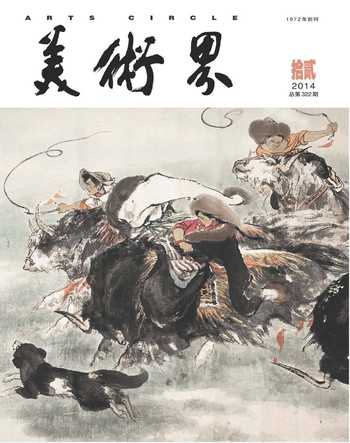武山拉梢寺石窟北朝摩崖造像藝術初探
【摘 要】武山拉梢寺石窟是天水地區規模僅次于麥積山石窟的一處始鑿于北朝的古代佛教石窟,主佛造像是世界第一大的摩崖浮塑造像。本文從拉稍寺石窟造像的藝術特色與匠作技藝等角度入手,結合實地考察調研結果對其進行了初步的整理及論述。
【關鍵詞】拉梢寺;摩崖浮塑;匠作技藝;造像
拉梢寺石窟是天水地區規模僅次于麥積山石窟的古代石窟藝術范本,雖然發現和研究的時間較晚,但因其特殊的佛教造像形態和歷史文化價值以及所具有的藝術價值,同時作為天水北朝石窟造像群落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些年愈來愈受到學界的關注。
拉梢寺石窟位于武山縣城東北約25公里的響河溝峽谷中,其主體部分開鑿于蓮苞峰南壁的一處弧形崖面上,造像以摩崖石胎浮塑大佛為中心,高寬分布皆約60米。現存大小窟龕24個,各類造像33尊,壁畫365平方米,融小佛龕、塑像、浮塑、懸塑和壁畫于一體。拉梢寺石窟的造像主要為摩崖浮塑與懸塑造像,以北周的1號龕造像為主體,另有宋代2、6、7 號造像和12號十身佛等。
據拉梢寺石窟大佛的摩崖題記所載,該寺始建于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元年(公元559年),現存部分亦多為北周遺存,在其后的隋、五代、宋、元、明等朝又歷經數次續建與重修,留下了各代造像及壁畫,反映了佛教藝術在西北地區的發展、演進與興衰。拉梢寺石窟既是研究佛教藝術發展的資料性文本,同時又對考察北周時期佛教雕塑藝術特點以及佛教美術的民族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一、拉梢寺石窟北朝摩崖造像的藝術特色
(一)拉梢寺摩崖造像的首要特色便是規模巨大,其大佛造像是亞洲乃至世界第一大的摩崖浮塑造像,因此拉梢寺亦稱作大佛崖。在約3600平方米的崖面上,浮塑了一佛二菩薩像,佛像通高34.75米,佛座高約17米,兩旁的脅侍菩薩通高也有27米。巨大的彩繪石胎泥塑與滿涂窟面的說法圖、千佛、飛天等壁畫構成了一幅宏大的佛國場景,為彰顯佛的尊貴與崇高,充分利用周邊的自然條件創作大型摩崖浮塑造像,使其觀之頂天立地,氣勢非凡,在中國石窟造像中,占據了摩崖造像最高和最大的記錄。
拉梢寺大佛這種體形高大雄偉、表情端莊肅穆、和平而威嚴的造像,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既昭示著佛的偉大,同時又象征著帝王的尊嚴與權威,這也是自佛教東漸以來何以受到各朝統治階級大力推崇的原因之所在。正如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親命的宗教領袖法果所說:“太祖明睿好道,即是當今如來,沙門宜應盡禮,遂常致拜。”又:“能鴻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禮佛耳。” 皇帝既是現實世界中世俗的主宰者,同時又是佛國中的精神領袖,這種佛如帝身的宣揚使佛教獲得生存發展空間的同時又成為國家鞏固政權的工具。在該寺贊助者尉遲迥的題記碑文中就有“愿天下和平,四海安樂,眾生與天地久長,周祚與日月俱永”的祈愿,顯示出開鑿拉梢寺建造大佛具有安撫民心,進而鞏固統治的政治功能。
(二)拉稍寺石窟造像具有北周造像的典型特征:手法稚拙古樸,形體端莊,神態凝重肅穆,服飾色彩鮮艷,衣紋簡潔流暢,是其摩崖造像最主要的藝術特色。
在形象塑造方面,大佛低平肉髻,薄發無紋,豐頭短頸,雙肩渾圓,著圓領通肩袈裟,結跏趺坐于七層佛座之上,雙手掌心向上重疊置于腹部,結禪定印,目光凝重而剛毅。菩薩面相略見圓潤,頭戴三瓣蓮式寶冠,體態豐腴,雙手托持寶蓮,表情虔誠溫順,慈眉善目。形態之中雖有北魏的清秀余韻,但整體呈現出豐潤敦實的特點。而這種豐壯敦厚的造型,也正是北周佛像的共同特點。
北周雖然在歷史中存在的時間很短,但在我國佛教藝術發展史上卻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進一步吸收外來佛教造像的精髓,與中華民族傳統的雕刻技藝加以融合,又創造出了一種肌膚豐腴、體魄健美、神情生動和充滿活力的藝術形象,為迎接唐代佛教藝術鼎盛時期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拉梢寺摩崖浮雕大佛無疑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
(三)藝術特色深受天水麥積山石窟的影響。早期石窟的開鑿地點,是與佛教藝術自西向東傳播的情況相一致的。佛教東漸,首及新疆,次及甘肅河西走廊,隨后進入中原北方地區。甘肅南部地區尤其是渭水流域是甘肅石窟寺分布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從最早十六國后秦時期始鑿以來,逐漸形成了以古代秦州麥積山石窟為中心的廣大石窟分布區。這一地區多數北朝石窟的遺存都與麥積山石窟的作品相近,應該是受到了麥積山石窟的影響,如拉梢寺石窟的北周雕塑均和麥積山同期作品相同,很有可能是屬于同一工匠集團所做,是研究中國佛教雕塑史的重要實物資料。
(四)多元文化的反映也是拉梢寺摩崖造像的藝術特色之一。拉梢寺摩崖大佛造像中反映的豐圓適中、深目高鼻、細薄而貼身的“濕衣”和佛頭像后面大圓盤代表光環的“法式”,明顯帶有印度佛教造像藝術的風格特征。大佛底座處在造像題材、風格和內容上近于寫實的象、獅、鹿等神獸以及半球狀彩繪的印度式覆缽塔等,都直接或間接地表明了拉梢寺北朝摩崖造像與古代中亞及西域的淵源和關系。
拉梢寺摩崖題記所載主持鑿建拉梢大佛的尉遲迥本來就是北方少數民族,而這一姓氏也來自于中亞胡族。美國學者羅杰偉在《北周拉梢寺藝術中的中亞主題》一文指出,拉梢寺摩崖大佛佛座浮塑中象、鹿、獅的造型,尤其是中間一頭大象頭朝前的形式常見于中亞地區的裝飾藝術中。同時在我國新疆克孜爾石窟第224 窟的壁畫中就有類似的大象畫面,這正是北周時期中原內地與西域、中亞不斷進行文化交流的客觀反映。
二、拉稍寺石窟造像的制作技藝
拉梢寺所在地的山巖屬第三紀砂礫巖,其巖石結構顆粒粗大,結構松散,無法完整進行雕刻制作。因此在修造龕像時,多是利用自然洞窟中較為垂直平整的巖面打樁懸塑或施泥彩繪。這一手法,在北方地區也多有使用,如麥積山石窟及炳靈寺等。
具體來講,摩崖石胎浮塑的制作是在崖面上先鑿出一佛二菩薩的石胎大形,雖不及普通石雕精細,但也已將五官的大形、四肢和衣紋雕出大概,同時為了泥層能夠牢固,將佛和菩薩的袈裟和裙裾衣紋雕得比較突兀而細密,減輕了泥層壓力,然后在其表面依序敷設幾層泥,直至完成塑造并施以彩繪。
底層敷設的泥料內加入了麥秸草稈,厚約2~3厘米,利用這層泥調整造像的整體關系,并做出大體細節。之所以使用粗泥的原因正是要使其在可控范圍內適度開裂,將上下幾層泥料的干燥收縮引向泥料內部,以此避免完成的造像出現表面開裂現象。在此基礎上,敷設一層細泥,一般是經過反復淘洗沉淀所得,在其內加入各種物質以提高膠結性能,常人所知有棉麻碎屑等,但據古代史料所載另有“糯米、粳米、小油、黃蠟、桐油、硼砂、皂角、土布、生絹、瓦粉” 等。拉梢寺摩崖浮塑大佛經歷1000多年之后,其表面仍然堅如磐石且細膩如滑,可見古時匠作工藝之精湛,尤為可貴的是這種做法綿延千年,歷代匠師在長期雕塑實踐中總結提高,直到今天的廟堂泥塑仍沿用此法,這也不由使人更加贊嘆古人的聰明智慧。
在造像的塑造環節,古代匠師克服各種困難,熟練運用各種泥塑技巧,展現出深厚的造型功力和審美追求。就技法而言,主要有“塑、挖、壓、貼、削、刻”等,充分發揮了泥塑在造型方面的主動性優勢,使大佛和菩薩整體比例勻稱協調,造型飽滿生動,在豐潤敦厚的基礎上又具靈動的氣韻,具有鮮明強烈的時代地域特征和藝術魅力。
綜上所述,拉梢寺石窟北朝摩崖造像,既展現了北周佛教造像莊重、敦實的藝術特點,又呈現出佛教造像民族化的智慧和胸懷。將雕刻、泥塑、彩繪等不同的造像技巧和諧相融并加以獨特應用,充分傳達了整體布局的宏大氣勢與嚴謹結構、造型技法和匠作技藝的純熟與深厚功力、造像氣韻的莊嚴與靈動,堪稱我國古代雕塑藝術中的又一精品。
【楊宇輝,西北民族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