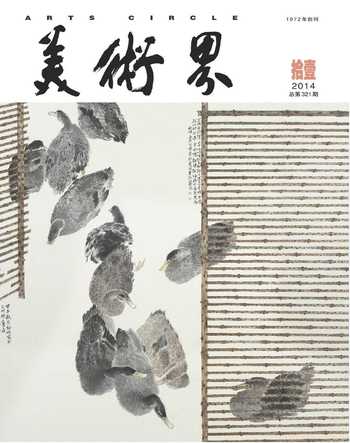中國古代女性繪畫“缺席”的情由
梁姁
【摘 要】歷史上,女性作為男性的從屬和客體的地位,因其薄弱的主體意識以及社會地位的淪落一直處于邊緣,使得中國女性繪畫黯然失色,在整個繪畫史中屬于弱勢和失衡。
【關鍵詞】古代女性繪畫;邊緣;古代女性畫家
在中國的古代和近現代美術史籍中,人們都把中國繪畫藝術成就歸功于男性畫家們,要尋找女性畫家頗為困難,能被記載下來的人數、生平事跡、畫作十分罕見,畫幅能流傳至今且能被我們所目睹的更是寥寥無幾,婦女的藝術才能一直都不被社會所提及,如被提及也可能只是一種點綴和陪襯。其中的原因并不復雜,大致可有幾種解釋。
從社會層次看,自父系氏族社會形成后,社會分工的出現,在日新月異的社會正當職位中也并沒有供給女性一些相應的職業,她們參與不到家庭之外的社會公共事務中,并不能獲得社會應當給予的尊重。社會不需要女性通過某項技能去獨立養活家人,也不可以像男人那樣自由的拜師學藝,更不能行萬里路去“搜盡奇峰打草稿”,因此女性被局限在私人領域之中,為家族繁衍后代、服侍一家老小的日常生活成為她的責任與人生使命,這樣也就導致婦女們沒有機會被社會了解。無論是文學,還是藝術領域,一直是以男人為主流,即使有聰慧過人、才華橫溢的個別婦女,她們的作品也只能在親朋好友小范圍中傳遞,往往如流水落花,了去無痕。就算是藝術史籍上偶爾有記載,也沒有作品能被流傳,對后世影響甚微。例如湯淑玉《玉臺畫史》中記載:“李夫人,西蜀名家,未詳世胃。善屬文,尤工書畫。……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要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窗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到了宋代,繪畫史中女性藝術家的姓名才逐漸被提及,但是她們的名字只是在男性親屬的姓名之后出現,身為女性的她們,不管自己多么有名氣、有聲望,貢獻有多大,都只能是以某人之妻、妾,某人之女、某人之姐妹等身份出現。比如,趙希全妻湯氏、陳暉之子婦方氏,等等。古代社會中,大部分的女性藝術家沒有自己姓名,由此可以推斷出當時社會的男性藝術史家們輕蔑女性,她們的獨立藝術家身份更是完全沒有被世人所認可。而生活在塵世中的另一群特殊的女性——名妓,她們平日里在與文人墨客的交好中,學習到一些繪畫知識與技能,正是由于這種不受干涉、不怕議論地特殊女性身份,才使得她們在侍候男性之余,不受凡俗干擾的從事著藝術創作,進而提高自己身價,這也是她們謀生和競爭的手段。而那些嫖娼的男性就算不是飽學之士,也要故作風雅,大肆吹捧才思敏捷、能書善畫的妓女,她們的作品這才能夠為風雅者所珍,名聞遐邇 。例如“蘇翠者,建寧之妓,以寫蘭竹名……”
至元、明、清諸朝,女性畫家的相關記載才日益增多,但是與男性畫家相比較,人數還是寥若晨星,比例嚴重失衡,很明顯她們只是一種點綴,一味調劑品。例如元代夏文彥編《圖繪寶鑒》記載“由始皇……下訖元”、“一千五百余人”,女畫家有7人。清政府于1907年頒布的女子教育章程中,雖然明確說明女性受教育是合乎法律的,但是她們的教育至始至終都在圍繞“三從四德、賢妻良母”等特點來展開。清代徐沁《明畫錄》所記載畫家1028人,其中女畫家22人。所以能側身其間的女性作品,也必須符合男性藝術規范,適合男性文人們的審美口味,以他們的評判標準載入史冊。這樣,女性一直處于一種邊緣位置,是文化層面上適應男權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調味品,無論如何她們都不會超過同時代的男性畫家的地位。
其次,來自家庭條件的制約。19世紀以前,只有當家里的經濟條件能夠滿足她們繪畫所支,以及家庭中的主要成員支持她們學習繪畫的情況下,才能夠從容的進行繪畫創作,美術史家們認為這是她們自我排憂消遣、填補時間空缺的一種娛樂方式。嶺南學界巾幗冼玉清在《廣東女子藝文考》后序中談道:“其一名父之女,少稟庭訓。有父兄為之提倡,則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閨房唱和,有夫婿為之點綴,則聲氣易通。其三令子之母,儕輩所尊。有后嗣為之表揚,則流譽自廣。”由此可見,當時女性想要成名成家可謂比登天還難,她們需要具備上等社會的良好出身、被支持去學習繪畫藝術的家庭環境、大量的閑暇時間等。她們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能夠成為男性眼中的一名賢妻良母,卻并不提倡從詩作文。
然而女性自身也存在一些主觀因素,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她們順利成章的把各種倫理道德、封建思想信為是天經地義、不可違逆的指南。統治者政令、輿論教化、家族誘導等無不據之而行,封建禮教的條條框框抑制了她們作為“人”的主體性意識,她們起初渴望受教育的想法被拋之腦后,把目光投向家庭瑣事,即使那些意欲表達自身情感的婦女通常拿起來的是針,而不是筆,描畫的是日常生活所需的被褥、被單或是繡花工藝品,而這些都不能被當作是藝術。在她們眼前呈現出這樣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能否畫畫不重要,能不能畫好更沒關系,她們看重的是自身的名份。而這種思想幾乎把女性畫家從整個中國藝術史中徹頭徹尾的抹去了,她們自信心喪失,認為創作毫無意義、毫無價值可言。
同時中國古代女性畫家缺席,原因還包括她們不能夠更深層次的進行理論研究,沒有對繪畫的技法多少創新,更是忽略了政治和權力的影響力。翻看中國的美術史冊,我們發現一些偉大男性藝術家,如東晉顧愷之的《畫云臺山記》;唐朝王維以詩入畫,意象萬千,并采用“破墨”法變革中國古代傳統山水畫;元代趙孟頫將書法用筆引入繪畫,做到融會貫通;明代徐渭自創“水墨大寫意”;還有從中國近現代大師徐悲鴻提出的“改良中國畫”、林風眠的“中西調和”等藝術理論觀點中可以看出,在理論上這些偉大的男性藝術家們提出了新的主張,或是在技法上都有新的突破,才使得男性藝術家們較女性藝術家們更容易獲得成功,而這些成功因素必當要引起女性藝術家們的重視。
不可置否,還有一些女性藝術家出生于官宦之家或是名家之后,前代在社會中擔當著有影響力的角色,他們的榮耀和地位為后代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是創造了便利的優勢條件,成為她們獲取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力量。由此可見,女性藝術家的缺席與社會的政治地位和權利也息息相關。
由此,我們能夠看出,中國古代女性繪畫一直處于社會的邊緣,女性畫家以及女性藝術作品可謂是鳳毛麟角。現在,我們通過找出女性繪畫缺席的一系列原因,期待在社會的迅速發展中,中國的女性藝術家們不束縛于傳統,不昧封建思想,孜孜不倦,勤奮努力,帶給我們一個別樣的藝術天地。
參考文獻:
[1]于文瀾.畫史叢刊 [M].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
[2]徐虹.女性:美術之思[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3]冼玉清.廣東女子藝文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41.
[5]謝麗君,李倍雷.中國美術史[M].合肥:安徽美術出版社,2003.
【梁 姁,安徽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