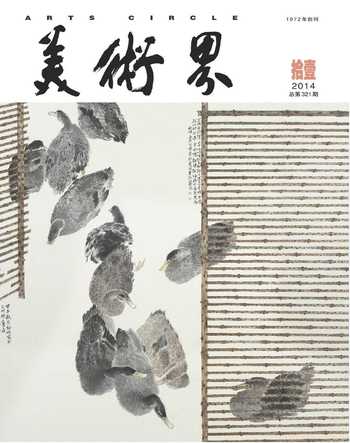商周云雷紋飾探究
【摘 要】作為商周時期最典型的青銅器紋飾之一,云雷紋的相關研究卻十分鮮見,這與學界往往將其僅僅界定為裝飾地紋或者輔紋有很大關系。本文結合詳實的研究資料和考古發掘成果,旨在對云雷紋的形態及其蘊含豐富的社會、宗教、人文因素進行深度的剖析與探討。
【關鍵詞】云雷紋;云紋;青銅紋飾;商周祭祀文化
一、引言
“云雷紋”是商周青銅器紋飾“云紋”和“雷紋”的統稱,一般來說圓形的為“云紋”,方形的為“雷紋”。這兩種紋飾都以渦旋形為基本架構并多用作青銅器表面裝飾,起到豐富背景、烘托主紋的作用。追溯源頭,“云雷”這個詞最早出現于北宋王黼編撰的《博古圖錄》。宋人之所以以“云雷”來命名這種盛行于青銅時代的古老圖形是受到許慎相關字形學學說的影響。許慎在《說文解字》中對云雷二字字形有如下注解:“云,山川氣也。從雨,云象云回轉形”①“靁,陰陽薄動雷雨生物者也。從雨,畾象回轉形”。②由此可見,許慎認為在古文字“云”“雷”兩字的各種形態中均出現的重要構字元素“回轉形”是古人對于相應自然物象地圖像化呈現。直觀之下,甲骨文中的云字“
云雷紋的圖形雖不復雜卻也經歷了一個從簡單到繁復的演變過程: 早期云雷紋圖形相對簡單,多應用于條狀的邊框裝飾;而之后則逐漸呈現為多層的渦旋紋,精致的圖紋往往密集的布滿整件青銅器的表面。云雷紋雖然被公認為商周時期青銅器裝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圖形元素,但相關研究卻因其“輔紋”“地紋”的定位而長久以來被學術界忽視。甚至,很多學者將云雷紋在商周時期盛行的原因簡單歸結為其圖形的高度適用性和美觀性。但是,僅從形式的層面來理解云雷紋無疑是片面的。事實上,紋飾總是別有深意,自古以來即是信息傳遞的重要媒介,甚至是其所處時代中人文、社會、審美特征的集中視覺呈現。為了透徹、全面的解讀隱藏在云雷紋背后的意涵,本文的討論首先從云雷紋的雛形即新石器時代的渦旋形云紋開始。
二、追根溯源:新石器時代的渦旋云紋
云雷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的渦旋形云紋。雖然,兩種圖形所處的時代相距甚遠,但是極其相似的渦旋狀結構揭示了兩者之間緊密的關聯。大量于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云形器為我們解讀商周云雷紋提供了寶貴的線索。人們在大多數與紅山文化 (約公元前4700~前2920年) 相關的中心墓葬中發現勾云狀玉掛件,而值得一提的是這些中心墓葬的所有者均為“王”(如圖1)。相關研究證明玉在紅山文化中是一種專用于祭祀的神圣材質。郭大順指出: 對生活于紅山文化時期的古代先民來說,玉不僅是政權的象征、人與神交流的媒介,更被賦予高貴品德,并因此而具有珍貴的內涵。對應至這些云形裝飾的掛件,其在墓葬中所處的中心位置及其特殊的玉材質都表明它們是表征王權與神權的符號。
云紋在良渚文化(約公元前3300~前2000 年)中的運用更印證了這一點。云紋與鳥紋、太陽紋等其他圖形共同構成良渚祭祀器物上最常見的符號,并反復出現在器物表面相同的位置(如圖2)。這些渦旋狀云紋也呈現出與商周云雷紋極其相似的圖形結構及布局特點,與后者有著明顯的承繼關系。良渚文化祭祀體系的基礎是中國傳統獨特的二元世界觀,即代表宇宙(如:“天”與“陽”)的“圓”與代表地與“陰”的“方”周而復始的相互作用而架構了生生不息的世界。以良渚文化中最重要的祭祀器琮與璧為例,琮與璧在祭祀儀式中的使用往往是密不可分的:璧在外形上模擬太陽圓形的運行軌跡并喻示太陽與天空,是良渚先民與天神、太陽神和人類始祖交流的重要媒介;琮則用來祭祀地神和女性先祖,甚至是女性貴族的特有標記(如圖3)。這些帶有渦旋云紋的物件的獨特祭祀功能及其所蘊含的深刻中國傳統宇宙觀念佐證了一個事實,即云紋與其他重要原始紋飾如太陽紋、鳥紋一樣是權貴與神圣天神的標記,更是人與神及先祖溝通的重要媒介。
很顯然,形態與結構上的高度相似性是人們將新石器時代祭祀文明中出現的渦旋形云紋界定為商周云雷紋的雛形的重要憑據。但是,如果說新石器時代文明中出現的渦旋形云紋與商周云雷紋有著直接的承繼關系,那么前者所具備的祭祀特性是否會在后者同樣得以延續?帶著這個啟發性的疑問,讓我們進入商周時期的社會文化情境深度解讀云雷紋。
三、商周祭祀文明中的云雷紋
殷商甲骨文為我們提供了解讀云雷紋最原始的文獻資料。據考證,甲骨文記載的內容以祭祀為主,其中與供奉自然神和先祖相關的占卜是最常見的主題。這證明祭祀是青銅時代早期社會和文化體系的核心,也為揭秘云雷紋提供了兩條重要的線索,即自然崇拜和先祖崇拜。
云在商周自然崇拜文化中占據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殷商甲骨文中就發現了大量有關云的文字,摘選如下:“呼雀燎于云,犬(《合集》1051)”“燎于帝云(《續》2·4.11)”“癸酉卜,又燎于六云五豕卯五羊(《合集》33273)”“惟岳先酒,乃酒五云,有雨(《屯南》651)”“……若茲……六云……其雨(《合集》13404)”。③
不難看出,云在祭祀儀式中的出現主要有兩層含義:首先,云是被膜拜的重要自然神;其次,云是預示降雨的重要兆象。人們密切關注自然界中云的形態、顏色和運動的變化,并據此為不同類型的云設定嚴苛的祭祀制度。儀式中,“燎祭”是最常用的祭祀方式,這與燎燒的過程中升騰的煙霧與天空的云彩極其相似有直接的聯系。
云在祭祀中特定角色的形成其實源自中國古老的農耕文明。悠久的農耕傳統決定了中國古人對于自然的態度:一方面,人們依賴自然而生活,崇尚“天人合一”。另一方面,險惡的自然環境讓人們心生畏懼,產生原始的自然崇拜:人們相信“神秘”的自然力都源自神的意愿,只有誠心的膜拜、祭祀才能得到神的護佑。自然界中云霧形態、色彩、運動的變化預示著天氣的變化,尤其是降雨,對古代農業生產有著舉足輕重的指示作用。在古人眼里,云正是神秘莫測的神的力量的顯現,故而被奉為重要的自然神和兆象。
云在早期祭祀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必然反映在視覺領域中。正如貢布里希所說,古老文明中的神秘圖像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它們不僅是審美的需求,更是力量的象征。古人相信圖像能護佑他們對抗自然力及其他未知力的肆虐。換言之,古老圖像的創造往往是為了達到某種神秘的宗教目的。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云形器和渦旋形云紋,以及商周青銅器上的云雷紋都是這類古老圖形的典型代表。人們將云轉化為祭祀儀式中的圖形,并期望以此獲得神的力量和保護,祈禱風調雨順。
先祖崇拜是商周祭祀文化中的另一個重要主題。Sarah Allan 在研究中指出:從古至今,先祖崇拜一直是中國宗教文化的核心,因為中國人相信人死后會繼續存在于另一個世界并需要生者通過祭祀不斷地供奉食物。更重要的是逝者具有操縱生者的能力,既能庇護生者,也能給生者帶來災難。大量考古發現已然確證了這一點:商墓中大量發現了填滿食物祭品的陶器和青銅器皿;而甲骨文占卜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如何恰當地向先人供奉祭品來阻止他們的詛咒并獲得蔭庇。
盡管呈現抽象幾何的簡單形態,云雷紋卻有著與先祖崇拜的傳統緊密關聯的深層意涵。商周青銅器多為祭祀用器皿是學界早已確證的事實。也就是說,裝盛供奉給神靈和先祖的祭品是青銅器的主要功用之一。Sarah Allan因此推斷青銅器上的紋飾絕非簡單的裝飾,而是一種超越現實、屬于靈界的視覺語言,象征著溝通與穿越。通過這些紋飾,祭品得以穿越生與死的界線,到達被祭祀者,從而實現生者與死者的溝通。云雷紋正是這類神秘圖形中重要的一種,密集排布的渦旋形紋樣所產生的強烈流轉動勢正是實現兩個世界之間穿越與傳遞的最佳視覺顯現。
云雷紋這種轉變與溝通的意涵可以通過對商周青銅器主紋的解讀得到進一步的論證。盡管青銅器上的主紋豐富多變,但圖形的種類卻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制。饕餮、龍與水族動物(如:蛇)、鳥、貓頭鷹、蟬和少數呈現寫實風格的動物圖形(如:鹿、大象、虎、犀牛)是商周青銅器上最常見的紋樣。這些題材都關乎死亡、轉變和存在于現實之外的世界(地下或天上):饕餮由祭祀用的動物和人所組成,它用來吞噬和殺戮的大嘴,正如同通向另一個世界的通道;潛伏地下的龍與來自天上神圣世界的飛鳥往往被結合成同一個圖像;蛇具有蛻皮的習性并象征著死亡;鹿周而復始地蛻去它的鹿角并再生……(如圖4、圖5、圖6)。
盡管主紋形態多變,但云雷紋一直是青銅器上不可或缺的地紋和輔紋紋飾。密集云雷紋旁襯下的主紋醒目而有力,展現了一幅可怕的未知神靈在云霧繚繞間出沒的景象。在祭祀儀式的參與者眼里,禮器上無處不在的云雷紋是神圣、莊嚴的符號,它們暗示著人們膜拜、祭祀的另一個世界的確實存在,是溝通人類與那些正俯視人世卻不被人們所知的神秘神靈的媒介。凝視這些青銅紋飾,祭祀者心中會油然而生恐懼、敬畏的情感。毫無疑問,正是云雷紋運用在視覺和象征意涵上大大強化了祭祀儀式的神圣氛圍并最終實現了人與先人及神靈的溝通。
四、結語
綜上所述,商周云雷紋集中體現了中國古老祭祀文化的延續性,其內在意涵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讀:首先,云雷紋是自然神“云”的表征符號;其次,云雷紋烘托出神秘而讓人敬畏的祭祀氛圍并暗示著青銅禮器上所描繪的神秘主紋物象的非現實性或者神性,是不同世界(現實世界和存在于人類感知之外神靈世界)存在的標示;再次,商周青銅紋飾是古人與神靈世界溝通的語言,人們希冀通過這些紋樣穿越生與死的界線把祭品送達所祭祀的神或者先人。確切地說,這些紋樣是實現現實世界與神靈世界之間轉化的視覺語言。古老的云雷紋正如同中國祭祀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焚香環節所產生的裊裊青煙都被古人視作呈送他們的祭品與愿望至另一個世界的重要載體。
注釋:
* 本文為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傳統云紋的文化判讀”(湘哲社領[2012]14號)的階段研究成果。
①許慎.說文解字[M]. 北京:中華書局, 1963:242.
②許慎.說文解字[M]. 北京:中華書局, 1963:241.
③郭沫若.甲骨文合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8-1983;姚孝遂,肖丁.小屯南地甲骨考釋[M].北京:中華書局,1982.
參考文獻:
[1]楊成寅,林文霞.雷圭元論圖案藝術[M]. 杭州:浙江美術出版社, 1992:216.
【蘇 豐,湖南師范大學美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