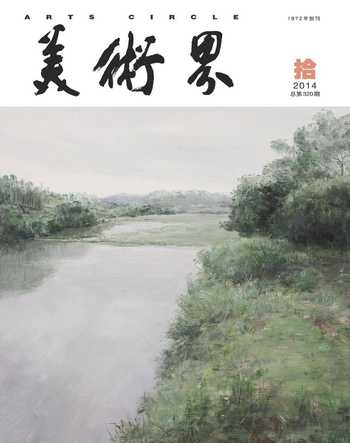圖案、符號、文化
[摘 要]作為日常生活的哈薩克民族工藝的裝飾圖案符號體系,形態豐富,形式多樣,體現出哈薩克民族的社會結構、社會制度、生活態度、生活觀念等社會文化,蘊涵著哈薩克民族的民俗、信仰、審美等精神文化。對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體系文化的闡釋,不僅要對圖案符號體系藝術本體進行分析,更重要的是對圖案符號的創作者所存在的社會進行深入分析,從而理解哈薩克民族圖案的審美特點和文化內涵。
[關鍵詞]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文化
柳宗悅在其代表作《工藝文化》一書中,對工藝進行了分類并提出工藝的基本特點,認為工藝是為了一般民眾而制作的器物,以實用為第一目的。工藝在滿足了實用目的后,就在工藝器物上進行圖案裝飾。這是不是就可以判斷圖案的產生是在滿足人們的日常生活之用的目的之后,就產生了我們所視覺感知的圖案藝術。我們從藝術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圖案藝術的產生是非常復雜,要完全探尋它,是一件非常困難甚至是幾乎不可能的任務。認為圖案的作用是為了裝飾,這僅僅是圖案作為裝飾的審美文化之一,圖案同時還體現著其制作者的社會制度、生存狀況等社會文化,以及蘊涵信仰、情感、心理等人的精神文化。對圖案的闡釋不僅從圖案藝術形式的本體角度進行審美文化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從制作圖案的人所生存的社會的社會學和人的情感、精神方面的人類學角度分析,進行圖案文化闡釋。對于歷史悠久、形式多樣的哈薩克傳統圖案,也應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哈薩克民族傳統圖案的文化闡釋。
一、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
哈薩克民族圖案藝術的發展過程實際是文化符號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因為人是符號的動物,人類所有的精神文化都是符號活動的產物。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在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圖案符號的類型、形式的歷史性以及圖案符號的符號化過程都顯現出本身的特點和內在的性質。
(一)圖案形式的日常生活化和理性認識的符號化
藝術中使用的符號是一種暗喻,一種包含著公開的或隱藏的真實意義的形象;而藝術符號卻是一種終極的意象——一種非理性的和不可用言語表達的意象,一種訴諸知覺的意象,一種充滿了情感、生命和富有個性的意象,一種訴諸感受的活的東西。因此它也是理性認識的發源地。從歷史性的角度來看,古老的哈薩克原始民族,將圖案刻畫在山崖峭壁的巖石和散落的石塊上,隨著工藝的發展,在工藝器物滿足了哈薩克民族實用目的后,逐步的在工藝器物上開始刻畫和制作圖案。從出土文物和草原民族的實用物品中很容易看出,所有的工藝圖案裝飾都出現在與他們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生活用品中,諸如氈毯、服飾、馬具、床具、袋包、刀具、家具、器皿、樂器、首飾、帷簾等。圖案的使用開始日常生活化,這種日常生活化的圖案藝術就變成了藝術符號。哈薩克民族圖案在符號化的過程中,哈薩克民族對自我的認識,個體的經驗、感受、情感等非理性因素和思維、判斷等理性因素參與到圖案的制作中,圖案形式逐步成為蘊涵意義的藝術意象,具有了人的知覺意象、情感、生命特征和訴諸人的生活感受的符號形式。
(二)圖案符號的形態類別與轉向
哈薩克民族圖案紋樣從表現內容可分為幾何形紋樣、自然形紋樣。幾何形紋樣以方形、圓形、菱形、三角形、多邊形等幾何體為基本形體結構,自然紋樣包括動物、植物、人物、自然景觀及其變形。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哈薩克民族圖案的幾何形紋樣伴隨著哈薩克民族圖案形成、發展的始終,只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藝術情境中,因哈薩克民族的認識、理解、情感、知覺、思維等因素,使幾何形紋樣所傳達的意義因人的知性和自我意識的發展而有所不同,而動物圖案、植物圖案與自然圖案與哈薩克民族的地理空間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哈薩克民族對地理分布上的動物、植物以及自然形態的視覺感受,逐步形成動植物及自然形態的感覺和知覺,在精神和物質需要的驅使下,根據他們的生產、生活經驗和審美需求按照一定圖案結構規律經過概括、抽象等方法逐步形成動物、植物以及自然物的心理圖式,而后形成圖案紋樣和圖案的符號化。從圖案的生命史或圖案符號的藝術發展史來看,動物、植物、幾何形等圖案形態表現出一定的連續性和交替性,并未因信仰宗教而發生斷裂,也并未遵循從低級到高級的進化模式,無論是構圖、色彩運用,空間布局、圖案紋樣、適用范圍、審美旨趣都不能證明現代人比古人高明。
(三)圖案符號的形式意蘊
在哈薩克民族圖案藝術中,對稱的主導性原則源自于哈薩克民族對自然形態的視覺感知和主觀意識的參與。自然中的節奏、比例、復合、簡約、線條、色彩等因素成為圖案的形式因素,自然形紋樣和幾何紋樣體系不過是同一觀照形式和文化方式的不同表現形式。在主觀理性思維的指導下將自然紋樣和幾何紋樣相互交替整體布局在哈薩克民間工藝中,以色彩和線條追求各種紋樣之間的對稱、節奏、比例關系的視覺和諧。哈薩克民族圖案形式的意蘊中色彩是重要的表現手段,色彩既是感覺的,也是心理的,同時也是生理的。哈薩克民族對自然環境色彩的視覺感知,形成強烈的自然色彩規律,表現出飽和的色度和強烈的色彩對比的色彩形式。同樣在心靈的深處內化為自我情感的色彩感受,也形成民族圖案的色彩表現形式,生理上的色彩冷暖感受也成為色彩符號的形成因素之一。哈薩克民族圖案的色彩形式整體上表現為色彩飽和、對比強烈、富有象征意義的色彩符號形式。在民族圖案藝術形式中,還要講究主次,考慮節奏、平衡等,達到一種和諧完美的效果,而這一效果的實現是通過對事物認識中的簡化原則而實現的。
二、民族圖案符號的文化內涵
符號是意義的代碼,實際上也是文化的代碼。人們能用符號進行交往,根本原因在于那些作為信息載體的實物,在人的文化聯系中具有了特定的意義。這些實體的意義,并不是它天然的就有了,而是處在文化世界中的人所賦予的,或者說,這些實體只有在人的文化世界中才會獲得它本身所不具有的意義,它才能成為這些意義的載體。而這就是“文化”的意義。從以上符號與文化的關系來看,歷史悠久、形式多樣、內涵豐富的哈薩克民族圖案,既是哈薩克民族圖案藝術的符號形態,也是哈薩克民族文化意義的外化形態。
(一)民族圖案符號所體現的游牧生活文化
生產事業是一切文化形式的命根,他給予其他文化因子以最深刻最不可抵抗的影響……我們可以相當肯定地說,生產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現象,和它比較起來,一切其他文化現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我們也可以從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看,生產方式決定和影響著哈薩克民族圖案藝術。同時,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藝術是由人創造的,人的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因而,圖案藝術也就展現了人的社會生活狀況、生產情況、社會制度、民俗習慣等基本的生產文化和社會文化。
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弗朗茲·博厄斯認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只能理解為歷史的產物,其特定性決定于各民族的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①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在形態上表現為植物紋樣、動物紋樣、幾何紋樣基本形式。以植物為主的各種自然植物再現性圖像符號,如:石榴花、忍冬花、腎臟花等草原上能夠見到的各種漂亮花卉而形成的各種紋樣符號,這是一種最直接的母題圖形的自然模仿;以動物為主的直接來自于“觀物取象”,反映了一些動物再現性圖像符號,如:羊、馬、牛、鹿、天鵝、雄鷹等動物形象。在服飾和日常器用中動物圖像符號、巖畫和雕刻中的人物圖像符號,還有一些以生活中的事物為原形,生產或制作的物體形象符號等,都是以草原上或生活的周圍環境中所常見的事物為主題內容。幾何紋樣也來自于草原上自然物體形態,然后將其抽象與概括后有規律性的加以應用。雖然紋樣形式在不同時代和不同器物上的表現形態有所不同,但他們的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體現出生活的歷史性,造就了文化的一致性。所有這些紋樣形式都展現出對哈薩克民族以高山、草原、河谷為獨特生存環境為主的地理文化和以游牧生產方式為主的游牧文化。
民族圖案在色彩上飽和的純色、強烈的顏色對比,藍色、紅色、白色、黑色等色彩的使用,代表藍天、太陽、真理、快樂和幸福、春天和青春等象征意義,給人一種濃重的草原民族氣息,使我們感受到哈薩克民族草原上豐富色彩的地域環境文化和他們的日常生活文化。哈薩克民族圖案中有寓示生靈常在并代神佑畜的羝角紋(公羊角、鹿角、牛角等)、代表草原畜物保護神的鷹紋、表達豐收之意的花卉及果實圖案(程式化的多瓣花、葡萄等)、象征吉祥美好的動物圖案(孔雀、鳳凰),有幾何、花卉、飛禽走獸以及大自然中的各種植物等圖案,這些圖案的主體是自然主義的,體現了質樸自然的草原生活藝術文化。
(二)民族圖案所蘊涵的審美文化
一種審美判斷力并不意味著證明了這一審美標準在所有的文化中都采取相同的形式。從實際來看,一切文化都是對現實加以美化而構成的。博厄斯認為:我們不能把這種世界范圍內的傾向簡單歸結為任何其他的終極原因,而不歸結為由圖案所激發的一種情感,換言之,歸結為對一種美的沖動。
傳統民族圖案在歷史上不是孤立存在的文化現象,他是審美與實用、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是物體之上的主體美的物化形態,是審美觀念文化紋樣化的表現。哈薩克民族圖案中自然紋樣和幾何紋樣是哈薩克民族對自己現實生活中自然現象的視覺感知,形成視覺形象,將視覺形象進行思維的活動,轉變成視覺圖案符號。在這一視知覺活動中,展現出來的是哈薩克民族對自然物象的整體感知能力,幾何圖形的概括性和對幾何圖形在思維意識中的組合能力,對自然中所表現的對稱、重復等自然秩序規律的運用,將自己的喜好、高興、悲傷、懷念、崇敬等情感因素參與到圖案藝術的制作中,諸如宗教、法律、制度、習俗等在心理上的制約因素參與在圖案創作的視知覺藝術活動中。如幾何圖形樣式簡潔,色彩樸素鮮明,圖形線條相對的粗獷豪放、淳厚大方;在木制器皿上的幾何形、日月形和簡單的花卉所體現出的簡潔、樸素雅致;在房屋的房檐上或大門的門頭上連續的花形紋或連續三角紋所具有的韻律;在木箱或木柜上規則的幾何紋和現實自然紋的結構;在服飾上圖案豐富多變,圖案的位置分布和形式多樣;重復、繁華的花草紋、三角紋裝飾在地毯邊緣、屋檐、窗簾等物品上統一而又美觀。雖然圖案樣式各異,它們的形式特征主要是對稱和重復。而哈薩克圖案中的對稱既表現為整體圖案的對稱又表現為每個單獨紋樣的對稱。這些圖案所顯現的審美特點都是人的視覺活動轉化為心理活動,然后又內化為審美意識,顯現為審美特征。因而視覺圖案符號藝術是一種文化活動的力量,包含了哈薩克民族的視覺感知、認識活動、心理感受、思維活動、審美感覺等一系列心理活動。
哈薩克民族圖案符號表現出獨特的審美特征。哈薩克民族圖案藝術表現出和諧、樸素、雅致的整體審美特點,而在具體的圖案符號以及符號的不同使用和組合形式上又表現出具體的審美特點。圖案中自然動物、植物紋樣的表現,是哈薩克民族追求生活和諧的幸福美和對自然物的崇尚美;哈薩克人特別喜歡紅、綠、藍、白、黃幾種純凈的顏色,特別是以日月星辰、云水花草等形象裝飾出的手工制品上的圖案更是著色濃郁,對比鮮明,集中反映了哈薩克族善良、勤勞、健康、愉快的思想感情及樸實的審美觀。刺繡圖案中動物紋樣的生動形態、植物紋樣的千姿百態、抽象紋樣的概括簡潔以及各種圖案的巧妙組合,形成自己的獨特風韻,顯現出單純、生動、簡潔的美感特點。注重圖案中自然規律對稱、重復、大小的運用等,把抽象和具象、自然形態和加工變化的圖騰紋飾、嚴密緊湊地構成格式以及艷麗的色彩統一為整體,顯現出圖案藝術的節奏美和韻律美。服飾圖案中的圖騰觀念,是一定物質基礎的產物,社會經濟基礎的變革必然引起意識形態的變化,并借助于傳統觀念和意識形態創建的服飾藝術觀念,也就賦予了圖騰新的意象。這些被“分化”出來的人的意識和精神,一旦復歸并結合至具體的個體身上,形成強化的心理導向,就會產生一種特定的形象,由此就會產生相對穩定的審美追求。
哈薩克族信仰伊斯蘭教以后,哈薩克織繡藝術在工藝、圖案、色彩等的運用上,部分上保留了傳統原始宗教的特點,更多的是體現了伊斯蘭教的宗教特色和統一、單一、運動的伊斯蘭美學形態,圖案的整齊、重復、規則的排列,對稱、均衡和節奏的置陣的審美特征。
三、民族圖案中的宗教、思想文化
哈薩克族在歷史上曾信仰過薩滿教、祆教、景教、佛教等,現在哈薩克族信仰伊斯蘭教,遵奉遜尼派正統主義。在宗教信仰的突出表現上就是對圖騰的崇拜和禁忌,這些圖騰崇拜和禁忌既有原始宗教的遺跡,也明顯表現在對信仰的伊斯蘭教的教義上。圖騰是超日常的集體儀式中,對社會性的情感和表征的有形表達,因此,群體成員在集體活動中常常用有形的和具體的物體來表示它們。如哈薩克人的圖騰表現為對火的崇拜,他們認為火是家庭的恩人、明燈,具有生命、靈性和某種神圣的力量,把火稱為“阿拉斯”,意即“夜間的火、神圣的火”,認為火是世界的本源之一、火是太陽在地上的化身。哈薩克族中有“我們的火母親,使挨凍的人得到溫暖,使挨餓的人吃飽”。②哈薩克人還對草原動植物進行崇拜,哈薩克族認為馬、牛、羊、駱駝都是各自有其主宰的神。這些圖騰崇拜物就會以圖形、圖像的方式表現在哈薩克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反映在哈薩克民族的圖案符號中,呈現出一定的植物紋、動物紋、幾何紋等圖案特征。這些符號圖像的能指即為本身圖像形象,而作為所指和內涵意義則表現為自然現象的崇拜、神靈觀念、圖騰觀念、祖靈觀念等原始意識,同時也是原始哲學思維的萌芽。
民族圖案符號中的水、火、土、云等自然現象,以及將其抽象化的符號的頻繁出現與使用,自然天象圖形的具象和抽象符號的相互組合、符號化形態的出現等,顯現出哈薩克民族樸素的自然萬物觀和宇宙觀念,他們在對世界的本原的看法上,具有樸素唯物主義的觀念和現實自然的客觀實在性。圖案中將不同形態的動植物紋樣、幾何紋樣,不同種屬的動植物形態類別,不同空間的物體圖形符號組合和建構在統一圖案體系中,顯現出哈薩克民族期望的自然和諧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圖案中具體物象的圖案化,表明哈薩克民族認為物質是世界萬物的普遍的本質和共同的屬性,物質決定意識的道理,具有豐富的辯證因素。
哈薩克族在信仰伊斯蘭教以后,在圖案符號藝術表現內容上最明顯的區別就是,動物紋樣和有生命物體形象的禁止,日常所見的自然景象如花卉、果實、云彩、水波紋等,體現出伊斯蘭教樸素的社會生活觀念和態度。紋樣形式由自然形態的具象形式逐步走向抽象紋飾,枝葉為螺旋狀紋,后又出現彎曲莖蔓的葡萄紋,自然紋樣與天象圖形相結合構成圖案形態,孕育著伊斯蘭教天地融合的觀念。色彩的使用更為復雜,整體色調沉穩,象征宇宙萬物的深奧精神和生命力頑強的伊斯蘭思想。
藝術是表現人類情感的符號。古老的哈薩克民族將生活中的所感、所思、所想轉化成圖像符號,創作出各種形式的藝術作品呈現出來,即富有圖像符號所表現的顯示意義,又具有深刻的內涵意義,充分體現了哈薩克人的藝術審美特色,也體現出哈薩克游牧民族獨特的草原文化。
注釋:
*本文為2013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新疆哈薩克族傳統工藝文化研究”(項目編號:13CB126)科研成果。
① [美]博厄斯,金輝譯.原始藝術·導言[M].上海藝術出版社,1989.
②阿利·阿布塔里普,汪璽,張德罡,師尚禮.哈薩克族的草原游牧文化(Ⅱ)哈薩克族的文化藝術,人文禮儀及禁忌習俗[J].草原與草坪,2012(6).
參考文獻:
[1] 參見[日] 柳宗悅,徐藝乙譯. 工藝文化[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20-22.
[2] [美]蘇珊·朗格,滕守堯、李海榮譯. 藝術問題[M].南京出版社,2006:134.
[3]仲高.絲綢之路藝術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173.
[4] 蕭楊.文化學導論[M].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186.
[5] [德]格羅塞,蔡慕輝譯.藝術的起源[M].商務印書館,1984:29.
[6] [英]伯特·萊頓,朱東曄、王紅譯.藝術人類學[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26.
【郭泳儒,新疆伊犁師范學院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