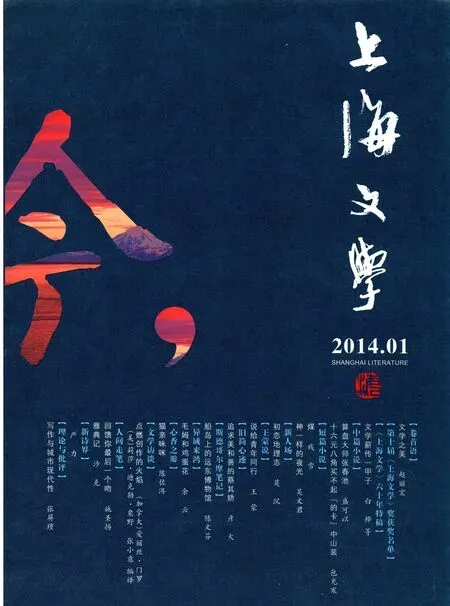寫作與城市現(xiàn)代性
張屏瑾
在中國城市化的過程中,相比經(jīng)濟(jì)和物質(zhì)環(huán)境的快速變化,文學(xué)性成了一個隱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像一把標(biāo)尺一樣,衡量出人們在急遽的生活轉(zhuǎn)型之際,未能同步轉(zhuǎn)變的意志、趣味、思維和觀念等等。換句話說,那些在“我城”之中被壓抑掉的不適感,通過白日夢的發(fā)酵,理應(yīng)回歸到藝術(shù)作品當(dāng)中,而建立起屬于這個時代的形式。城市并不是簡單的地理或地域概念,一方面,它是社會生活基礎(chǔ)建設(shè)的獨立體,另一方面,它又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產(chǎn)生種種典型的現(xiàn)代自我認(rèn)同,這兩方面的結(jié)合,構(gòu)成了我們今天所說的空間。自有現(xiàn)代歷史以來,空間就不僅僅是物質(zhì)規(guī)劃的后果,而是重新塑造人的感受與行為方式的文化場域。每一個來到城市的人,都會改變這座城市,也會被城市所改變,從而重新定義自己與外部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這使得城市成為了一個獨特的審美對象。正如布羅代爾所說,城市勢力之大,竟能左右整個國家。城市猶如一個超級主體,而寫作必然表現(xiàn)這一主體的話語功能。寫作應(yīng)該是對城市生活從形式到內(nèi)容的寫照,同時,也是對城市現(xiàn)代性的批判。
從歷史上看,隨著工業(yè)革命、啟蒙思想以及現(xiàn)代性的展開,城市曾經(jīng)一次又一次地為某一特定時代的寫作者內(nèi)心注入新的動機與創(chuàng)造力。寫作的意義在于,在現(xiàn)代知識范式轉(zhuǎn)換下,建立時代精神的話語和新的審美觀,扶植人們在現(xiàn)代世界中對于自我的重新認(rèn)識,與此同時,表達(dá)人們在生活觀層面上的,各種各樣的訴求。城市中的寫作并不一定自然主義式地還原城市風(fēng)貌與細(xì)節(jié),更重要的是創(chuàng)造城市中的“人的條件”,包括新的生活方式、趣味和想像力、情感教育,等等。廣義的寫作(也包括其他類型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對城市居民來說自有其重要性。當(dāng)下中國城市的寫作,無論意識還是內(nèi)容,都不應(yīng)該持續(xù)落后于城市生活給予各種人群的感受,落后于各種人的命運被城市改變的速度,落后于城市幻夢的生長。
考察當(dāng)下寫作與城市現(xiàn)代性的關(guān)聯(lián),一個前提是,這樣一種關(guān)聯(lián)曾經(jīng)在1920年代的北京,1930年代的上海、廣州,1940年代的昆明、重慶、香港等地,引發(fā)相關(guān)的創(chuàng)作潮流。雖然,人們多給予那些作品和流派“現(xiàn)代主義”的稱謂,實際上,現(xiàn)代主義在近現(xiàn)代中國的發(fā)生,正是與不同的空間感受結(jié)合在一起的。從空間的角度考察現(xiàn)代主義,就會發(fā)現(xiàn)它不僅是,甚至完全不是一種影響和比較意義上的思潮,而是出自藝術(shù)家對于生活環(huán)境變化的探索。這種探索固然精彩,卻又十分短暫。空間問題在中國現(xiàn)代歷史的發(fā)生過程中,注定會變成一個意識形態(tài)論爭的副產(chǎn)品。城市的命運變化不定,作家的寫作也經(jīng)歷多重波折,然而就是在短暫起伏、迷惘和波折之中,讓我們看到了混合了戰(zhàn)爭、殖民地、商業(yè)化、革命等等一切的錯綜復(fù)雜的空間感受。這些支離破碎的城市之夢所制造的,往往是大俗的傳奇或奇觀,如張愛玲、無名氏、徐訏作品中小市民的悲歡離合,或是市井生活孕育出的神秘幻覺。亦俗而大雅,如馮至和穆旦等人的詩歌所表現(xiàn)的破碎和整飭之間的關(guān)系,城市的日常生活倫理與動蕩的民族國家命運之間的悖論。城市曾經(jīng)意味著極大的不確定,激動人心的可能性和超乎想像的新奇文明,寫作則完全在人與城市的共同成長中成立。
其次,現(xiàn)代白話文原本就植根于社會整體轉(zhuǎn)型帶來的劇烈變化。在“背井離鄉(xiāng)”或是“浪蕩進(jìn)城”的總體氛圍下,近現(xiàn)代文化中存在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藝術(shù)主題:鄉(xiāng)愁。從鄉(xiāng)村到城市的寫作,都與鄉(xiāng)愁的情緒有著很大的聯(lián)系。正如魯迅所說,由于城市新文明造成的陌生感,僑寓作家們只能追憶家鄉(xiāng)風(fēng)土,“回憶故鄉(xiāng)的已不存在的事物,是比明明存在,而只有自己不能接近的事物較為舒適,也更能自慰的”。鄉(xiāng)愁與流浪感結(jié)合成為波西米亞式的漂泊感受,兼以自戀、傷情、頹廢,也成為他們的敘事的整體基調(diào)。那一代人所經(jīng)歷過的,相對而言比較完整的鄉(xiāng)村與傳統(tǒng)生活經(jīng)驗,提供了鄉(xiāng)愁書寫的來源,也成為書寫城市的起點之一。
1949年以后開展的城市改造,逐步掃蕩城市中所有藏污納垢、暗影叢生之處,如同一則家喻戶曉的散文標(biāo)題展現(xiàn)出的自信——“臭水溝變成林蔭道”。新中國以后出版的文學(xué)史,將城市中的寫作敘述為“小市民、知識分子的灰色生活”所構(gòu)成的“城市生活的面影”①。與此同時,戶籍改造政策使得城市的流動性幾乎下降為零②。這光明、坦白、凝固、講求工業(yè)化與現(xiàn)代化生產(chǎn)力的城市,幾十年間所造就的城鄉(xiāng)差異,更多體現(xiàn)在心理層面。城鄉(xiāng)之間完全隔膜的生活經(jīng)驗,對農(nóng)村人的不再同情的理解,自“新時期”由一類新作品傳達(dá)出來。在小說《陳奐生上城》中,“火車站”和“招待所”既是新的城市想像的符號,也是城鄉(xiāng)關(guān)系中呈現(xiàn)出的社會重新官僚化的象征物,農(nóng)民陳奐生差一點犧牲在了這兩種進(jìn)入城市的途徑之中,而這失敗的經(jīng)驗卻反過來變成了他理解新的社會秩序的資本。這種經(jīng)驗的隔膜還體現(xiàn)在新的衛(wèi)生、文明和美的觀念之上,風(fēng)靡一時的小說《人生》中有一個經(jīng)常為人引用的細(xì)節(jié),美麗的農(nóng)村姑娘巧珍為了符合心上人的現(xiàn)代衛(wèi)生觀念,用把牙刷努力改造自己,并做出“堅持刷牙”的新穎的愛情承諾。在那一鄉(xiāng)村文化全面褪色的歷史拐點上,回蕩在我們耳邊的是德順爺爺對高加林發(fā)出的感嘆,“巧珍,那可是一塊金子呀!”
鄉(xiāng)村中國與城市中國息息相關(guān),但城市化讓它們處于一種此消彼長的關(guān)系之中,今日的城市寫作有如今日的城市建設(shè),總是推倒、拆毀舊日的遺跡,無論這些遺跡是否扎根于民族的心理、習(xí)俗和情感,一律要拆毀重建。實際上,鄉(xiāng)村生活受到城市的輻射,年輕一代的生活內(nèi)容在很大程度上已經(jīng)被城市文明所裹挾,有更多從鄉(xiāng)村出走的年輕人亟需受到城市文化的啟蒙,實際上,他們本身也在當(dāng)代城市建設(shè)的模式之中,為城市文明奠基。在國家—社會—市場的整體規(guī)劃中,“流浪者”以進(jìn)城的勞動力以及小部分的流民面貌出現(xiàn),“打工文學(xué)”、“底層敘事”等因而成為書寫城市空間的一個重要內(nèi)容。賈平凹的《高興》,劉震云的《我叫劉躍進(jìn)》;劉慶邦、曹征路的城市底層系列,丁燕的東莞打工系列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寫作。這一類作品,似乎有意將鄉(xiāng)村的經(jīng)驗帶入城市,使之在倫理層面上發(fā)揮一些作用,有時候,鄉(xiāng)土生活習(xí)慣變成了城市中的打工者和流浪者所據(jù)以生存的唯一條件。但是,這種條件并不充分,無法據(jù)之建立起道德理想,更不用說據(jù)之批判現(xiàn)代文明了。小人物依靠本心之善在大城市中重拾溫情脈脈的人際關(guān)系,這如同田園詩般的浪漫主義想像,卻未必常常有效,有時恰恰是城市中的游戲規(guī)則,捕獲并檢驗出所謂的人性“本質(zhì)”與城市空間結(jié)構(gòu)的矛盾關(guān)系。
李師江的小說《鞏生與彩霞》中,民工鞏生與妓女彩霞發(fā)生了一樁性交易,本來按照大城市的生存法則,他們會立即擦肩而過,但由于彩霞無意中找了鞏生一張假幣,兩人圍繞這張假幣產(chǎn)生了糾紛,他們才發(fā)現(xiàn)原來兩人是鄉(xiāng)里鄉(xiāng)親的。在大城市的貨幣哲學(xué)面前,鄉(xiāng)土鄉(xiāng)情完全不起任何作用,底層生活中的艱辛和無奈倒是被這張假幣一一喚出。底層人群同樣依靠城市生活的市場與商品邏輯生活,只不過,這種商品邏輯延伸到末端,除卻了一切涂飾與包裝,呈現(xiàn)為最粗糙和直接的演算公式,往往是由他們來直接承受這些赤裸裸的生存演算。寫作在這里呈現(xiàn)出寫實本色,傳遞城市中的多元空間和人群的信息和狀態(tài)。值得注意的是,這類寫實只能將這些信息與狀態(tài)定義為真實,定義為自然,卻難以從這種“真實與自然”之中提煉文化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敘事,因為它的敘事的出發(fā)點往往在于大城市整體化的分層想像,各種等級秩序建構(gòu)了城市空間的理性化秩序,有如豪宅與貧民窟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好比城市拾荒者,他們的生活建立在城市排泄出來的垃圾和碎片之上,他們必須對垃圾和碎片加以分類,而他們本身的生活也成為這分類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底層敘事雖然包含人文關(guān)懷,在城市中間起到表現(xiàn)苦難和撫慰人心的作用,但同時也變成一種類型化的寫作,在城市寫作的分類法當(dāng)中承擔(dān)其結(jié)構(gòu)功能。底層敘事在大城市中往往是去政治化的。
彼得·比格爾認(rèn)為,現(xiàn)代社會中藝術(shù)起著矛盾的作用:“它投射了一個更好的秩序的意象,就此而言,它是對流行的壞秩序的抗議。但是,通過在想像中實現(xiàn)更好秩序的外觀意象,它對現(xiàn)存社會中那些導(dǎo)致變革的力量所造成的壓力起舒緩作用。這些力量被局限在一個理想的領(lǐng)域”(【德】彼得·比格爾《先鋒派理論》)。在20世紀(jì)二三十年代,中國最早的一批現(xiàn)代派作家通過感知都市中空間、社會的巨大分層而獲得了階級和民族想像,以城市為背景逐步建立自己的政治、文化認(rèn)同,同時也構(gòu)建了自足的城市寫作范疇,建立起一系列的意象。他們來到城市后,看到的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試圖對之加以理解,加以追問,給出種種不完滿的定義和結(jié)論,那些有歧義、裂縫和可能性的城市空間,像噩夢一樣折磨著藝術(shù)家的神經(jīng),必須書寫城市。
相比之下,今日的寫作者面對的,是同一個世界的不同的層級和分類,無論多么不協(xié)調(diào)的建筑、貧民窟與殘破的廢墟,訴說的是景觀社會的同一個邏輯。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像是在這片新的場域當(dāng)中尋找座標(biāo),這是一次脫胎換骨的過程,作家將自己綁上城市化的流水線,變成機械復(fù)制時代的抒情詩人。如果僅僅把中國當(dāng)代的先鋒寫作定義為西方藝術(shù)技巧的模仿,那么它的高潮顯然已經(jīng)過去了,但是,如果著眼于先鋒的叛逆精神,包括比格爾所說的,處在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中的先鋒藝術(shù)的悖論性,那么針對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市場的先鋒寫作其實還未到來。另一位德國人斯賓格勒曾說,“絕對的城市”“像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每一偉大文化的生命歷程的終點”(【德】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它所投射的速度感、機械感,人和人之間的功利化相處產(chǎn)生的距離,以及自我保護(hù)產(chǎn)生的精神麻木等等,對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廣義上可以包括所有的中國人)的精神持續(xù)產(chǎn)生壓迫力。考察今天在城市中的寫作,會發(fā)現(xiàn)這種壓迫力常常以兩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首先,是對物質(zhì)符號的迷戀。鮑德里亞曾將現(xiàn)代物品分為使用功能、象征功能、歷史性和系統(tǒng)性等層面。戀物是商品拜物教向人的心理乃至身體領(lǐng)域的擴(kuò)張,這似乎已經(jīng)成為了現(xiàn)代性中的一個不可顛覆的邏輯③,物質(zhì)符號作為寫作中純粹的裝飾品而存在。從1999年出版的《上海寶貝》到2008年出版的《小時代》,新世紀(jì)十年形成的一種精神狀態(tài),跟品牌形影不離,這類寫作也始終暢銷。其次,從王朔的青春期到朱文的美元,再到1970年代出生的作家馮唐的《北京,北京》,京城青年喜歡從自嘲出發(fā),有時傾向于自我取消。油滑、虛無,時刻準(zhǔn)備著傷心又時刻準(zhǔn)備著滿不在乎與遺忘,幾乎成為了漢語在上世紀(jì)八九十年代至今的表達(dá)特色之一。使用這種語言所抵抗的,基本上是城市生活的空洞與不真實。城市中除了眼花繚亂的景觀外,還有城堡似強大的官僚機器,脆弱的個體無法與之對碰,小人物和失敗者的悲涼感轉(zhuǎn)化成了躲避、逃逸、消解、嘲諷等寫作姿態(tài),假裝放逐語言內(nèi)涵,敘事朝低處走,緊貼地面以獲取生存的真實感。這一類作品在述說小人物的內(nèi)心壓抑時,有時非常激進(jìn),但這樣的激進(jìn)很快就被更加來勢洶涌的大眾文化所吸收。
有些年輕的作家開始重新尋找城市現(xiàn)代性的特性,也許“先鋒”、“荒誕”、“超現(xiàn)實”這類昔日桂冠已經(jīng)不再合適戴在他們頭上,如果他們?yōu)檫@些名詞生產(chǎn)出了新的內(nèi)涵,那可能會是:酷。實際上是針對新的異化生存狀態(tài)的寫作。港臺地區(qū)這樣的寫作已經(jīng)算得上是成熟,像北京、上海、廣州這樣的大城市,其強度、速度、“絕對感”和消費社會的特征也毫不遜色,但這一類型的寫作似乎才剛剛開始。首當(dāng)其沖的問題是對現(xiàn)代時間的感知,現(xiàn)代社會將人的所有生活納入到線性時間的規(guī)律化切割當(dāng)中,形成了一種現(xiàn)代時間霸權(quán)下的新的集體意志,這種看不見的威權(quán),卻是以個人自由的面目出現(xiàn)的。阿乙的短篇小說《先知》,將象征現(xiàn)代理性、健康生活和個人自由的“時間表”推演成一張“終極作息表”,人們一切行為的意義最后都在于“殺時間”,龐大的現(xiàn)代時間統(tǒng)治著人們,時間的流逝本身就是鐵律,就是現(xiàn)代性的“一個牢籠”,人們實際上并沒有真正支配自己人生的自主權(quán)。這就是小說中一位精神疾患者寫在一封書信里,試圖告訴所有人的“先知”內(nèi)容。
除時間這樣的抽象物外,城市的典型意象,也不再僅僅作為故事的背景或符號化的點綴出現(xiàn),而成為批判工具化生存本身的寫作對象。地鐵對城市居民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之物了,但地鐵中獨特的精神狀況與冷漠癥,卻剛剛開始有人表達(dá)和研究④。被歸為科幻作品的韓松的小說《地鐵》,把現(xiàn)代生活的極限想像,速度與距離的關(guān)系、公務(wù)化生存等等元素,與底下的兩條鐵軌和一團(tuán)漆黑聯(lián)系起來。我們在地下空間穿梭,造就了一次又一次與異形相遇的驚魂時刻,實際上是與我們自己相遇。
世界上最大的軌道交通市場,正在這里迅速形成。億萬人都降入了地窟。他們不再過祖先們千百年來沿襲的生活了——面朝黃土背朝天,而是匿身于厚厚巨石下,成了不銹鋼車廂中的居民。而在某些線路上,早已“妖孽叢生”。
閱讀這一類作品,有一種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對于生活越來越人工化、越來越孤獨的孩子來說,他們試圖提煉城市生活的形式感,試圖把環(huán)境與人的關(guān)系,真正落實到那些手段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奴役和創(chuàng)傷之上,制造出與精神迫力相對應(yīng)的意象,他們的寫作,會越來越深刻和成熟。但另一方面,這也就意味著,六十年來社會價值觀的精神紅利正在流失殆盡,不安全感,異化感,被剝奪感,遲早會在淺薄的拜金電影、僅追求輕松一樂的白領(lǐng)話劇之后降臨到年輕人頭上。寫作在這場文化領(lǐng)導(dǎo)權(quán)的轉(zhuǎn)變之中,究竟可以承擔(dān)什么樣的功能?在這里可以對照另外一篇描寫地鐵的小說,王繼明的《借個男友回家過年》,作品描寫了回上海工作的知青子女,一名年輕的地鐵女司機的生活。女主角長得并不漂亮,沒法跟城市里的女孩子相比,但她對生活充滿期待。
深夜時分,我駕駛著最后一班地鐵結(jié)束運營,回到梅隴地鐵基地。走進(jìn)地鐵司機公寓,已是子夜。梅隴之所以叫梅隴,是因為到處種著梅花。司機公寓樓就處在梅花包圍之中。對于大上海來說,元旦還是初冬,天氣還未冷透,深夜的梅隴有些許寒意,梅花還未開放,只是探頭探腦地露出細(xì)細(xì)的嫩芽,就好像我對愛情微弱的向往。
地鐵響著鳴笛,從黑黢黢地下深處開出。候車乘客騷動起來。我沒動。我雙眼看著四周洶涌的人流,我鼻子嗅著四周涌動的味道。對,到處是生活的人流。對,到處是人的味道。
作為荒誕象征物的地鐵,從女司機的勞動者眼光中來看,雖然也時常引發(fā)她的疲倦和安全擔(dān)憂,卻不再是異化的,經(jīng)歷了一場甜蜜而酸楚的假訂婚事件之后,她更將自己駕駛的這架地下列車,視作充滿煙火氣的生活的載體。在這里,“全自動”機械所引發(fā)的黑暗想像,被人在勞動中建立起來的主體感和尊嚴(yán)感所克服。城市的動物,既是它的工具也是它的犧牲品的蕓蕓眾生,還原為有自控能力的,有血有肉的人。這篇小說仿佛回歸到了工業(yè)時代的城市氣氛之中,有一點懷舊的意味,但并非如通常那樣懷上海1930年代的舊,而是重新提出了普通勞動者與城市的關(guān)系,雖然是小題材,卻有大敘事的味道。
《借個男友回家過年》這樣的小說傳達(dá)出清新和樸素的氣息,遺憾的是,這類作品并不多見。事實上今天所能看到的寫作,更多的是大量現(xiàn)實原料的堆積和泛濫,瑣碎而無序,讀來令人沮喪。中國城市的快速發(fā)展和變化,必然在精神層面制造出新與舊的強烈對比,倫理的斷層,豐富的物質(zhì)消費之下,人們對自身的理解卻停滯不前甚至趨于短視與保守。所以,一方面是景觀社會,另一方面,生活的實質(zhì)倫理內(nèi)容卻變得日益空洞,與大城市帶來的不安全感結(jié)合在一起,催生了一種對只與眼前利益得失相關(guān)的細(xì)枝末節(jié)的關(guān)注。城市小說因此變成了城市故事會,充斥著雷同的生活噱頭,夸張的情節(jié)和作者毫無控制力的絮叨。這類寫作看似基于日常生活,卻是在擴(kuò)大生活的裂隙,是對拙劣生活的更加拙劣的模擬,是贗品中的贗品,雖披著“日常真實”的外衣而出現(xiàn),實際上是一些劣質(zhì)趣味的展現(xiàn)而已,很難從中得到任何升華。不夸張地說,如果僅僅是用這一類雞飛狗跳的故事作為表征,那么今日寫作的尊嚴(yán)正在大面積地倒退與降低。
好在日常生活的美學(xué)問題從來就是一個歷史問題,在后現(xiàn)代理論家,如西美爾、列斐伏爾和德·塞都那里,日常生活本身是一個對現(xiàn)代性的診斷。理論家們常常追問,現(xiàn)代生活中各種紛繁的、看上去無頭緒的、互相脫離的原子構(gòu)成,應(yīng)該如何在其中找出總體性。在這些歧義叢生又雜亂的線索之后是否埋藏著一張總體性的地圖,這不僅僅是一個哲學(xué)問題。從人類歷史上可以看到,越是在日常現(xiàn)代性的過度刺激和極度分裂爆發(fā)的時刻,總體化的危機感和敘述追求也會愈發(fā)強烈,這本身是在城市現(xiàn)代性內(nèi)部生成的獨特現(xiàn)象,20世紀(jì)的藝術(shù)、社會學(xué)、哲學(xué)的發(fā)展都與這種獨特現(xiàn)象有關(guān),甚至被日常生活的美學(xué)綜合成為同一種文化美學(xué)寫作。
在中國的現(xiàn)代歷史之中,日常生活一直是重要的主題,每臨歷史變局,就會有一大批憧憬、書寫穩(wěn)定日常生活的作品出現(xiàn),而對于形成一個準(zhǔn)市民社會來說,日常生活話語同樣是其中重要的元素。早在民國初年,一批新文學(xué)作家的作品就表現(xiàn)出對重組日常生活的關(guān)注,城市的日常生活蘊含基于個人主義價值觀的新倫理,對于中國現(xiàn)代“自我”的生成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1940年代戰(zhàn)亂結(jié)束之后,更是掀起了日常生活寫作的高潮。當(dāng)代仍有一些作家在積極地延續(xù)這一種風(fēng)格,新的作品,如蘭州作家習(xí)習(xí)的《小酒館手記》,讓人想到蕭紅的《呼蘭河傳》,通過小酒館中的眾生相,把市井生活的花開花落,不溫不火地表達(dá)出來,更具一份別樣的蒼涼感。與中短篇相比,長篇作品在這一點上更有發(fā)言權(quán),有充足的容量容納一個類似于“城市之心”的主題。尤其是通過寫作長篇,可以關(guān)注一個或一群主人公的成長過程,將人物性格塑造成日常生活本質(zhì)的象征體,而將其命運塑造為偶發(fā)的凌亂的歷史事件,本質(zhì)與偶發(fā)的相遇構(gòu)成了所謂寵辱不驚的生活觀念。像上海這樣的城市,從整個中國現(xiàn)代歷史中來看,擁有相對穩(wěn)定的市民階層生活經(jīng)驗,他們久經(jīng)考驗,形成了自己的生存智慧與哲學(xué),依靠生活本身的重量抵抗一切浮華和變亂,在這一方面,確實可以形成結(jié)構(gòu)性的敘述,賦予日常生活以輪廓和框架,使日常的具體性不僅僅作用于人的感官,而是變成一種有機的藝術(shù)品,以部分地抵抗荒誕與宰制。不過,這樣的寫作雖然有主心骨,有世界觀,卻仍有一個問題,對于“變”與“常”的關(guān)系的本質(zhì)化強調(diào),使得每一次歷史變局的具體內(nèi)容與具體沖突被罔顧,被均質(zhì)化處理,被統(tǒng)一描繪成對于日常生活的滋擾,正如西美爾所說,市民對于“事物之間的區(qū)別”形成“總體性的漠不關(guān)心”。城市或許是這樣的一個熔爐,它將各種各樣的歷史動機吸納和熔鑄為信息與景觀的體系,在這一點上,寫作者必須與之展開漫長的對話。
① 參見王瑤《新文學(xué)史稿》,1951年北京開明書店初版,1982年上海文藝出版社重版,上冊。
② 1960年代開展的“上山下鄉(xiāng)”運動并非自然意義上的人口流動,雖然也在客觀上造就了城市與鄉(xiāng)村經(jīng)驗的一次互動。參見【美】托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鄉(xiāng)——一個美國人眼中的中國知青運動》,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③ 參見【法】鮑德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這方面有代表性的論述,參見殷羅畢的論文《作為媒介的地鐵空間及其催眠效應(yīng)——兼論當(dāng)代中國地鐵主題文學(xué)和電影》,發(fā)表于《上海文化》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