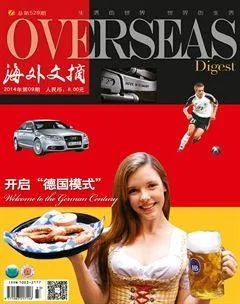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影響深遠
2001年,美國以“包庇‘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為由出兵阿富汗,推翻塔利班政權,隨后推動阿富汗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多領域的重建。然而,美國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爭,將大部分精力和資源轉移到伊拉克,塔利班獲得喘息之機,最終成功卷土重來,阿富汗戰爭呈現長期化趨勢。2009年,奧巴馬政府上臺,迅速公布了“阿巴新戰略”,其核心內容就是通過較大規模增兵實現阿富汗安全形勢的整體好轉,然后再逐步“撤出”阿富汗,由阿富汗安全部隊承擔主要的防務責任。2014年5月28日,奧巴馬公布最新撤軍時間表,將在2014年之后保留9800名士兵,2015年底削減至4900名,到2016年底削減到僅能確保駐阿使館安全的兵力水平。美國逐步“撤出”阿富汗、結束這一“史上最漫長的戰爭”,將對阿富汗及地區安全形勢、地緣政治博弈走向及大國關系產生深遠影響。
地區極端勢力或將再度抬頭
如上文所言,美國計劃在2014年后保留約1萬名安全部隊,其主要任務有二:一是繼續為阿安全部隊提供培訓、指導、情報支持和空中火力支援;二是繼續打擊“基地”組織等國際和地區恐怖勢力,防止其利用阿富汗領土“東山再起”。美軍這種讓阿安全部隊“打頭陣”,自己“退居二線”的軍事部署很難阻止地區極端勢力再度抬頭。
首先,阿富汗安全形勢存在短期內惡化的可能性。一是美國有限軍事存在的影響不明確,阿富汗將呈現“亞戰爭”狀態,恐怖襲擊、武裝沖突將成為常態。阿富汗國土面積遼闊,地形復雜多山,區區1萬名美軍遠不足以覆蓋阿境內的戰略要地,也無法對塔利班構成戰略壓制。美軍在2014年之后將不從事具體安全保障行動,而是偏重進行反恐行動。鑒于美軍高度依賴空中火力打擊和夜間突襲阿富汗民居,未來美軍仍有可能造成較大規模平民傷亡,進而引發當地民眾反對外國軍隊的排外情緒,并被塔利班利用收買人心。屆時,駐阿美軍將不是阿富汗的穩定力量,反而會成為一個破壞性因素。二是塔利班仍有能力在阿全境活動。塔利班是阿富汗境內反政府武裝力量的領導者,同時與“基地”組織、哈卡尼網絡等組織存在密切聯系。塔利班在阿境內大部分地區活動,主要控制城市郊區及周邊鄉村。2009年,塔利班已將活動區域從東南部的普什圖部落區向外延伸,擴展到阿富汗的中東部。到2011年,其活動區域覆蓋首都喀布爾北部地區,包括卡皮薩省、帕爾萬省、拉赫曼省。2014年,特別是總統大選開始以來,阿富汗境內暴力恐怖事件層出不窮。3月10日,塔利班宣布武力抵制總統大選,將外國人聚集區和選舉部門列為襲擊重點目標。3月20日,4名塔利班武裝分子攻入位于喀布爾的塞雷納酒店,造成重大人員傷亡。3月25日,候選人阿什拉夫·加尼的住所附近發生兩次爆炸。6月6日,武裝分子針對候選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連續發動兩次自殺炸彈攻擊。三是阿安全部隊不足以消滅塔利班。近年來,阿安全部隊戰斗力有所增強,如逐漸承擔主要安全保衛責任、有能力獨立采取軍事行動等。然而,阿安全部隊仍存在情報、后勤、空中火力支援能力不足等弱點,且不斷爆出遭塔利班等反叛組織滲透的傳聞。就阿國內武裝力量對比來看,塔利班雖無力像1996年那樣武裝占領喀布爾等大型城市,但阿安全部隊也無法阻止其在南部和東部地區控制相當數目的村鎮,更無法徹底消滅塔利班。
其次,巴基斯坦安全形勢同樣面臨嚴峻挑戰。2014年以來,謝里夫政府持續推動與“巴基斯坦塔利班”(簡稱“巴塔”)的和平談判。雙方同意暫時停火,并展開多輪接觸。3月5日,雙方談判委員會在首都伊斯蘭堡附近阿克拉哈塔克鎮一所宗教學校舉行對話,宣布完成第一階段對話,并進入至關重要的第二階段。然而,和談此后很快陷入困境。巴塔提出釋放“非戰斗”被關押人員、在南瓦濟里斯坦地區劃定“安全區”、在全國范圍實行嚴格的伊斯蘭教法等要求,這顯然超出了政府的承受范圍。6月8日,巴基斯坦卡拉奇的真納國際機場遭受恐怖襲擊,造成34人死亡。事后,巴塔發表聲明,稱和烏茲別克武裝組織共同制造了卡拉奇機場襲擊事件。這是巴基斯坦近期發生的最大規模恐怖襲擊,標志著巴基斯坦政府試圖進行和平談判的努力以失敗告終。在卡拉奇國際機場遇襲之后,巴基斯坦軍方于6月10日空襲了西北部與阿富汗接壤地帶的提拉山谷,并于15日宣布對位于北瓦濟里斯坦部落區的武裝分子展開代號“利劍行動”的軍事行動,目前已經進入地面進攻階段。巴方官員表示,巴塔并無談判誠意,只是希望通過談判爭取時間,待美國從阿撤軍后再以阿為基地重整旗鼓。近年來,阿巴境內極端武裝組織在人員上互通有無,在戰術上相互借鑒,在后勤方面互為“庇護所”以躲避本國安全部隊的打擊。例如,巴塔頭目法茲魯拉長期在阿東部的庫納爾和努里斯坦等省藏身。隨著美國及國際安全援助部隊逐步撤離,未來阿巴邊境線兩側的安全形勢不能排除交織共振、持續惡化的可能。
此外,美國撤軍將為以“基地”組織為首的國際和地區恐怖主義組織提供更大活動空間,有可能借機謀劃實施“反撲”。以“烏茲別克斯坦伊斯蘭運動”(簡稱“烏伊運”)為例,該組織目的是在中亞以武力建立“哈里發國家”,目前主要在阿巴部落區,特別是北瓦濟里斯坦藏身。
地緣政治環境更趨復雜
首先,地區國家在阿博弈趨于激化。阿富汗地理位置特殊,可謂溝通中亞、西亞和南亞的咽喉之地。隨著美啟動撤軍進程,地區國家紛紛加大在阿戰略博弈。例如,印度與阿富汗建立“戰略伙伴關系”,強化對阿政府支持力度。一方面,印度增加對阿經濟援助力度,對阿援助總額已達20億美元;承諾推動TAPI油氣管道等跨地區合作項目,幫助阿實現“陸橋”潛力。另一方面,密切安全合作,雙方承諾合作打擊國際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販毒、洗錢等不法行為。印度繼續為包括特種部隊在內的阿安全部隊提供軍事培訓,提供一定規模的軍事援助。阿富汗則不斷要求印度提供坦克、大炮、直升機等重型武器裝備。
地區國家在阿博弈對阿重建產生雙向影響。一方面,地區國家紛紛強化對阿投入,促進了阿在經濟、社會、安全等領域的重建進程,如環阿公路及連接阿與周邊國家公路網的日趨完善,普通民眾享受醫療、教育等服務水平不斷提高等。但另方面,由于各自利益訴求分野明顯甚至相互沖突,地區國家在阿博弈呈現明顯的對抗性,并成為阿實現長治久安的主要障礙之一。其中,印度與巴基斯坦、沙特與伊朗的對阿政策最具對抗性和排他性,并妨礙阿政治和解取得實質性進展;烏茲別克斯坦與俄羅斯也因歷史恩怨及現實分歧而在阿問題上相互拆臺,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上合組織作為地區機制在阿問題上發揮應有作用;地區國家間的矛盾還妨礙以阿為中心的地區交通網絡和經濟一體化的實現速度,阿要想發揮溝通東、中、西、南亞的“十字路口”作用仍有待時日,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阿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后勁。此外,美伊關系僵局也減少了阿富汗問題的脫困選項。
其次,大國地緣政治博弈逐漸壓過反恐合作。“9.11”事件后,美國時任小布什政府對外戰略重心定位為打擊恐怖勢力、消除恐怖威脅。在此情勢下,美國擱置地緣政治沖突,暫時放下“冷戰思維”,與俄羅斯、中國等大國展開卓有成效的反恐合作。反恐一度成為大國合作的重要“壓艙石”。但如今美國將反恐視為國家安全戰略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甚至明確指出反恐戰略必須服務于維護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美國以從阿富汗撤軍為契機推動國家安全戰略的深入調整,其實質是甩掉沉重“反恐包袱”,進而開啟美國全球戰略的新局面。在中、南亞地區,奧巴馬政府雖力推“新絲綢之路”經濟合作計劃,但其實質是謀取政治、安全利益,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大中亞”計劃確有復活的可能。即以美國控制阿富汗為契機,使其成為連接中、南亞的紐帶,同時與地區國家展開全方位、各領域的合作,在中、南亞建立一系列“民主政權”實現美國在該地區的利益,避免中亞國家投入俄羅斯和中國的懷抱。
面對美國新一輪地緣攻勢,視中亞為傳統勢力范圍的俄羅斯同樣動作頻頻。軍事上,俄無償向阿警察部隊提供2萬支步槍及250多萬發子彈,助其提高執法能力,同意出售米—17直升機供阿安全部隊使用,并與北約成立聯合信托基金專門維護阿軍配備的俄制直升機。俄就第201師駐塔吉克斯坦基地與塔政府達成了續租49年的框架協議,成功說服吉爾吉斯斯坦政府不再向美提供瑪納斯空軍基地,并保留俄在吉的坎特空軍基地。政治上,為確保在阿影響力,俄展開一系列外交活動,推動召開“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領導人峰會,承諾共同應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并從毒品生產、走私、消費的各個關節加大打擊毒品犯罪的力度;提出整合“上合組織”反恐資源,同意接受阿富汗為上合組織觀察員國;建議北約以解決阿問題為契機與集安條約組織建立聯系,以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為平臺就阿問題展開協商。此外,俄羅斯還推出“歐亞聯盟”戰略構想,試圖以此整合獨聯體地區,建立并鞏固其主導地位,對抗美國“新絲綢之路”計劃的影響。可以預見,大國在阿富汗及中亞、南亞地區將展開長期地緣政治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