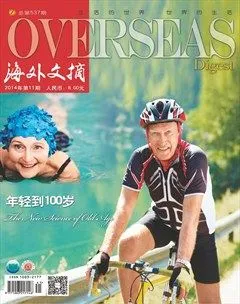折翼,之后

自欺欺人的力量是強大的,經歷損失和創傷時,它是至關重要的應對手段,能讓你逃避現實。今年2月我失去了大部分左臂,從那時起,我就活在一個與現實平行的思維空間,在那里我可以為所欲為,拒絕承認截肢所帶來的不便,直到4月6日那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出去跑步。
我摔倒的地方只不過是一段有點坡度的人行道,對兩只手臂的跑步者來說絲毫不成問題。事實上,這段人行道就在我家后面,我與它和平相處了許多年。手臂截肢后,有兩件事一再發生:第一,我總忘記身體一邊減輕了8磅,身體重心會明顯改變;第二,雖然我的手臂不見了,但在我的腦海里,它還像以前一樣,一直在那里,我感覺得到每個手指,甚至能感受到一直戴在左手腕上的手表。當我跌倒時,我完全本能地想用左手撐住身體,結果我的鼻子成了“替罪羊”,因摔倒而受傷。
當我躺在人行道上痛苦地呻吟,摸著滿是鮮血的臉,感覺到粘在傷口上的混凝土碎片時,我終于抵達了自欺欺人的盡頭。那一瞬間我終于明白,自己確確實實殘廢了。我摔倒時一位女士從不遠處經過,她看了我一眼,恐慌地對她丈夫喊道:“天吶,他的手臂怎么了?”“沒了,”我說,“但別擔心,不是今天發生的。”
說實話,我從未覺得自己的手臂“沒了”。整件事情如此偶然,讓我很難接受。簡要地說,我的慘痛故事是這樣的:當時我正在遠東采訪途中,先是去日本采訪福島核反應堆事故,之后到菲律賓采訪轉基因水稻問題。當我收起電視設備時,一只重型“派力肯”設備箱砸中我的左前臂。起初瘀傷相當嚴重,過了幾天竟然威脅到生命:急性骨筋膜室綜合征,阻礙血液流動。當我去馬尼拉看大夫時,他意識到這一問題,安排我緊急手術,試圖挽救這只手臂,但為時已晚,必須在生命和肢體之間做出抉擇。
麻醉消退后我清醒過來,又回到活生生的世界,確信醫生拯救了我的左臂。第一眼看去,藥物仍流淌過我的血管,真讓人開心。但是,左手沒了,前臂沒了,肘關節沒了,整個左臂沒了。不,手術根本沒成功。
過去我一直獨自旅行,作為獨立電視制作人,我總在想法子節省幾塊錢,成為了一個善于自己動手的人,“獨行俠”的記者生活非常適合我。這種氣質也是我不擅長于向他人尋求幫助的原因。從菲律賓醫院出院后,我住進了當地一家賓館,在一周多的時間里,我沒有讓任何人知道發生了什么。在我的想像中,他們一旦得到消息就會坐著飛機往我這兒來,我還得為他們的旅行、航班、酒店操心。但那時我真正想做的是管理好疼痛和思維。也許等傷口稍微愈合一些,我就可以偷偷溜回家。你懂的,就是自欺欺人地否認正在發生的一切。
我沒有召集親友團,而是沉浸在工作中,將福島的故事寫下來。在獨臂生活中,我遭遇的第一個真正的障礙是敲擊鍵盤,我只好搜索、安裝,并從此開始依賴語音識別軟件。我全力以赴撰寫福島故事,在大災難發生3周年之際,稿子必須趕出來。作為一名自由職業者,我要么及時把作品交上去,要么蒙受巨大的經濟損失。
一回到家,我就通過Skype通話軟件將情況告訴了孩子們。我21歲的兒子在北京學習,而19歲的女兒則在北卡羅萊納大學就讀。我很怕將自己的狀況告訴他們,但孩子們表達了對我的愛和支持,知道我依然活著,他們對此心存感恩,讓我熱淚盈眶。
另一項最大擔憂是生計問題。我從事的是一項注重外貌的職業,從沒見過獨臂電視記者。空蕩蕩的袖管會不會結束我的電視攝像生涯?在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的《新聞時空》頻道,大家待我如家人,同事們接受我、支持我,像我的兒女一樣。當我詢問身體殘了還能否進行拍攝和編輯工作時,老板告訴我:“沒人在乎。發揮你的聰明才智,努力去做吧。”
一直以來我總聽到截肢者說起別人盯著他們,把他們看成異類。在我第一次用一只手臂為《新聞時空》拍攝期間,我身穿顏色鮮艷的運動上衣,與接受采訪的一位女學者碰面。節目錄制途中她離開了一會兒,期間我將上衣脫掉了,當她回來看到我時,大吃一驚。我們兩人都看著那條殘肢,我聳聳肩說:“世事無常。”她微笑著點頭,然后我們繼續錄制節目。這個小插曲并沒有讓我如何煩惱——因為她的反應很實在。而當我每每發現人們刻意地將目光從我身上移開時,才更加讓我不安。是同情嗎?還是厭惡?走在人行道上,我直視那些看我的人,而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報以微笑。或許我仍魅力十足,抑或我是個怪物。
獨臂生活比想象中的要更容易掌控。試著把一只手綁在身后過一天,你會發現自己也能做任何事。雖然花費的時間會長一點,但可以做到。一些物件可以讓獨臂生活更便利。我使用的砧板固定在吸盤上,上邊安有刀片和小釘,可固定面包片和水果塊。我有一個開瓶器,可以單手使用;一個掛鉤,可以用來解開或扣上袖口的紐扣;一種名為Dycem的粘性材料,可以將瓶瓶罐罐牢牢地固定在桌面上。我也在學著使用義肢。作為一名科技類記者,近年來我報道過不少義肢方面的先進技術,但現在作為一名消費者,我看到了它們的不足。器械依靠傳動裝置驅動,傳動裝置依賴電池。這樣一來,手臂重量增加,可靠性降低,還不耐風雨。
修復醫生認為我應該會喜歡一只裝飾性假手,雖然它不具有實際功能,但看起來就像真的手一樣。他為我做了一只硅膠手臂,甚至還從我的右手上剪下些體毛粘在上面,讓假肢足以亂真。但我不喜歡它,我不知道要這個義肢給誰看,覺得沒必要造假,或者讓自己的形象更易被接受。
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幻痛。消失的左臂仿佛變成了魔鬼,像吊索一樣固定在我睡前看到的那個位置。早晨醒來,整個手臂似乎沉睡了一個晚上,現在又開始循環運作了。剛睡醒時,快樂無痛,手臂吊吊著,好似沒有重量。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手臂感覺越來越緊,逐漸轉變成為劇痛。此外,我還常常有一種手指被電擊到的感覺。
對于不存在的身體部位所產生的疼痛,醫生也不知道如何治療。針灸、按摩、運動治療我都嘗試過,我還試過鏡像治療。我在面前的桌子上垂直放一面鏡子,靠近坐著,看起來好像失去的左手又回來了。如果我集中精神移動不存在的左手,使之跟上右手的動作,大腦就會誤認為身體的內部神經系統仍是完整的,這種動作大大減輕了幻痛。
除了疼痛之外,獨臂生活的最大不便并非處理個人事務,而是與人合作。失去手臂前,我的工作日程排得滿滿當當,現在不管做什么都像老牛拉破車一樣慢, 有時更要費盡周折。想想早上我要做些什么吧:洗澡時我要戴上手套,用腿夾住瓶子,倒出沐浴露和洗發水。為了在腰上系條毛巾,我得用牙咬住毛巾一角再往后一甩,手從身后抓住另一頭,然后繞到前面塞緊。我用大腳趾踩著指甲剪的壓柄。穿襯衣前必須先系好右邊袖口,再將手伸進去,其他紐扣一只手就可以搞定,不過在每一顆扣子上要花費較多的時間。我從一位獨臂朋友那里學會了打領帶的方法,他的視頻在YouTube網上點擊率很高。
以前每天早晨的常規動作半小時足夠了,現在一小時我都干不完。每天結束的時候,工作總是達不到自己的預期,我的情緒一落千丈。凡事未必要親力親為,我也懂這個道理,只是不想承認罷了。我比以往更渴望別人的幫助。你猜怎么著?人們很樂意幫忙,尤其是其他截肢人士,他們對我傾囊相授一些建議和經驗。
遭遇不幸兩個月后,在家門外摔倒的那個早上,我平生第一次去看心理醫生,不知道從何說起。我們探討了損失及恢復能力,人要堅強地活著,勇敢地面對現實。意外發生后,關愛和鼓勵潮水般向我涌來,然而當談及這些事情時,我情不自禁地失聲痛哭,破天荒地發現自己的內心正在全然接納別人的關懷,獨行的氣質漸漸消失不見。截掉的手臂以某種方式將自己和其他人聯系在一起,這種感覺我從未有過。沒錯,我損失慘重,但在某種程度上我覺得自己因禍得福,這一次,我絕不是在自欺欺人。
[譯自美國《紐約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