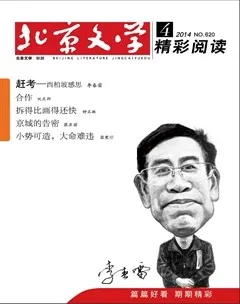西塘的心思
耽于玩耍的西塘,就這樣在千年的水巷邊,安然坐定。
我見到她的時候,她什么也沒說,只是神秘一笑,嘴唇抿緊,仿佛在刻意地守著一個什么秘密。其實,看一看水巷里悄然而逝的流水,便知道,西塘已經把浩浩蕩蕩的時光都誆進了水巷,而自己卻成功躲過了歲月的逼迫,繼續在春色可人的江南忘情流連,并成為一個讓人忘情流連的去處。
相傳,春秋時期,吳國大夫伍子胥興水利,通鹽運,開鑿伍子塘,引胥山(現嘉善縣西南12里)以北之水直抵境內,故有胥塘,別稱西塘。這樣算來,西塘的存在已經有兩千年以上的歷史了,不知道這兩千多年的時間,它到底是以怎樣的方式沿著抽象的時間之軸行走,依憑一個小小的空間讓自己在時間流程之外悄悄延宕下來。許多時代都已經從它的身邊一一過去,而它,至今仍然沒有起身離去。
地老天荒啊!
到底誰有勇氣和能力把這樣的守候或等待付諸實施?
人類總是在沿著具象的空間之軸到處奔走。前天鹽官,昨天嘉善,明天或后天又將是杭州或上海,我們不知道時間的秘密,所以無法在時間里久留。地也未曾老,天也未曾荒,只是有一天,我們和我們的心愿將一同在時間里老去,化為塵煙。大概,也只有西塘這樣的事物能夠懂得時間的秘密,只有西塘這樣的事物才能夠在時間里堅守并直指永恒。
太陽在水巷的另一端升起,照亮了西塘古鎮和古鎮的清晨。寧靜的街溪水仿佛受控于一種神秘的力量,突然就停止了流動,成為一渠泛著金光的油彩。逆光中,一只小船無聲地從水巷轉彎處駛來,恍若時光深處的一幀剪影。胭脂色的漣漪從船頭一圈圈蕩起,無聲,在濃稠而凝重的水面上傳播。遠遠望去,平滑的水波仿佛已經不再是那種液態的質感,而是水波過后留在沙地上的固態紋絡。此時,水巷兩岸的建筑愈發顯現出古舊的色彩和形態,粉墻黛瓦以及其間的斑駁,經過時光和歲月的反復涂抹修改之后,變得更加深沉、厚實。偶爾有微風從葡萄藤的縫隙間穿過,輕輕拂過臉龐,提醒我確實身處現實之中,并且正浮于時間的表層,但我的心,卻分明感受到了歲月的稀薄和時間的沉重。
這是一天中行人最為稀少的時刻,古鎮的一切都如一夜間去除了遮蔽、撣掉了浮塵,清晰地顯現于視野之中。走在狹窄而悠長的小街上,竟然能聽到自己腳步的回聲,空曠而悠遠,如同從很久以前傳來,又仿佛要傳到很久以后。低頭時,目光能夠很幸運地直接觸到那些辨不清年代的麻石。它們與兩旁林立的房舍,銜接得天衣無縫,就好像在兩千年前西塘剛剛誕生時就已經緊密地結合為一體。倒是在其間行走的行人與這些建筑有一點格格不入,貌合神離。很顯然,短暫的停留和居住,還不能讓我們把“根”扎入時間深處,我們無法打開與古鎮溝通、融合的心靈之門。
南來北往的客,紛紛慕西塘的盛名來看西塘,卻又難免經常與西塘擦肩而過。
有的人知道,西塘不僅僅是一渠水、一座橋、一篷小船或一些舊房子,更不是被杜撰、修改了很多次似是而非的傳說,但西塘究竟是什么,還是無法確定、無法明了。于是,便在游覽的流水線上格外地用心看、用心找。無奈市聲嘈雜,人潮如蟻,目光交錯如麻,心便被攪得紛亂,遂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最后只好乘興而來掃興而歸,自覺或不自覺地陷西塘于“其名難副”的怨聲之中。
有的人,興沖沖地到了西塘,一撲入西塘的街,一住進西塘的老房子,就把西塘徹底忘了。找一張正對著水巷的雕花木床,在徐來的溫風里,把沒有想完的心事繼續想起;抱著電話與遠方的親人或朋友“微”來“微”去;或隨人流在一家挨著一家的店鋪里找一件似曾相識的工藝品,盤算著如何低價買下,帶回家去……
很多來古鎮的人,吃飽喝足之后,總是要給自己留下一些曾到過古鎮的憑據,要么在某一重要景物上偷偷刻下“某某到此一游”,要么就是擁著擠著爭著搶著在古鎮的水巷邊、石橋頭或某一處刻著字的古宅前排隊留影,希望在古鎮背景的映襯下自己的倩影會更加雋永美好,以便事后愉悅一下遠方未能成行的親友。但很多人拍完片子在相機的顯示器里一看,竟然大呼奇怪。他們都忍不住抱怨起古鎮的不予“配合”,因為拍出來的片子看上去很不真實也很不和諧,就跟“P”上去的一樣,人與景兒之間你是你我是我地分離著、隔閡著,如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不同事件的硬性捏合。
相對于漂萍一樣去留無定的人們,似乎還是墻角、石階上的青苔與古鎮之間的關聯度更高,也更貼近、更默契、更和諧。它們就像古鎮從歲月深處呼出的翠綠、濕潤的氣息,絲絲裊裊地升騰纏繞在行人的腳邊。
而那些守候于客人門外或觀光必經之路,低聲細語或高聲叫賣的商販們,則是真正的當地人,他們常常以主人的身份向外出租和出賣著西塘。不知道經年累月的相伴與廝守,有沒有讓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擁有了與西塘心意互通的通道,使他們與西塘之間像葉子與樹一樣氣息與共,互為表達?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每天背靠著西塘,卻只把兩眼死死盯住如流水一樣川流不息的游客,一顆心不舍晝夜地懸掛于客人的背包和口袋之上。對于他們來說,西塘也不過是一個棲身和謀生的地點,是一扇木門、一面舊窗、一個懸掛招牌和鋪設貨攤的店鋪。
然而,西塘卻總會以自己的方式展開另一程的生命敘事。
水巷兩邊的老房子,別致的木質雕花窗,通常都是敞開著的。從窗外進去的是風和陽光;從窗里流溢而出或隱蔽著的是各種各樣的聲音、各種各樣的色彩、各種各樣的情感和故事。它們很輕易地就讓我想起被稱為“心靈之窗”的眼睛,而眼睛注定要成為某種內在與靈魂的流露與表達。不知道此時的西塘是醒著還是睡著。如果醒著,那么窗里的一切必定是它秘而不宣的心事;如果睡著,窗里的一切則是它夢里的內容。來西塘的人,大概也都與夢有些關系吧,他們不是來尋找自己的夢,就是來古鎮做夢。也不知道此時每扇窗背后的人們是醒著還是睡著。如果醒著,西塘則是他們未來的記憶;如果睡著,也許西塘就在他們的夢里。
于是,便有繾綣過后的情侶情不自禁地把自己的夢延伸到窗外。他們像一對蝶或一雙燕一樣,在窗前的美人靠上把風景依偎成夢幻。大約是為了印證一下那情景的現實性和真實性,他們開始用店家事先備好的釣竿去釣街溪里的魚。其實他們并不急于得魚,他們只是要讓那些幸福的時光如街溪水一樣緩緩地在西塘流淌。如果能夠偶爾從水中釣得一條或大或小的魚兒,那便是平靜的幸福中快樂與激情的象征了。果然,就有一條指頭大小的魚兒上鉤,搖頭甩尾地在水面上掙扎,他們笑著把魚線收回,小心將那魚兒存放在盆中,如存放一枚生動的記憶。然后,彼此交換一下眼神,重新消失在窗子的暗影之中。
水面很快就平靜下來。兩天后,也許這個曾經上演過甜蜜故事的窗后已經人去屋空。再以后,或長久虛置,或住進了一對足不出戶的老夫婦,而那窗前的水巷和擁有著這樣水巷的西塘,卻依然如故,仿佛什么都不曾存在,什么都不曾發生。
這夢幻般的細節,時間之水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讓我想起了短暫與永恒。如果僅從擁有時間的長度上論,我們之于西塘,正如蜉蝣之于我們。有時,人類躺在樹下睡一覺或醉一次酒的工夫,蜉蝣已經度過了它朝生暮死的一生。對于人類來說,一只蜉蝣的生而又死幾乎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當他一覺醒來的時候,并不知道曾有一個生命在他的身邊生而又死。對于蜉蝣來說,它的一生也許和人類一樣充滿了數不盡的起起落落和悲歡離合,充滿了道不盡的曲折復雜和豐富多彩。而人類卻如沒有生命的靜物一樣,在它的一生里幾乎一動未動。蜉蝣并不懂得人類的一個動作就能夠跨越它的半生,不知道人類能夠把它們所經歷的一切在時間的流程里拉長、放大,并演繹出更加驚心動魄的波瀾。它們沒有能力懂得人類,就像我們沒有能力懂得西塘。大象希形,大音希聲,人類中的智者隱約感知到了自身的局限,并對那些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超越者,進行了支離破碎的猜想和描述。
然而,雄心勃勃的人類,從來不甘于生命的短暫與幻滅,即便擁有了某個閃光的或意味深長的瞬間,也希求將其轉化成永恒。
無形的風掠過水面,正在搖櫓的船夫放下手中的櫓柄,伸手抓一把,風迅即從指縫間溜走。而微波興起的水,卻在這時記住了風短暫的拂摸,于是便心花怒放,讓菱花從水中開出來;菱花艷黃,如時光的莞爾一笑,開過之后就謝了,但在以后那些沉寂的日子里,那一泓多情的水,卻悄然把那次甜蜜的記憶,在內心醞釀成外表堅硬內在甜軟的菱角。與菱角相呼應的還有一種很奇特的水生植物叫做雞頭米或雞頭蓮,屬睡蓮科,花深紫而大,據說菱花開時常背著陽光,而芡花開時則向著陽光,所以菱性寒而芡性暖。不管怎么說,這一切都是短暫的,一切的發生、發展不過是一個季節的事情。但人類卻不甘心一切就這樣結束、消失。遂有人將菱角采來曬干后剁成細粒,以作日后備用口糧熬成粥,一邊食之一邊回想起那些逝去的光景。更有人將芡實采來磨粉,蒸熟,并傾注了自己的心力敲敲打打,制成了芡實糕。一種傳說中的美味小吃,一傳幾百年,名聲已差不多與西塘相齊。
人類就是這樣,把自己希望永久或永恒的愿望寄托于一切所經手的事物,通過物的傳承實現自身生命信息的傳承。我一直想不通,說不準,這是人類的理想、夢想還是妄念。
沿著一排排擺滿了芡實糕和煮田螺的攤子前行,總能夠在某一處房子的陰影中,看到一個只管低頭操作而無心叫賣、推銷的傳統手工藝加工者。有的在織粗布方巾,有的在用當地的一種木材加工梳子,有的則揮汗如雨,加工灶糖。有一位剪紙的老婦人,穿著灰色的布衣,坐在自家門檻外,專注地裁剪著手中折疊的紅紙,鮮紅的紙屑像是時光的碎片,撲簌簌落在她腳下的暗影中。當天色已經變暗時,我再一次路過她身邊,她仍然坐在原地未動,依然神情專注地剪著她心里的那些圖案,腳下的紙屑已經積了厚厚一層,并變成了暗紫色。這時,那老婦人已經與她身后的房屋融為一體,一同在黃昏里變得身影模糊,模糊成古鎮的一份記憶。
兩千多年歲月所成就的西塘古鎮,就這樣點點滴滴凝聚著人類世世代代的心愿和種種努力,但最后它卻無情地超越了多情的人類,成為一個冷峻、高傲的巨大背影,嚴嚴地擋住了我們探尋的目光。
莊子曾在《逍遙游》里描述過一種植物,叫大椿,據說它以我們的500歲作為自己的一個春秋,因為沒有人能夠親歷它的生命過程,所以就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它的壽命,沒有人確切地知道它的壽命,便也就沒有人知道它已經行進到了生命的幾分之幾。如果,我們如此這般地比擬、揣度西塘,那么我們同樣不知道它到底處于生命進程的哪一個階段。
在那些與西塘日夜相伴的日子里,我一直主觀地認為,西塘就是一個年輕俊美的女性。在夜晚的靜謐之中,側臥于水巷邊的客棧床上傾聽西塘,仿佛就能夠清晰地感覺到她那年輕而柔媚的呼吸。倏然,有一半自水一半自花的暗香越過半合半開的窗,長驅直入,直抵枕邊,半夢半醒之間,西塘似乎真的就幻化為了最心愛的女人,陪伴身旁。持續的溫情如窗前沐浴薰風的樹,沙沙地徹夜搖動不停,不但有聲,而且有影,激活了生命里所有的渴望與想象。
眩暈中,我曾一遍遍追問西塘,那個關于時間和永恒的秘密,但西塘始終沉默不語。我揣度,深諳天機的西塘,是不會向我開口的,一開口,便觸犯了天條,也會和我一樣墮入紅塵,在時光的洗滌中慢慢老去。
夜一定是很深了。從環秀橋的方向突然傳來一個神秘的聲音,像搖櫓,像鳥鳴,也像一聲訕笑。突然的驚醒,讓我很快意識到,夜色中,真實的西塘,離我已經更遠了,遠得不可觸及。環秀橋外一閃即逝的那個背影,到底是傳說中多情而委婉的胡氏,還是執著而羞怯的五姑娘?清麗而又有一點兒曖昧的西塘,到處都是新鮮或陳釀、熱烈或凄婉的愛情與傳說。但那一刻我卻感覺到,那似有似無一閃而逝的影子,正是西塘刻意躲閃與回避的身影。
清晨起來,我站在客棧窗前,久久地凝望著古鎮上的一切,內心感念叢生。無法收束的目光涉過水巷,跨過永寧橋,沿煙雨長廊向前,像撫摸自己的前世今生一樣,一直抵達送子來鳳橋。
有一對早起的戀人,攜手相依,正從來鳳橋頭幽暗的巷口走出,兩張甜美的臉在初升陽光的照耀下,像花兒一樣明艷、燦爛,我想,也定如花兒一樣芬芳。他們一路徜徉,一路纏綿,在靠岸的烏篷船邊悄聲私語,在滴水晴雨橋畔相擁而立。一方艷麗的土布披肩如他們借以飛旋的翅膀,一路把西塘演繹成一個故事里的模糊背景。一時間,竟讓我忘記了關于永恒這個話題的追問與思量。當他們在永寧橋欄上端坐拍照,相擁而笑時,突然有些許的震撼與感動擊中了我的心。當那庸常的快樂與幸福,能夠被一個人銘記,被古鎮銘記,被時間銘記,我知道,我已經沒有什么必要再去追問那個叫作永恒或永遠的字眼兒了。
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表情是什么樣子。但那一刻,我恍然而悟,我們之所以看不清西塘,是因為我們身在西塘;我們之所以猜不透西塘的心思,是因為我們就是西塘的心思。
薰衣草
這是第三個連晴日。
在英國,一年中透晴的日子加在一起也不會超過30個,所以這樣連續地晴,就會讓人感到有一點奢侈,好像把不多的一點兒積蓄集中在這幾天揮霍了。如果不是天氣而是人類,大概只有在節日里才能夠這樣慷慨吧。在這一點上,全世界的人都擁有著共同的稟賦,吝嗇,往好聽的方向說,是節儉。但不論如何,這幾天于英國人于我,都是比節日還難得的好日子。
對英國人來說,雖然每年的節日也不算多,但那些日子終究會如期而至的,該來時必然要來,像盡義務一樣。時間久了就習以為常,不必驚喜,也不必感激。但天什么時候晴或什么時候陰,可不會隨人們的意愿而改變,那得老天說了算,只有老天高興時才能晴,也只有老天非常高興時才可以連晴,那就注定了英國的晴天比節日來得不易。這一點很好理解,如果自己的老婆在家里給自己做一頓飯,那是正常的,理該如此,自然不必感謝;但如果是別人家的老婆在百忙中為你準備了一頓飯并無圖謀,只是因為你需要有人幫助。那么,不管是誰都會覺得那女人真的很偉大,圣母瑪利亞一樣可愛,豈止要感謝,還要崇敬呢。
對于我來說,這些天就更比節日珍貴了。許多年以來,一直也沒有機會和女兒朝夕相處,一起做一些喜歡或不一定喜歡但是需要做的事情。哪怕是為了一些小事兒爭論爭論,和她一起吵吵嘴、生生氣也好。最起碼,想看到她的時候一抬眼就能夠看到,想聽她說話時,召喚一聲就會有回應。突然就能夠和她在一起,并且大部分時間是和她沒有阻礙、沒有干擾地單獨在一起,這豈不是比過節還值得珍惜的事情嗎?
女婿浩提議,這么好的陽光,應該開車去農場看薰衣草。于是我們三個人懷著陽光一樣的心情,笑逐顏開地上了路。如果時光倒退幾十年,倒退回小學時代,為了這樣一份好心情,需要寫一篇應景作文向老師交差,我想我都會毫無怨言。
為什么要去看薰衣草呢?女婿浩從小在倫敦長大,平日里應該很少到鄉下,對于薰衣草大概也是聽得多見得少,偶爾想起這個世界級的“大明星”可能也是情系之,心往之,想看個新奇。另外,浩雖然生在中產階級家庭,但并沒有像中國的富家子弟一樣養成好吃懶做的習慣,他基本上一切都不依賴父母,不但讀書刻苦,生活方面對自己要求也很嚴格。一邊在公司工作,一邊還要利用業余時間攻讀注冊會計師,日子過得忙碌而清苦,很少有時間到處游逛。和女兒從戀愛到結婚這幾年時間里,兩個人也始終沒有一起去看過薰衣草,不知道兩個人以前有沒有過這方面的約定和計劃,但借陪我的機會,也算是做了一件與愛情有關的事情吧。
其實,薰衣草一直就與愛情有關。特別是這幾年,通過媒體和網絡,全世界到處都在流傳著普羅旺斯、普羅旺斯的薰衣草和與薰衣草有關的美麗傳說。其中有一則是這樣講的:從前,有一位普羅旺斯少女在采花途中偶遇一位受傷的俊俏青年,少女一見傾心,將青年人留在家中療傷。痊愈之日,深愛的兩人已無法分離。由于家人的反對,女孩準備私奔到開滿玫瑰花的愛人的故鄉。臨行,為檢驗對方的真心,女孩依照村中老奶奶的方法,將大把的薰衣草拋向男青年,突然間紫色輕煙升起,男青年隨之不見,只留下一個隱約而神秘的聲音——“其實我就是你想遠行的心”。不久,少女也隨著輕煙消失,兩個人共同融化在愛情之中。從此,普羅旺斯,法國南部一個不起眼兒的小鎮便成為薰衣草的故鄉,也成了愛情的故鄉或代名詞。
然而,我所知道的事實是,薰衣草,作為一種傳統香料,它的歷史遠比普羅旺斯和普羅旺斯的愛情更加悠久。這種開有紫藍色小花的芳香植物又被人們稱為靈香草、香草、黃香草,其英文名為Lavender。早在羅馬時代就已經普遍種植,原產于地中海沿岸、歐洲各地及大洋洲列島,后被廣泛栽種于英國及南斯拉夫。
在英國,早在伊莉莎白時代就有“薰衣草代表真愛”的詩意表述。因此,當時的情人們流行著將薰衣草贈送給對方表達愛意。而在這方面,英王室也是作出表率的,據說查理一世在追求Nell Gwyn時,就曾將一袋干燥的薰衣草,系上金色的緞帶,送給心愛的人。
比較而言,法國的薰衣草比英國的薰衣草,香味更濃烈,更具有提神作用;而英國的薰衣草香味較淡,起到的是寧神的作用。這倒有一點一方水土一方人的意思。法國的薰衣草在特性上竟然和總體上浪漫、激情的法國人一脈相承;而英國的薰衣草卻與英國人一樣偏于保守、穩健、優雅、理性。
我們要去的農場在距倫敦并不很遠的薩里郡的小鎮班斯蒂德,據說這里種植薰衣草的歷史已有300年之久。薰衣草正常的收獲季節大約應該在七月末八月初的樣子,但對于這點我們并不是很了解,所以我們去的時候,收獲季節已過去一個多月,已經看不到想象中的紫藍色花海。
這時,田野上的麥子已經收割完畢,只留下一片平整的麥茬,遠遠看去仍然顯現出一片金黃,而近處采摘過的薰衣草田卻顯得有一些灰頹,除了少數田壟上仍有一些新生的淡紫色花穗,大部分田壟呈現出令人失望的暗灰色。有的是因為花穗被采摘之后,只留下了那些小灌木的枝葉,有的則是因為還沒有采摘的花穗變老變暗失去了原有的色彩。但當我們走進薰衣草田壟時,仍然有陣陣濃郁的香氣撲鼻而來。原來,這薰衣草竟是一種很奇特的植物,并不像一般的花草,青春逝去便芳華盡散。當它們顏色褪去后,便是最成熟的時候,這時會比以往更加芳香濃郁,更加令人沉醉。說來,這也正是人類中某一些人刻意追求的美好境界呢。
薰衣草的靈魂,就是它的香。人們先是沉醉于它的香,然后才喜愛它的色,否則光憑借它的顏色也不至于令人們如此迷戀。但人們的不良習慣就是太依賴眼睛,用眼睛替代一切感官。應該聽的,我們要用眼睛去看;應該觸摸的,我們要用眼睛去看;應該用鼻子聞的,我們仍然要用眼睛來判斷。久而久之,我們除了動用眼球就不再有別的評判能力,不管是什么事物,只要不能夠吸引“眼球”,我們就不聞不問,就嗤之以鼻。在這個浮躁跟風的時代里,我們并沒有誰認真地想過這件事,但這樣下去的結果,遭受損失的正是搞不準真假虛實是非好歹的我們自己。
面對眼前那一大片薰衣草田,身心沉醉于它的芳香之中,遂想起那句薰衣草的花語:等待愛情。一個“等待”便把愛情的本質和美學價值說穿。真正的愛情,往往并不是四處尋找和通過相親找到的,它要你耐心等待,等待那個機緣的來臨;真正的愛情,需要卿卿我我,但卻不能在卿卿我我中得到長久的延續,沒有等待、沒有思念的愛情會如沒有陽光照耀的花朵一樣日漸枯萎和凋謝;真正的愛情,往往就是在無望的等待中得以永恒,我們所熟知并深受感染的愛情故事,梁祝、孔雀東南飛、魂斷藍橋、廊橋遺夢等等,哪一個不是因為等待和將進入恒久的等待,才得以升華和感人至深的!真正的愛情,原來是如此的憂傷。
據說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還有這樣的傳說:當你和情人分離時,可以藏一小枝薰衣草在情人的書里,當下次相聚時,再看看薰衣草的顏色,聞聞薰衣草的香味,就可以知道情人有多愛你。對于這件事兒,我是這樣理解的,按照自然規律,每一對真心相愛的人,都在共同經受著歲月摧折,總有一天會容顏老去,如眼前這一壟壟暗淡無光不再鮮艷的花穗。但所有的真情和真愛,一定不會因為時間的改變而變淡,它應該像老去的薰衣草一樣,時間愈久芳香愈濃。
下午的陽光依然強烈,強烈得讓人睜不開眼睛。但如此強烈的陽光卻仍然不能讓我感覺心情開朗,因為我還不能及時從薰衣草以及愛情的主題里抽出思緒。望著那些秋天里的薰衣草,我仿佛望著鋪滿秋天的愛情,并且深深地意識到,世界上最憂傷的顏色并不是那種如煙如霧如夢的紫色,而是比那紫色更深更暗的深灰,那是等待的顏色,是比地老天荒更讓人心疼的顏色。
責任編輯 王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