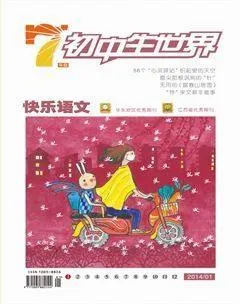土洋結合的中國標點符號
中國標點符號的完善與廣泛使用,不過一百年的歷史,而且是“土洋結合”的產物。老祖宗最早的書面語言是沒有標點符號的,不但閱讀困難,而且不易理解意思。
秦漢時,開始有了“離經辨志”讀書法,據漢、唐兩位經學大師鄭玄、孔穎達的解釋:離,指斷句;經,指儒家經書,是說讀斷經書文句,理解圣賢志向。可見當時的讀書人已有分章斷句的意識,但還沒有相應的符號。
到了唐代,有人開始用“圈”和“點”標讀文章,叫做“句讀”,又叫“句逗”。具體用法是:文詞語意已盡處用“圈”,相當于現在的句號;語意未盡而應停頓處用“點”,相當于現在的逗號。當時的“圈”與“點”,主要標在啟蒙讀物上,便于兒童閱讀與理解語意,對此,文學大家韓愈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句讀之不知, 惑之不解。”到了明朝,又新添了在人名旁畫上單線,地名旁畫上雙線,即現在所說的“專名號”。
雖然唐代就已有了句讀,但一直停留在初級階段,與現在應用的標點符號相比,數量上只是其中的幾分之一,遠不能用來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的性質和作用,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靠著有識之士大膽地“洋為中用”“土洋結合”,方才得以大改觀。
近代以來,隨著西學東漸,歐美的標點符號也到了中國,第一個介紹國外標點符號者,是清廷外語學堂“同文館”的學生張德彝,他學的是英文。
同治七年(1868年),張德彝以“辦理中外交涉使團”翻譯的身份訪問歐美。其間他記錄了在西方世界的所見所聞,意在讓國人開眼界、長知識,特別是中國沒有的事物,如蒸汽機、縫紉機、巧克力等,其中的一項便是標點符號。他在名為《再述奇》的游記里寫道:泰西各國書籍,其句讀勾勒,講解甚煩,如果句意義足, 則記“。”;意未足,則記“,”;意雖不足,而義與上句黏合,則記“;”;又意未足,外補充一句,則記“:”;語之詫異嘆賞者,則記“!”;問句則記 “?”;另加注解,于句之前后記“()”;又于兩段相連之處,則加一橫“——”。
張德彝介紹的西方“句讀勾勒”,引起了學人的注意與興趣,感覺用來表示停頓、語氣以及詞語的性質和作用大有益處。
1897年,有個叫王炳章的廣東東莞學人,取中國原有的“圈”和“點”,及西文中的“句讀勾勒”,草擬了10種標點符號。由于合乎實用而被人接受, 胡適、陳獨秀、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著名教授、作家均表歡迎并應用。1916年8月,胡適應《科學》雜志之請,編寫了《論句讀及文字符號》一文,就句讀及文字符號作了心得之談。
“五四”以后提倡白話文,標點符號被應用于書報雜志,只是因為沒有“法定”,用法不盡統一,還有人不接受。據說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使用了標點符號,出版后贈送國學大師章太炎一冊,扉頁上工工整整寫了“太炎先生指謬”,下署“胡適敬贈”,兩人姓名旁各加了專名號——黑色直線。
不料章太炎看到自己名字旁畫一黑杠,勃然生怒:“何物胡適,竟在我名下胡抹亂畫!”及至看到胡適的名字旁也有黑杠,才省悟到文字符號并非不吉的東西,方才消氣。
鑒于當時對標點符號的應用有擁護,有反對,使用中又各取所需,顯得混亂,胡適、錢玄同等六位教授在1919年4月間,向“國語統一籌備會”提交了《請頒行新式標點符號方案》。北京政府教育部予以批準,于1920年2月2日頒行了《通令采用新式標點符號文》,規定了12種標點符號及其用法。中國第一套法定的標點符號由此誕生,其用法合情合理,為大眾所認可接受。
(選自《文史博覽·文史》 2013年第10期,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