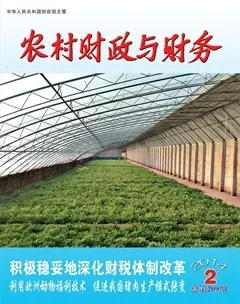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回顧與展望
黨的十八大的一個突出亮點,是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高度。而生態文明的內涵,主要包括了完善的生態制度、發達的生態經濟、先進的生態文化和良好的生態環境。進一步完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既是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加強森林資源保護的必要保證。
2001年,中央財政正式啟動了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試點工作。以此為標志,我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以下簡稱生態補償)制度從無到有、范圍從小到大、資金從少到多,經歷了不平凡的十二年。這期間,各級財政部門會同林業部門攜手共進,使我國公益林的保護和建設得到了極大加強,國土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獲得了有效保障,農民收入實現了穩步增長。201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對今后的生態補償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新一屆中央政府正引領全國人民走在建設美麗中國的光明之路上。站在2013年這重要的歷史交匯點,有必要深入回顧中央財政生態補償的以往歷程,及時借鑒地方財政生態補償的經驗,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制度。
一、政策回顧
1984年,《森林法》提出要建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1998年修訂后的《森林法》明確要求:“國家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用于提供生態效益的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的森林資源、林木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自法律明確規定之后,社會上對于要求國家盡快建立補償制度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為貫徹落實《森林法》,中央財政積極謀劃,多措并舉,建立并逐步完善生態補償政策。
(一)啟動補助試點。經國務院同意,2001年—2003年,中央財政每年預算安排10億元,在遼寧、河北、福建、廣西、山東、新疆、江西、黑龍江、湖南、浙江和安徽等11個省(區)啟動了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試點工作。試點總面積為2億畝,補助標準為每畝每年5元。補助資金用于重點防護林和特種用途林保護和管理費用支出。2001-2003年3年試點期間,中央財政累計安排補助資金30億元。補助試點工作的實施,促進了2億畝試點國家級公益林的管護工作,為正式建立生態補償基金制度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二)建立補償制度。在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試點的基礎上,2004年國家正式建立了中央財政生態補償基金。當年,中央財政預算安排20億元,按照每畝5元的標準,用于對全國4億畝國家級公益林管護者發生的營造、撫育、保護和管理支出給予補助,資金規模和補償面積比試點期間翻了一番。中央財政生態補償基金的建立,是繼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以下簡稱天保工程)、退耕還林工程后,中央財政支持林業發展又一重大舉措,標志著我國生態補償制度正式建立,結束了我國森林生態效益無償使用的歷史。
(三)不斷完善發展。“十一五”時期,中央財政補償范圍不斷擴大,補償標準適當提高,補償政策不斷完善。2006年,中央財政增加安排10億元,補償基金總規模擴大到30億元,全國28個省(區、市)、新疆兵團和軍事管理區的6億畝國家級公益林納入了補償范圍。2007年,繼續擴大補償面積,將湖南、廣西、新疆三省(區)尚未納入補償范圍的非天保區國家級公益林的有林地5784萬畝和吉林、黑龍江、甘肅、寧夏四省(區)補劃的國家級公益林有林地998.39萬畝也納入補償范圍,補償總面積達到6.68億畝,補償基金規模33.4億元。2008年,補償面積增加到6.99億畝,補償基金規模為34.95億元,增加的部分主要是西藏自治區非天保區公益林中的灌木林、管叢林、苗圃地等。2009年,中央財政大規模增加了補償面積和資金,將已區劃的非天保區國家級公益林和天保區新增造林全部納入補償范圍,補償面積達10.49億畝,補償資金達到52億元。根據中央林業工作會議有關精神,從2010年起,中央財政提高了國家級公益林的補償標準。國有的國家級公益林平均補償標準為每畝每年5元,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為每畝每年10元,2010年當年安排補償基金75.8億元。2011年,結合貫徹落實天保工程二期財政政策,將天保工程區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按照每畝每年10元的標準,納入中央財政補償基金。當年資金量達到96.8億元,納入補償的國家級公益林面積達到12.59億畝。2012年,按照新的國家級公益林界定結果,納入補償的面積達到13.85億畝,補償金額為109.3億元。2013年,中央財政又把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15元,全國總補償金額達到149.3億元。2013年補償金額大約是2001年建立之初的15倍。
中央財政生態補償基金制度的建立和發展,維護了公益林經營者、所有者的切身利益,對促進山區農民增收,轉變我國林業經營思想,促進公益林管護,實現分類經營等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意義。在取得成就的同時,還要清醒地看到,生態補償基金制度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如補償基金來源渠道單一,缺乏動態調整機制等。特別是補償標準偏低問題,是矛盾的焦點。盡管從2010年起中央財政適當提高了補償標準,但是廣大群眾、基層部門乃至社會各界要求大幅度提高補償標準的呼聲依然強烈。據初步統計,2010-2013年,由我部牽頭辦理的林業方面的人大建議和政協提案主辦件共計93件,要求完善補償制度、提高生態補償標準的主辦件達62件,占總主辦件的66.7%。因此,中央財政應盡快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勇于開拓創新,以更寬的思路、更大的力度,進一步完善生態補償政策。
二、地方生態補償經驗
十幾年來,各地財政部門按照“各級政府要建立和完善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制度”的要求,加快建立健全生態補償制度的腳步。據初步統計,各地已區劃并實行生態補償的地方公益林共5.24億畝,其中省級公益林4.02億畝,省級以下公益林1.22億畝。各地在推進補償制度過程中,注重創新機制,多渠道籌集資金來源,逐步提高補償標準,不僅有力地推進了本地區公益林的管護,而且為中央財政完善生態補償政策提供了寶貴經驗。其中具有代表性是以下八個省(市)。
(一)北京市。從2010年開始,北京市建立了山區生態公益林生態效益促進發展資金,標準為每畝每年40元,其中24元為生態補償資金,16元為森林健康經營管理資金。根據山區生態公益林的資源總量、生態服務價值、碳匯量的增長情況和全市國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北京市將合理核定生態效益促進發展資金增加額度,每5年調整1次。資金來源,生態補償資金由市、區(縣)財政按1∶5的比例共同負擔;森林健康經營管理資金全部由市財政負擔。
(二)福建省。從2006年起,福建省根據城市工業用水和生活用水量,綜合考慮各地公益林數量及其對流域的貢獻大小和經濟發展水平,按每年每噸用水量承擔生態補償金0.1元、0.05元、0.06元三種標準籌集生態補償資金的來源,期限為三年。2010年,福建省繼續推進多渠道籌集補償資金工作。在上述政策的作用下,全省共籌措生態公益林補償資金12910萬元,使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均達到每畝每年12元。此外,廈門市財政在省財政每畝每年12元的基礎上,再按12元的標準安排補償基金,達到24元/畝。晉江市在福建省、泉州市(2元/畝)安排補償基金的基礎上,本級財政再增加安排補償資金5元/畝,達到了19元/畝。
(三)廣東省。廣東省較早地建立了森林分類經營體系,2003年的補償標準即達到每畝每年8元。從2008年起,每年遞增2元,2011年已達到16元/畝。對于本省的國家級公益林,廣東省每年從東深供水工程水費收入中安排1000萬元,用于東江流域水源涵養林建設,將國家級公益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再提高1元,達到17元/畝。廣州市財政統籌安排省、市補償資金,2008年的補償標準達25元/畝,2009年達39元/畝,2010年達41元/畝。東莞市在中央、省、市三級財政資金的基礎上,縣級財政再拿一部分,2008年補償標準已達到100元/畝。
(四)江西省。從2006年開始,江西省按照中央財政的補償標準建立了地方生態公益林省級補償機制。2007年將補償標準提高到6.5元/畝,2008年補償標準達到8.5元/畝。2009年,全省公益林補償標準統一提高到10.5元/畝。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江西省2011年生態補償標準將達到15.5元/畝。
(五)江蘇省。江蘇省2002年就建立了省級生態補償制度,當年補償標準為每畝8元。2008年國家和省級森林生態效益補償標準均提高到每畝10元,2009年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15元,2010年補償標準提高到每畝20元。
(六)浙江省。浙江省從2004年起建立了地方生態公益林補償制度。補償標準為每畝8元。近年來,浙江省生態補償標準不斷提高,達到每畝17元。
(七)安徽省。安徽省從2003年起建立了省級生態補償制度,2010年補償標準達到每畝10元。銅陵市在中央和省級財政補償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標準:國家級公益林補償標準達到每畝19.25元,省級公益林補償標準為每畝17.25元,市級公益林補償標準為每畝11.5元。
(八)四川省。成都市從2010年起,對集體公益林地按每畝30元的標準安排補償基金。成都市大邑縣從風景名勝區的門票收入和部分育林基金中,再統籌安排,將補償標準提高每畝10元,達到每畝40元。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地方財政生態補償工作成績比較突出的地區,一部分是經濟比較發達,財力比較雄厚的地區,如北京、廣東、江蘇等;一部分是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比較深入,推進生態補償的決心和力度比較大的地區,如江西、安徽等。地方財政的生態補償實踐經驗,對完善中央財政生態補償政策帶來了兩點啟示。一是要高度重視生態補償工作。凡是重視程度高的地區,不論財力如何,都能有所作為。二是要建立完善的生態補償制度是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三、未來展望
(一)建立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合理的生態補償標準究竟是多少?目前,各界看法不一,歸納起來大致分為以下三種觀點:第一種是按照生態效益價值核算的標準。理由是:顧名思義,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的標準應按照森林發揮的多種生態效益的價值來核算。這些效益既包括傳統概念中的凈化空氣、涵養水源、防風固沙、保持水土等,也包括熱門概念中的林業碳匯。近年來,國家林業局在探索生態效益價值核算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實踐中運用的案例較少。第二種是按照機會成本,也就是公益林能夠產生的經濟效益價值核算的標準。理由是:對集體和個人所有者或經營者而言,被界定為公益林后,僅發揮生態效益而喪失了經濟收益。因此對公益林所有者或經營者的補償標準應當以能夠產生的經濟收益來核算。目前,在集體林權制度改革比較深入的地區,這種呼聲很高,但是所列標準缺乏科學的依據,隨意性很大。第三種則是將前兩種觀點折中,對兩套價值核算方式賦予一定權重再加權平均。這種觀點還停留在探索構思層面。但是,不論哪一種觀點,各方形成的共識是:補償標準首先要能滿足營造、撫育、管護的成本。以此來比較,目前的中央財政生態補償標準還有較大差距,而且近年來物價和工資上漲迅速,補償標準與實際成本的差距越來越大,迫切需要盡快建立補償標準動態調整機制。
建立補償標準增長機制,要從三個方面著手。一是高度重視生態補償工作。一方面,這是地方經驗帶來的啟示。例如,江西省的財力與東部沿海省份有相當的差距,但是省委、省政府長期以來高度重視生態補償工作,在預算安排上始終傾斜,以致江西省生態補償的標準已接近了浙江省。另一方面,生態補償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林業財政政策的亮點。隨著天然林資源保護工程二期政策的逐步落實,以及新一輪退耕還林財政政策的基本成型,作為林業財政政策三大支柱之一的生態補償政策,應當作為林業財政工作的抓手,下大力氣抓緊完善。二是將補償標準與財力增長適度掛鉤。中央林業工作會議明確要求,中央財政生態補償標準,隨著國家財力的增長適當提高。“十一五”時期全國財政收入年均遞增21.3%,五年增長一倍多。如果“十二五”時期財政收入增速保持不變,且補償標準與財政收入僅同比例增長, 2015年中央財政生態補償標準(集體和個人所有部分)應達到每畝每年20元。三是加強績效評價工作,建立以獎代補機制。中央財政生態補償基金作為績效評價試點,納入我部地方專款績效評價工作統一的部署。建議抓好績效考評工作,在指標設計上分別突出生態保護工作與地方投入力度,并以此為依據,建立中央財政生態補償獎補機制。即在逐步提高補償標準的前提下,中央財政適當集中一部分公共管護支出,用于對生態保護突出、地方重視且投入大的地區予以獎勵。
(二)多渠道籌集補償資金。根據《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推進集體林權制度改革的意見》(中發[2008]10號),要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機制。當前,生態補償資金來源渠道單一,基本靠財政預算,這也是補償標準偏低的重要原因。下一步,建議從直接補償和間接補償兩方面著力推進多渠道籌集補償資金的工作。
1.直接補償。所謂直接補償,是受益者與補償對象之間不經過中間方的補償。地方財政這方面已經有了成功先例。在省域內,福建省的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受益大戶,按照用水量對水源涵養地的南平、三明、龍巖等地安排了生態補償資金;在省際間,廣東省擬對東江水源地的江西省給予生態補償。目前省財政已預留資金,擬于年內啟動實施。因此,對于中央財政,要借鑒經驗,抓住時機,大力推進直接補償工作。根據“十二五規劃綱要”中“鼓勵、引導和探索實施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生態受益地區對生態保護地區的生態補償”的要求,建議由國務院牽頭,先從全局性的大江大河入手,組織下游省(區、市)對上中游省(區、市)進行生態補償。一是我國大江大河下游多是經濟發達、財力雄厚的地區。在生態觀念深入人心的今天,有條件也有義務開展生態補償。二是開展大江大河上中下游之間生態補償的時機已經成熟。不久前,江西省要求建設鄱陽湖綜合水利樞紐工程的消息引發了熱議。面對經常性的旱災,這一工程的目的是要把寶貴的鄱陽湖水留在江西省內。目前,這場爭論未有定論。有專家預測,鑒于鄱陽湖全局性的生態價值,國務院可能不會同意江西省的建議,但考慮到江西省的實際困難和所做貢獻,可能給予某種形式的生態補償。
2.間接補償。所謂間接補償,是受益者與補償對象之間通過第三方統籌安排的補償。目前,生態補償基金由公共財政預算統一安排的做法,已經是間接補償方式之一。但是這種方式缺乏政策導向性,至少補償者(生態受益者)難以意識到在進行生態補償。建議從稅收和收費兩方面加強間接補償工作。一是稅收方面。結合正在研究完善的資源稅、環境稅政策,明確按一定比例提取資金,用于生態補償工作。二是收費方面。進一步改革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復費,將其用途明確為生態補償。由于各種歷史原因,育林基金等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偏離了設立的初衷,普遍成為養人、養機構的資金,迫切需要改革。完善生態補償制度,為育林基金和森林植被恢復費政策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三)抓緊研究相關林業政策,從而更好地推動完善生態補償制度。除建立補償標準增長機制、多渠道籌集資金來源外,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研究相關林業政策。一是在國有林與集體和個人林混合交錯的地區,用國有的商品林置換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公益林。通過改變公益林的權屬性質,既能滿足群眾的經濟訴求,又保持生態功能。但是,這項措施對條件要求比較苛刻,且必須規范操作。二是完善和落實林木采伐管理政策。對于南方部分水土光熱條件較好、林木生長較快、生態地位較弱的地區,公益林不應絕對禁止砍伐。2013年4月,國家林業局聯合財政部印發了《國家級公益林管理辦法》(林資發【2013】71號),其中第十六至第二十條針對一、二、三級國家級公益林的采伐管理,分別做了既嚴格又符合實際的規定。林業部門要抓緊落實上述規定,使得國家級公益林在有效保護下求發展。
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五位一體的戰略高度,標志著我們的黨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規律、自然資源永續利用規律和生態環保規律的認識進入了新的境界,為提升發展提供了高瞻遠矚的指導。生態文明既是對傳統發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又是對未來永續發展的美好憧憬。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制度作為生態文明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將以《森林法》為依據,在財政和林業部門,以及社會多方面共同努力下,成為保護我國森林資源的一項永久性的制度,發揮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作者單位:財政部農業司林業處)
責任編輯:宗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