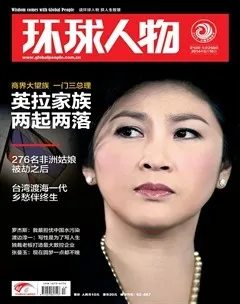“士”何以出游?

士原來是西周貴族的最低一層,但到了東周戰國,這種身份越來越不固定和明確,“士”和上層貴族如“卿大夫”的界限也越來越不清楚,或至少很容易越過。而且,隨著武士向文士的轉變,隨著孔子興辦私學、“有教無類”理念的廣泛傳播,“學”越來越不在官府。而有“學”或只是有一特殊“技藝”即可成“士”,如此一來,“士”越來越多地擺脫了身份血統的約束,而完全可以通過個人后天的努力來達到。于是,“士”也越來越像是一個泛稱,泛指那些有一定學問或才華,對思想或政治有興趣和才能的人們。這些人在社會上自然仍是少數,但是,他們的來源和功能則相當廣泛。
所以,戰國時代泛指的“士”,往上數可以包括過去的卿大夫子弟乃至宗室的流落公子,往下數可以包括各種社會職業出來的人們,甚至包括那些暫時隱于“挽車屠狗者之流”的人們。但也不是說什么人都是“士”,“士”還是與社會上穩定地從事生產和交換的“農工商”迥然有別,可以和一般的“民”或“勞力者”相對而稱;“士”還是具有政治性或觀念性的階層,是社會中一個“活躍的少數”。
總之,“士”是一個廣泛的概念,但也有其確定性,這一確定性主要是相對于兩個方面來說的:第一是與之相對而言的、身份比較固定的多數農工商生產者;第二是同樣身份比較固定的少數宗室貴族。但是,如果宗室貴族也不得不背井離鄉,或者農工商生產者也嘗試改變身份,他們也就都可被稱為“游士”了。
士之出游有時是為了道義,如孟子說:“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這是因為不愿待在不合道義的本國了。還有的時候,出國則是因為要尋找合適之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或者為了扶危濟困的道義。如果本國是一個小國、弱國,或者恰恰宗室當政,又或是與執政者政見不合,在本國往往會受到限制,到他國卻可能更有機會。他們不是沒有故國之思,但同時還有一種天下興亡意識和個人政治抱負。此外,也還有為了避世的游走,為了逍遙的游走,為了生計的游走。當時諸侯國甚多,“東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國君的任用,還有公子的養士備用。所以士人游走的空間是相當之大的。
“士”不為一世家所有,也不為一國家所有,甚至自身的家族意識也相對淡薄,戰國時代的“士”大概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自由,也最有個性的士人,或可說成一個沒有階級意識的“客觀階級”,一種無組織的巨大“組織力”,甚至憑其三寸不爛之舌便能調動千軍萬馬,或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尤其那些縱橫之士,就像是職業外交官,而他們所擁有的權力遠遠超過當代那些往往只是本國政府傳聲筒的外交官。其職業倫理有時似乎還勝過其愛國之心或忠君之心。還有像同時為數國之相,或者今天在這一國為相,明天又到另一國為相的現象,都可以說是現代國家中不可思議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