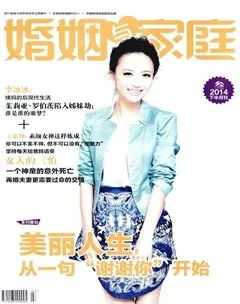二馬的戰爭與和平
搞教育的朋友跟我說:男孩子,當他意識到自己是男人時,都無可避免地會與父親來場“真槍實彈”的沖突……
戰爭
周五。晚9時45分,老馬和小馬敲門。
“回來啦!”“嗯,回來了。”二馬如常應答。我榨好果汁,剛走到客廳就聽見激烈爭吵。我跨進書房,二馬正臉紅脖子粗,四目怒視,眼看要發生肢體沖突。
“哎呀,剛才好好的,轉臉就雷聲滾滾,鄰居都休息啦。”我邊說邊拉走小馬,關嚴書房門,先隔離。
“學了一周,放松下不行嗎?”小馬一屁股坐到床上,氣憤又委屈。“我一首歌還沒聽完,他就催了兩次,我心煩,說‘快不了’,結果他一下子就把電腦關了,太不尊重人了!”估計是小馬的態度激惹了老馬的情緒,但這茬先不提。我只贊同地說:“嗯,爸爸有點過分。”“不是有點,是太過分了!我忍他不是一年半載了!”小馬滿臉怒氣一腔憤慨。“喲,潛伏期還挺長,可以做特工了。”我笑著調侃,小馬翻翻眼睛沒理我。
我稍微停了停,語調緩慢地說:“這個吧—要從一個人的生長環境來看,你看爸爸和姑姑們在爺爺面前是不是很順服?”“嗯。”“老馬家的家風就是長輩有絕對權威,小輩完全服從,所以,爸爸不能容忍你態度差。”“我一次態度差他就不能容忍了,他總居高臨下教訓人,我還無法容忍呢。”“對,人人都有不能容忍觸碰的軟肋,彼此間發生摩擦也正常,只要相互多寬容理解,矛盾會慢慢化解的。”“我和他的矛盾沒法化解,他不講理。”小馬執拗地說,但情緒已經不像剛才那般激憤,音調也降了下來。
“確實,爸爸不民主不講理,你既然這么了解,就別跟他講理了,咱們今晚不理他。”抬頭看看鐘,快11點了,我拍拍小馬的背,轉移了話題。
安撫了小馬,去看老馬。他正沉著臉抽煙,我趕緊八卦了會兒足球和彩票,老馬臉色漸漸緩和。我打著哈欠往外走:“困了,先睡了。”門口處轉回身,不經意地說:“對了,小馬現在長大了,以后咱倆不能再把人家當小屁孩兒了。”大男人愛面子,點到就好。
僵持
周六。
小馬有了難題,平時,他那套大校服都是老馬手洗的,現在當然沒法張口了。餐桌上,二馬做不識狀。飯后,小馬“吭哧吭哧”地把校服搓洗了,看起來累得夠嗆。
午后,小馬因順暢做出兩道壓軸題,精神明顯振奮了。我借機問:“生活,有時也不錯,是不是?”“是。”“可你倆昨晚的架勢,很有種魚死網破的感覺。”“嗯,昨晚大吵那會兒真想跟他拼了。”
“沖動是魔鬼啊,以后要學著控制情緒,不成熟的人才動不動就跟人拼呢。”“呵呵。”小馬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實,有些細節你可能沒在意,以前爸爸習慣晚飯后去泡三四小時澡,自從你有晚課,他都不泡澡了;他還推掉不少應酬,爸爸挺在意你。”“哦,是吧。”小馬猶疑地應著。“有時,爸爸加完班七八點了,還餓著肚子去接你。”“嗯,是。”這次小馬口氣肯定了。“爸爸常跑老遠買你愛吃的面包,為了新鮮,總現吃現買,不嫌煩。”小馬沒吱聲,臉上現出慚色。我趁勢小結:“當別人不小心對我們做了錯事后,我們要多想想他對我們做過的好事。”小馬微低著頭默默靜聽著。
晚上,我問老馬何時能恢復邦交,他悶聲答:“順其自然。”
顯然,盡管情緒都平復了,但打破僵局,還需契機。
和平
周日。冷戰進行中。
我問小馬:“明天周一,面包怎么辦?”“在樓下面包店買。”“你倆何時能對話?”“明早再說。”忽然間,原先那個愛依賴、常常沒主意的孩子就長大了。看來,父子危機也可成為孩子成長契機。
傍晚,老馬出去了一趟,回來時手里拎著袋面包,小馬看到了,眼里一亮,但沒說什么。
老馬往冰箱里放面包時,發現冰箱里漆黑一片。“冰箱壞了嗎?”“不能吧,剛才還好好的呀。”我答。“燈不亮了,也不制冷了。”“是不是插排壞了。”我邊說邊找出個新插排換上,依然不亮。老馬把冰箱拉出來,想卸后蓋,但只找到把一字螺絲刀,而冰箱上的螺絲是十字形。正撓頭呢,小馬無言地遞來個木盒,里邊齊全地碼著各式螺絲刀頭。
父子倆搭著手卸開后蓋,看來看去,啥毛病沒有。“再插上電源試試。”我把電源插上了,“咔噠”一聲響,冰箱竟然啟動了。“莫名其妙啊!”二馬瞪著眼,詫異對望。然后,我聽到了簡短對話:“爸,你給我買面包啦?”“嗯,買了。你這套工具不錯啊!”“那是。”僵局打破了。
矛盾化解不好,就會成為洪水猛獸,讓親情疏離,還會在孩子心靈留下傷痕;化解好了,父子會更了解對方,他們的關系也會升華。
現在,老馬對小馬少了命令、多了尊重;小馬對老馬少了不滿、多了理解,父子相處得特別融洽,甚至讓我有點小嫉妒。我一直忍著沒說—其實,冰箱的“莫名其妙”是我鼓搗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