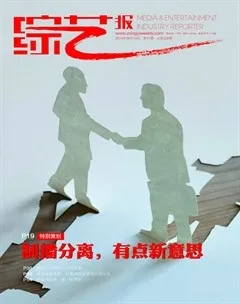《寶貝兒回家》影視“打拐”的現(xiàn)實(shí)重量

抗戰(zhàn)劇與都市劇的二重奏,似乎讓眼下的國(guó)產(chǎn)電視劇陷入了單調(diào)的格局中。作為一部極富現(xiàn)實(shí)意義的作品,5月31日獻(xiàn)禮“六·一”于山東衛(wèi)視首播的《寶貝兒回家》,算是近期熒屏一次頗有新意的題材探索。
《寶貝兒回家》取材自秦艷友、張寶艷夫婦自費(fèi)創(chuàng)辦公益尋人網(wǎng)站“寶貝回家尋子網(wǎng)”的真實(shí)事件,以陶紅、董勇演繹的“尋子父母”找尋丟失的孩子為主線,還原了孩子被拐賣后一個(gè)家庭的破碎與苦痛,以及尋找孩子的千般艱辛、萬(wàn)般絕望。它以一個(gè)失子家庭為窗口,透視著中國(guó)社會(huì)對(duì)“打拐”的審視與呼喚。
《寶貝兒回家》看似尋常的人物設(shè)定、故事背景,卻因?yàn)椤按蚬铡钡默F(xiàn)實(shí)映射讓作品變得格外揪心與抓人。一貫以“親和大姐”與“錚錚硬漢”亮相影視劇的陶紅、董勇,一改往日熒屏形象,在劇中飾演一雙苦苦尋子而不得的苦難夫妻。丈夫啟明在水族館里無(wú)意中丟失了四歲的兒子琪琪,妻子小曼絕望又堅(jiān)定地踏上漫漫尋子之路。過(guò)程中,夫妻倆創(chuàng)辦了“寶貝兒回家網(wǎng)”,通過(guò)網(wǎng)站幫助被拐賣的兒童回家。
以往的諸多國(guó)產(chǎn)電視劇,很大的弊病在于沉溺于理想的人、情、事中難以自拔,更難以觸發(fā)觀眾的情感共鳴。題材與內(nèi)容的浮躁,大多讓人觀后即忘。而電視在社會(huì)文化傳播中的“涵化功能”,恰恰說(shuō)明了電視對(duì)人的塑造作用是極為深刻的。《寶貝兒回家》的“公益性”難能可貴,但其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遠(yuǎn)不只體現(xiàn)在題材的現(xiàn)實(shí)性上。《寶貝兒回家》在每一集片尾都會(huì)有一段真實(shí)的尋親信息。劇組在拍攝過(guò)程中接待了諸多打拐志愿組織,拍攝了48個(gè)家庭的尋子信息,這期間也確實(shí)有離家十年的孩子被找到。承載著“公益”與“親情”兩大砝碼的劇集,平視了“打拐”這一日趨顯著的中國(guó)社會(huì)問(wèn)題,讓作品在講故事的同時(shí),更多的作為一個(gè)容器,裝下社會(huì)寄托和期待,并在一定程度上幫助這一社會(huì)群體。這樣的作品,貴在真實(shí)自然,不刻意煽情催淚,人性中的悲天憫人能夠涓涓流淌,撼動(dòng)人心。
顯而易見(jiàn),《寶貝兒回家》是具備一定現(xiàn)實(shí)重量的。看似還原一個(gè)失子的普通家庭,其實(shí)是在刻畫所有尋子家庭的苦楚與艱辛。相較于過(guò)往的電視劇作品,《寶貝兒回家》對(duì)于演員的要求更高。劇中小曼的掙扎與絕望,啟明的無(wú)助與痛苦,都需要在整體表現(xiàn)上更具沖擊力,并及時(shí)捕捉到情感爆發(fā)點(diǎn)。小曼的飾演者陶紅曾表示:“我一天要哭好幾場(chǎng)戲,直到殺青都仍然籠罩在丟孩子的陰影中,甚至引發(fā)了身體的不適。”也正因?yàn)槿绱耍秾氊悆夯丶摇返那楦袀鬟_(dá)十分到位,甚至?xí)屇阌X(jué)得這個(gè)家庭好似就在自己身邊。
《寶貝兒回家》作為一個(gè)故事,感人;作為一個(gè)容器,幫助了社會(huì)中尋子家庭這個(gè)群體。當(dāng)然,從電視劇制作來(lái)看,它并非盡善盡美。作品整體的呈現(xiàn)風(fēng)格就顯得十分老派,無(wú)論是敘事推展或者畫面剪輯,都很傳統(tǒng),不夠新穎,總讓人錯(cuò)覺(jué)又回到了十年前的中國(guó)電視劇市場(chǎng)。不過(guò),只要內(nèi)容足夠扎實(shí),形式感也都是后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