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看見別樣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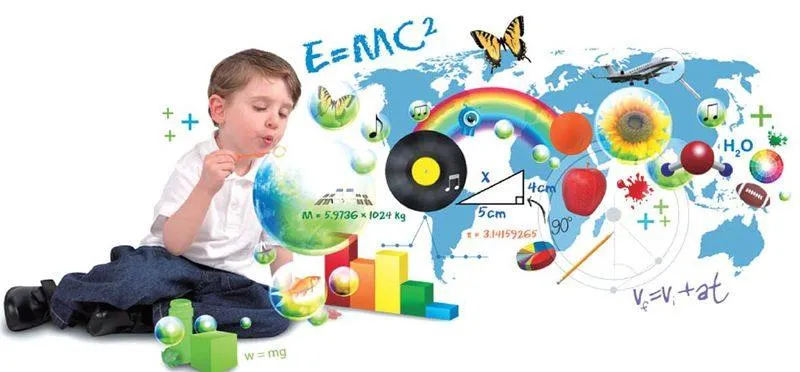
2014年某大型網站搞過一次“新視角高峰論壇”,名家云集,探討“富裕的中國還需不需要啟蒙”的問題。大多數論者主張,啟蒙精神是“五四傳統”中值得繼承和發揚的重要遺產,但在網絡上也可以讀到許多質疑和反駁,比如,“那些主張啟蒙的人,自己才是蒙昧的。到底誰來啟蒙誰啊?”“啟蒙本身是一種自負的現代迷信”等等。
上世紀80年代,中國思想界曾有過一個熱烈的“新啟蒙運動”,而20多年后的今天,社會環境和思想背景發生了改變,啟蒙變成了一個可疑的主張,甚至會遭到譏諷嘲笑。那么,今天再來談論啟蒙理想還有意義嗎?我想,這或許取決于如何理解啟蒙的涵義。
“啟蒙”對應的英文詞的原意是“光照”。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講過一個“洞穴寓言”,常常被用來解釋何為“啟蒙”。按照某種簡單化的理解,啟蒙就是走出習俗的蒙昧洞穴,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看到真實的世界。在這一解說中,習俗是黑暗落后的,理性是光明進步的,而啟蒙就是一個棄暗投明走向真理的歷程。但問題在于,你怎么知道自己啟蒙了呢?你走出了原來的“自然洞穴”,但很可能你進入了“第二級洞穴”;你以為自己看到了太陽的光輝,但說不定這是“日光燈”之類給你造成的幻覺。更糟糕的是,因為你自以為真理在握,就會急切地去啟蒙別人,自以為是地批判所有習俗。在這樣一種傲慢的“啟蒙心態”中,啟蒙不也會變成了一種偏見、狂熱和迷信嗎?
如果把啟蒙定義為通過理性發現終極真理,這或許是一種自負,也一定令人爭議不休。但是,可能有另一種不同的思路來理解啟蒙。無論是“棄暗投明”的說法,還是進入“第二洞穴”的闡釋,都肯定了一個事實:啟蒙是一次“出走”。于是,我們可以將啟蒙理解為由于“出走” 而獲得的“視野轉變”。這種轉變是由于看見了“別樣的生活”所激發的反思意識,而并不需要任何“發現真理”的假定。
試想,在一個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村莊里,父母打孩子是家常便飯,而且“好孩子”都是被打出來的。但假如有一天,有個男孩來到另一個異邦村莊,發現父母基本上不打孩子,而那個村莊居然也有很多“好孩子”。他會作何感想?在一個世世代代恪守“守寡戒律”的村莊,有一個喪夫的女子,有一天到了另一個遙遠的村莊,在那里她見證到女人是可以改嫁的,而那個村莊竟然沒有“秩序的崩潰”,她又會作何感想?
在見證了異邦別樣的生活之后,他們的視野發生了轉變。他們不再可能如同“出走”之前那樣,將“打孩子”或“守寡”當做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知道“生活可以是不同的樣子”。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必定會放棄原有的習俗。這個男孩可能仍然心甘情愿地接受“嚴厲的”教育方式;這位寡婦仍然可能繼續堅守她的貞節事業。但他們的理由變化了,或者說,他們需要一個理由來面對“異邦”的另類可能性。
在此,我們沒有假定“異邦的村莊”代表了什么“普遍真理”,也無需主張“不打孩子”或“允許改嫁”的文化就是“更高的文明”。我們甚至可以想象另一種情景——異邦的村民遠游到了“本邦”,驚奇地發現:打孩子可以成為一種教育方式,而且沒有多少孩子“被打壞”了;守寡可以是一種忠貞的方式,也并非那么不可忍受。“異邦人”也會因此而形成對自身習俗的反思意識。
所謂“洞穴”,就是由特定習俗構成的社會。生活在特定的習俗中而不自知,是一種“前啟蒙”的狀態。而我所理解的“啟蒙”,就是獲得對自身“洞穴性”的一種自覺——意識到自己生活在洞穴之中。我們不需要假設看見了“光明”才能獲得這種自覺意識,只需要知道“生活可以是別的樣子”就夠了。
如此理解的啟蒙仍然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習俗本來無需理由,而在啟蒙之后,各種習俗就會面對各種理由的挑戰,也需要用理由來應答和辯護。于是,“說理”就成為啟蒙之后的文化核心。而任何“不由分說”的政治與道德秩序,也就越來越難以維系。
(摘自中信出版社《中國有多特殊》 作者:劉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