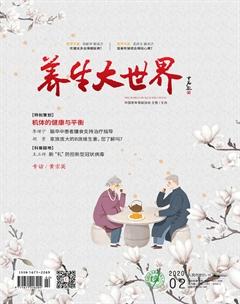吃出健康來——牡丹籽油
張軍

說到牡丹,人們腦海里就會浮現出美麗的牡丹花的畫面,耳邊也會響起蔣大為先生唱的牡丹之歌,“百花叢中最鮮艷,眾香國里最壯觀”,自古牡丹就被喻為“花中之王,國色天香”,你不知道的是牡丹不僅僅能觀賞,還可以“喝”,還可以“吃”。
一、牡丹渾身都是寶,牡丹籽油益處多
牡丹渾身都是寶。牡丹根的皮叫丹皮,含有丹皮酚,有非常好的抗菌消炎的功效,可作為藥材用于醫藥方面;牡丹的花朵能夠萃取精油,能美容養顏、調整內分泌;牡丹的花蕊可以做成花蕊茶,具有通經活血之功效,對于女性痛經、男性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都有不錯的功效;特別是牡丹籽可以榨油,不僅可以作為食用油,更有助于人體健康和自然養生。
牡丹籽油與其他油脂的比較


人們都知道吃橄欖油健康,因為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比較高,細分一下,是油酸高,而最重要的營養成分α-亞麻酸含量確很低(低于1%)。相比橄欖油,牡丹籽油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不僅遠高于橄欖油,其中α-亞麻酸的含量達到42%以上,遠遠超過了橄欖油,居所有植物油之首。同時含有獨特的牡丹皂甙、牡丹酚、牡丹多糖、牡丹甾醇,多種脂溶性維生素(如維生素E、維生素F)、此外還有豐富的萜類化合物--角鯊烯、黃酮類等營養物質。
二、牡丹籽油的優勢在何處?
(一)耐高溫
大家都知道橄欖油雖然較普通食用油營養價值高,但一般多用于涼拌菜,如果用于炒菜,一旦加熱以后,它的營養活性會大大降低;而牡丹籽油最大的亮點是可以耐高溫,因其高抗氧化性和黃金比例的不飽和脂肪酸含量,使其在高溫時化學結構仍能保持穩定,牡丹籽油的煙點在攝氏240到270度之間,也就是說,即使我們炒菜或者是油炸使用,都能夠保持不飽和脂肪酸的活性和它的高抗氧化性。
(二)富含α-亞麻酸
最權威的世界衛生組織推薦:每人每天α-亞麻酸的攝入量要大于1200毫克;中國營養學會也推薦:α-亞麻酸的攝入量要大于1400毫克。但是,我們國家衛生部調查結果顯示:中國居民α-亞麻酸的平均攝入量約為400毫克,僅達到適宜攝入量的三分之一,因此,α-亞麻酸攝入量不足,是加速衰老和多種疾病高發的原因之一,所以,富含α-亞麻酸的油脂是人們亟待滿足的健康需求。
三、α-亞麻酸——“植物性魚油”
(一)α-亞麻酸是什么?
為什么我們特別強調α-亞麻酸的含量?它究竟對人體健康起到了什么作用?細胞是人體最基本的組成單位,保持細胞的完整性和活性才能維持機體的正常功能。細胞膜一般是由磷脂雙層分子所組成,其中含有豐富的α-亞麻酸,α-亞麻酸對于細胞膜的流動性、通透性和完整性以及參與信息的傳遞方面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α-亞麻酸含量降低就會引起細胞膜流動性、通透性、完整性的一些改變,就會引起細胞的老化,細胞的代謝降低,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疾病。所以,α-亞麻酸的含量決定了細胞的代謝,同時也決定了是否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疾病以及細胞是否老化。α-亞麻酸除了能維持細胞正常代謝外,還在維持腦健康和血管健康方面起著重要作用。

最長壽的日本人經常吃深海魚,主要是其富含ω3(也就是α-亞麻酸),這個印象十幾年前人們就有,所以,各種制品應運而生。ω3不僅僅存在于深海魚里,還存在于植物油中,α-亞麻酸俗稱“植物性魚油”,經過體內酶的作用能轉化為 EPA和DHA。EPA又稱為血液營養素,能保持血流暢通、預防血栓、中風和心梗。維持血管良好的彈性與通透性,預防動脈硬化。DHA,又名腦黃金,能促進、協調神經傳導作用,以維持腦部細胞的正常運作,從而集中注意力、提高記憶力和理解力。攝食過多亞油酸,會導致體內ω6太高,從而競爭性抑制ω3的活性,繼而導致ω3生成DHA和EPA的功能障礙,打破ω6和ω3的平衡關系,其不良后果就是細胞代謝障礙,疾病產生。因此,WHO要求ω6/ω3二者比率為1:6,且各占熱量攝取的3%和0.5%為宜。中國居民膳食中吃魚特別是深海魚很少,很難從這類食物中獲得補充,大多數食用油中ω6含量高,很容易補充,而ω3含量低,包括人們熟悉的橄欖油,很難通過常見的食用油進行補充,因此,機體總處于ω6遠遠高于ω3的失衡狀態。研究表明:ω6和ω3的動態平衡對人體內環境穩定和正常生長發育具有重要作用,主要體現在穩定細胞膜結構、調控基因表達、維持細胞因子和脂蛋白的平衡等方面。目前人類日常飲食中ω6/ω3比例過高并呈現逐年上升趨勢。飲食中ω6/ω3比例過高與某些疾病的高發密切相關,如冠心病、糖尿病、乳腺癌等。因此,如何調節機體內ω6和ω3的平衡對預防三高、癌癥等慢性疾病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