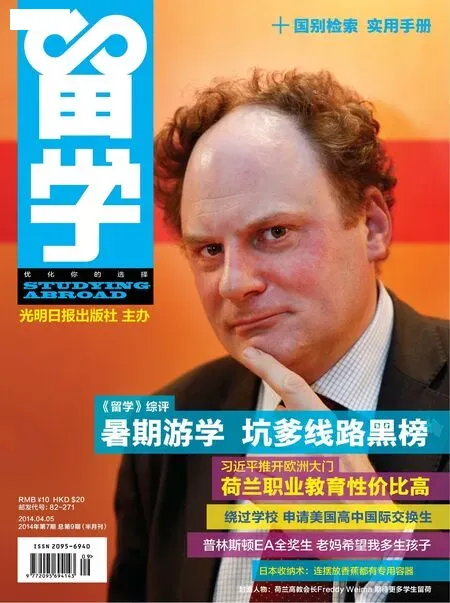《結婚話語權》跨國婚姻中的話語權
——德國版的《喜福會》
記者_安娜 發(fā)自北京 編輯_王泓瀅 攝影_董德
《結婚話語權》跨國婚姻中的話語權
——德國版的《喜福會》
記者_安娜 發(fā)自北京 編輯_王泓瀅 攝影_董德
讀完這本《結婚話語權》,抑制不住沖動要會一會作者黃梅女士,不僅因為她傳奇的經(jīng)歷,還希望得到書中大片大片留白的解讀,更別提她竟是李澤厚先生的關門弟子。無論是跨國婚姻,還是涉外戀情,總有挖掘隱私的尷尬。從小心翼翼地引導,到拿著文學名著做介質(zhì)探討,終于像第三次見面的熟人那樣聊起這些過往和帶來的思考。

《結婚話語權》是一本傳記體小說,以作者的實際經(jīng)歷為故事來源,講述了主人公梅林和吉姆一段真實的跨國愛戀,詮釋了作者對愛情和婚姻、對不同文化下的價值觀和婚姻觀的認知和感悟。
在談到書中第一個讓我玩味許久的片段時,黃梅忽然表現(xiàn)出驚喜和興奮:“我看過不少篇讀者的書評,但幾乎沒有人注意到這樣的小細節(jié),這都是我花了很大精力寫的,可大部分人的注意力還是放在了戀愛和婚姻的篇幅上;只有你。幫我寫篇書評吧。”
男人買單,與國籍無關
馬蒂亞斯站起身去了吧臺前,回來對梅林說可以走了,梅林說我還沒付賬,馬蒂亞斯笑著說他已經(jīng)全付了,梅林說這不行我必須自己付,但馬蒂亞斯已走出了店門,梅林只得跟在他身后。走到大街上,梅林再次說我該付我的賬單,馬蒂亞斯說他付了是一樣的,梅林說不行那不一樣,馬蒂亞斯停住了腳步,轉(zhuǎn)向梅林,聲音竟然有些澀:“怎么不一樣,在中國是這樣嗎?”梅林也停住了腳步,轉(zhuǎn)向他,聲音也有些澀:“在中國是男士付,可是我知道在德國是分開付賬的,分開付賬這個詞我在德國學的,并且已經(jīng)習慣了。”……馬蒂亞斯望著梅林,眼神里有說不清楚的意思,愛憐卻明明白白在其中,他短促地說:“是一樣的,我喜歡你。”
這就是中國女孩兒梅林(黃梅在小說中的化身,《結婚話語權》的女主角)在德國讀博士期間的第一段愛情,是他們的開始也是結束。如果《結婚話語權》哪天拍成了一部電影,這個無始無終的愛情片段一定是最難演的段落之一,盡管它充其量能占5分鐘的戲份兒。其實梅林在異國的第一次約會中的表現(xiàn),就為后面的婚戀奠下了基調(diào);盡管這朵玫瑰含苞未放,滄桑過后回首,發(fā)現(xiàn)它就像一言讖語,投射出未來的世界。
跨國婚姻中的話語權所在并不復雜難懂,黃梅直接道出了兩大要素—文化和經(jīng)濟。還是通過這個片段來細細探究。
糾結的AA制情結
梅林的糾結和困惑不難理解。八十年代末踏出國門的她,當時已經(jīng)在德國生活了八個月,學習并逐漸適應了AA制。就像那個年代出生的國人一樣,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時,漸漸開始使用并習慣了AA制。這既符合中國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訓,也彰顯了女性的獨立自主;在這之前,一般不都是男人結賬嗎,即便現(xiàn)在,還是有不少男人遵循“絕對不讓女人掏錢”的原則。
但這同時也讓不少女孩子們在一些常見的衍生議題上百思不得其解:異性和我AA是因為互相尊重還是因為我不是美女呢?談戀愛是應該堅持AA還是回到男人付賬的傳統(tǒng)呢?時至今日,讓男人買單是否是不自愛、貪小便宜的行為了呢?更有近來瘋傳的一個帖子《德國男人不為女人拎包》,兩性爭議已經(jīng)從敏感的經(jīng)濟話題延伸到了舉手之勞的日常行為,并且被上綱上線。
這些疑問顯然也困擾著當年在異域文化中求學的梅林,黃梅給了梅林一段非常坦誠的心理獨白:“我畢竟是個中國女孩,天生就希望被紳士們寵著,可是在德國八個月,替我開門的紳士不少,幫我付賬的紳士卻沒碰到過,每次被熱情地邀請聚會,臨終服務小姐向大家一一收款,當然是分開付,我心里卻總是有說不出的滋味。”
所以,當一個聊得來的男人給自己買了一個冰淇淋的時候,梅林迷糊了、惶恐了,進而有了種情緒,叫“自尊的委屈”。是啊,他為什么要付錢呢?這不符合他們的文化呀。他覺得梅林是個窮學生,吃不起冰淇淋?越想越復雜,越復雜就越可怕。在他付錢的行為中,他對梅林的定位是個窮學生還是個中國姑娘?他是覺得中國人窮,還是覺得中國姑娘需要或樂見男人買單?
而這時的梅林要如何反應?
在華裔文學名作《喜福會》中,也專門提到了這個問題—Lina的丈夫事事都要AA制,而且是搜腸剮骨占便宜類型的AA制,Lina覺得不妥,卻從未提出過異議。直到有一天,母親告訴她這不是尊重,更與愛無關,Lina才逃出了“女性如何表達自尊與男性如何表達喜愛”的迷宮。
梅林是如此的坦誠可愛,她直接向馬爾蒂斯發(fā)問了,也得到了最讓人踏實的回答:“(不論在德國還是中國)道理是一樣的,因為我喜歡你。”在黃梅聊完這個片段后,我還是忍不住刨根問底:“真的如此嗎?我聽說過不止一個和外國人談戀愛AA制的案例呀。那么拎包的傳說也是謠傳嗎?”
“是真的呀,這是人性,與國別關系不大,”黃梅很耐心,“他喜歡你,所以買單時也非常坦然,并不刻意。后來在戀愛和婚姻中,我的先生也是這樣。當然,我那時還是個靠打工為生的窮學生,如果我有工作有收入,主動要求平攤,他也不會執(zhí)意不要。但嚴格的AA制,我很難想象,也沒見到過。戀愛時可能可以,一旦進入婚姻,尤其有了孩子之后,嚴格的AA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個偽命題呀。”至于拎包,黃梅還真注意到了這個現(xiàn)象,不過她感覺和什么獨立啊自尊啊無關,“德國女人身體普遍比我們強壯多了,真的,咱們和她們骨架就不一樣。”

德籍華人、《結婚話語權》作者黃梅。
經(jīng)濟基礎真的是婚姻基礎
書中這樣提道:梅林是因為未能在生孩子的問題上和吉姆達成共識才離婚的。但在這之前,他們已經(jīng)分居了,因為經(jīng)濟問題和繞不開的自尊話題。
在兩個人戀愛時,梅林一邊打工一邊讀博士,有穩(wěn)定工作的吉姆非常自然的承擔兩人的生活開銷,并且非常支持梅林打工。結婚后,梅林卻成了全職太太和博士研究生,因為吉姆說,“我的老婆可不能去打工。”提起這句話,黃梅仍然覺得很好笑:“不理解吧?同樣是我,同樣是他的愛人。做女朋友的時候,他有時候還催我打工不要遲到;做了老婆,他就不許我去了。”吉姆有著典型的德國式的上進和嚴謹,他甚至在結婚的第二天就六點半起床去上班了。他既嚴謹又浪漫,既文藝博學又陽光運動,而且還出身名門,是個真正的白馬王子。更難得的是,吉姆的媽媽對梅林非常滿意,甚至還主動增加了對他們小家庭的經(jīng)濟資助。
如果就這樣下去,他們最多在什么時候生孩子的問題上多吵幾次架。但遇上了經(jīng)濟環(huán)境不景氣,吉姆失業(yè)了,盡管很快又找到了工作,但這讓他對家庭經(jīng)濟狀況產(chǎn)生了極大的不安全感,而他的處理方式實在讓人費解。
吉姆生活富裕的父母很樂意給孩子經(jīng)濟資助,且并不因此多提要求,吉姆也受之怡然。于是失業(yè)的吉姆算了一筆賬—如果靠著父母的資助,他可以一個人周游世界,瀟灑生活;但如果帶上沒有工作和收入的梅林,他的生活質(zhì)量就要打?qū)φ邸S谑牵芬笈c梅林做財產(chǎn)公證。這似乎應了一句中國的老話: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來時各自飛。這個要求讓當時的梅林倍感屈辱。
很快,他們正式分居,按照當?shù)氐姆梢?guī)定,吉姆要付給梅林自己收入的1/4作為贍養(yǎng)費。梅林感到可笑又無奈:“我們一起過日子的時候,我這個主婦嚴格控制開銷,一個月絕對花不到他1/4的收入,而現(xiàn)在他要付給我這么多,再用剩下的錢生活。”到底在吉姆的眼里,怎樣才算保護自己的經(jīng)濟利益呢?我們不得而知。后來,梅林放棄了贍養(yǎng)費,這是不少女人離婚時為了保衛(wèi)自尊而放棄財產(chǎn)的老橋段了。
現(xiàn)在,黃梅將這歸結為當時自己沒有工作,家庭經(jīng)濟皆來源于吉姆一個人,所以一次失業(yè)就把吉姆嚇著了。確實如此,除了和梅林公證財產(chǎn),他還在此后一直保持著投簡歷的習慣,像強迫癥一般,要保持自己的簡歷在30家公司的人才庫里,每接到一封拒信,就立刻再投出一封簡歷。
黃 梅
德籍華人,職業(yè)策展人、譯者。德國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李澤厚先生哲學碩士,北京大學理學學士。現(xiàn)任德國藝術與教育國際交流促進會主席及三和尚經(jīng)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
文化話語權是左右婚姻的終極原因
如果說經(jīng)濟基礎真的是婚姻基石的話,它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決定話語權的其中一個因素,而文化話語權才是黃梅總結的、跨國婚姻中影響話語權的最終原因,也是導致他們最終分手的一個癥結。
提起文學與文化對愛情觀的影響,黃梅舉的第一個例子就是《簡愛》。書中的梅林也熱烈地向吉姆朗誦過簡·愛對羅切斯特先生那段著名的剖白。而得到的回應卻無異于一盆冷水—吉姆向他推薦《魯濱遜漂流記》,當時的梅林和吉姆都認為這是本娛樂讀物。不同的在于,吉姆希望梅林讀來娛樂身心,不要像簡·愛小姐那么沉重;而梅林覺得人生就是努力奮斗,哪有時間讀這種玩樂作品。
看來他們都沒有意識到,《簡愛》的愛情觀本身就布滿隱憂;而《魯濱遜漂流記》也并非完全反應了吉姆瀟灑愛玩的心態(tài)。他們對這兩本書的態(tài)度,絕妙地映射出了二人懸殊的文化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日后的發(fā)展。不知這是黃梅有意安排,還是世事就是這么妙不可言。
簡·愛不僅是個窮家女,而且是個私生女,同時作為家庭教師的她其實是羅切斯特先生的雇員。面對著無論在經(jīng)濟地位還是社會地位都高出她許多的愛人,簡·愛也一直都有“自尊的委屈”,這就是她為什么要一再強調(diào)“靈魂的平等”。說到底,這二人的行止見識都不平等,三觀恐怕也有著階級性的差別。當時的羅切斯特是簡·愛精神與經(jīng)濟的全部,越是如此,她更是要對著強勢的一方堅決維護自己僅有的尊嚴。
而《魯濱遜漂流記》則反應了吉姆的瀟灑個性,以及他所代表的強勢文化,魯濱遜不是還馴化了一個土著人嗎?正是這種強勢文化帶來自信與自我,以及梅林簡·愛式的自尊與自愛,讓他們之間打了個水手結,越掙扎越緊,解不開了。
黃梅回憶起當時她和前夫(吉姆的原型)關于中國的爭論,說到底還是因為當初的德國較之中國而言,更處于文化和經(jīng)濟的雙重強勢地位:“我記得那個時候他跟我來中國。他根本不喜歡北京,覺得北京灰禿禿的,建筑都是灰色調(diào),高樓像大盒子一樣。其實我們自己也會批判自己的國家,但聽到他們一講,心理就會特別不舒服。”
是啊,這畢竟是我家,你是個客人,一進門就說我家臟,還看不慣我們辛辛苦苦置辦的家具,我能舒服嗎?黃梅分析說,擱到今天,這種反感可能會小很多,因為中國富強了,我們也漸漸地處于強勢文化的一方,對于德國也有了批判,“但對當時的我們來說,我是那么喜歡德國,他竟然這么說中國,我能平衡嗎?但如果是一個德國人和一個法國人,他們的國家情況差不多,既沒什么懸殊,也沒多少誤解,可能互相批評、互相調(diào)侃,這都很正常。”
于是,吉姆對一個地方的感性評價被感性的梅林上升到了要求平等的位置。但梅林沒有冤枉吉姆,因為當時的吉姆真的不喜歡當時的中國,他甚至表示,如果生了孩子,不許梅林帶回中國。德國人對中國的文化不認同,同時梅林在德國多年,哪怕有了合法的身份,也沒有真正的歸屬感和足夠的發(fā)展空間,這種文化不安全感帶來的恐慌成了婚姻走向破裂的催化劑。
在講到歸屬感時,黃梅舉了一個在國外打拼的人多少都會遇到的例子。“在德國時,我的學校所在的城市工作機會少,我要跑到周圍的大城市打工,周末在餐館里端盤子,周日晚上坐火車返校,趕周一的課。有一次,大晚上的,一輛車晚點了,停在那不開。我心里又急又怕,就去問詢問售票員為什么不開車?然后他打量了我一番,就說了一句,‘你覺得中國的火車不晚點,你就回中國去。’”
中國的火車也會晚點,但黃梅還是回來了。當積蓄只足夠買一套房子的時候,她選擇把家安在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