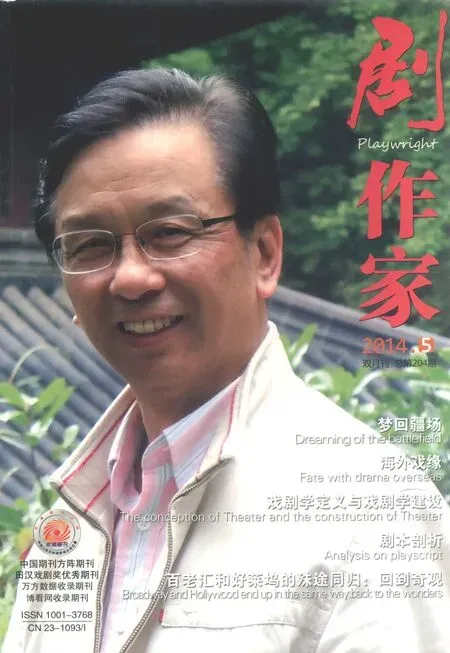思想是作品的靈魂——序《劉呼同劇作選》
曾獻平
思想是作品的靈魂——序《劉呼同劇作選》
曾獻平

(劉呼同在悉尼)
“在各種文學樣式中,劇本是最難寫的一種”,這不僅是名人箴言,也是業內人士的共識。但是我認為,最難寫的不是哪一種文學樣式,而是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品。思想才是作品真正的靈魂。讀劉呼同先生的劇本,感受最深的,不僅僅因為其作品文筆流暢,用詞精當,語言俏皮,幽默風趣,而因其思想的犀利性、尖銳性和深刻性,刻畫人物、描摹生活、針砭時弊、揭露社會陰暗面,往往一針見血、一語中的、令人擊節。
呼同兄個頭不高、貌不壓眾,說話大嗓門、好爭論、面紅耳赤,時不時還會冒出幾句臟話,若不是鼻梁上架一副近視鏡,似乎不太像個文人。但他腹中確有“干貨”。多年來,他創作小品五十余個,其中不少獲省市及全國大獎:如《求職路上》獲中國劇協曹禺杯小品小戲一等獎;《誰來買單》《會蟲》《等待鎮座》《酒瘋》《誘惑》獲中國戲劇文學獎一等獎;還有不少省市一二等獎。當然,獲獎不是主要的,能在思想上、心理上與觀眾引起共鳴才是最重要的。我看過幾個由業余演員演出的他的作品,效果出人意料,不但贏得滿堂笑聲和掌聲,有的作品如《會蟲》,令全場觀眾從頭笑到尾,而在笑聲背后,卻蘊藏著非常尖銳的社會問題,啟人深思,發人深省。
他的獨幕劇大都寫于改革開放初期,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太多超前意識的東西,可是當時卻是令人震撼的。就在中央關于“改正”右派的決定剛剛在坊間傳說的時候,人們還不知是真是假,呼同兄便“冒險創作了獨幕話劇《乍暖還寒》,讓一個工廠黨委書記的女兒(共產黨員),去愛一個“右派”,并且喊出“難道在我們這個沒有種族歧視的國度里應該有另外一種歧視嗎”這樣撕心裂肺的“天問”。這不僅美化了右派,而且犯了文藝作品“寫愛情”的大忌(“文革”中不成文的規定,文藝作品不能表現愛情)。這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無怪當初看到原稿的人,都異口同聲地說:“你好大膽!”
獨幕話劇《真是,怎么辦》,是作者看到報紙上一則小信息而受到觸動,產生了靈感,于當晚一氣呵成的,寫得有智慧、有膽識。與著名劇作家沙葉新先生根據同一報道創作的話劇《假如我是真的》各有千秋。
四幕話劇《月黃昏》創作于1986年,是寫婚姻、戀愛、家庭的倫理劇。作者沒有把筆墨放在寫故事、寫事件上,而是側重揭示人物的潛意識,展示人物在特定情境下的心態變化及復雜、微妙的情感歷程;寫人物的歡樂與痛苦,幻想與追求;寫人物性格上的弱點及由于他們不能自制而做的蠢事,并為此付出的沉重代價。劇中指出,在婚姻上,和諧美滿的只占少數,大多數是不盡人意的,其中不少是瀕臨解體、死亡的。應該怎樣對待這種狀況呢?當時社會上已經展開辯論。有人引用恩格斯的話說,“沒有愛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因而應當完全解除。有人則認為,維持婚姻關系是倫理道德,是社會責任、家庭義務等等。
《月黃昏》沒有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而是通過兩對貌合神離的夫妻之間微妙、復雜的情感糾葛,來啟示人們,對不幸婚姻要因人而異。一對夫妻離異了,我們要給予理解和寬容;另一對夫妻勉強維持下來了,我們同樣要給予理解和寬容切不可說三道四、橫加指責。夫妻間的事,往往當事人自己都說不清,別人怎么能說得清呢?
有人說,他不喜歡于芳這樣的女性,這很正常。文藝作品既可以寫招人喜歡的人物,也可以寫不招人喜歡的人物,還可以寫既招人喜歡又不招人喜歡的人物(即不好不壞,亦好亦壞、時好時壞的人物)。當然,就同一個人物,人們從不同角度、不同愛好出發,可能得出不同結論。可能有人對于芳“深惡痛絕”,也可能對于芳“一見鐘情”,這是好現象。只要觀眾動了感情,引發了思考,那就是作品的成功。最可怕的是觀眾對作品提供的人物和情節置若罔聞、無動于衷,那才是真正可悲的結果。這種多元的、包容的、各抒己見的創作思想,在當時人們思想還相當僵化、言論管制還相當森嚴的社會背景下,其真言、直言、敢言的精神,是多么難能可貴!
六場喜劇《八喜臨門》寫了幾個從全國各地來深圳求發展的“淘金者”。他們身份各異,性格各異,相同的是,他們都經歷了不少坎坷和挫折,碰了不少的“釘子”,但最后都在深圳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全劇充滿了機趣,令人忍俊不禁,笑口常開,同樣在笑聲中揭示了不少社會弊端和人性弱點,是一出思想深刻的通俗喜劇。全劇一個場景,七個人物,既可以在大劇場演出,也可以在小劇場演出,且都能產生極佳的“笑果”。廣州市群藝館的曾志灼——一位熱情洋溢的青年劇作家,對劇本很感興趣,為適應廣州人的口味,經作者同意,他把劇本改成方言劇,由廣州市劇協組織嶺南話劇團演出多場,反響強烈,他們準備繼續演下去。
電影文學劇本《瘋狂的欲望》,是1991年作者在長春電影制片廠修改他的《小店經理》時,從報上看到一個發生在哈爾濱的大案即興創作的。這個劇本的特點是,不賣關子,不故弄玄虛,不人為設置“懸念”,讓偵查員與犯罪嫌疑人時不時地打個照面,從而產生許多有趣的情節,也就是用喜劇手法寫偵破劇。只可惜,當時社會上對電影的觀賞取向是:“文戲要上床,武戲要上房。”為迎合市場,有關人員讓作者把劇本改成“槍戰戲”,但被作者拒絕,此劇本制作事宜因此擱置。
縱觀全書,不管是舞臺劇或影視劇,不管是為文或為人,作者都堅守了自己的獨立思想和做人的原則,決不附炎趨勢,決不隨波逐流,字里行間散發著文人的骨氣和社會的良知。幾十年的風云變幻、得失榮辱,呼同兄變得更為灑脫、更為飄逸了,所以讀他的劇本感受不到絲毫的教化感和壓抑感,有的只是一股穿透紙背的思想鋒芒和靈性之光。
(曾獻平: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本文轉自《劉呼同戲劇選》,中國文聯出版社,2013年版。)
責任編輯 王彩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