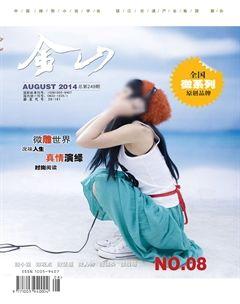《雷雨》故事如果發生在今天
烏克彈
話劇《雷雨》的第一次公演是1934年,在浙江上虞一個中學的禮堂里。臺下的好多觀眾是連普通話也聽不懂的當地村民。但這沒有妨礙這些村民鼓掌擦眼淚,人間的悲歡離合,誰看不懂啊?算算日子,這次公演距今已是整整八十年。寫話劇的,中國有兩個了不得的人,一個是曹禺,一個是老舍,《雷雨》《日出》《茶館》《駱駝祥子》,就好像李白的唐詩和蘇東坡的宋詞,后來寫劇本的,怎么寫也沒超過他倆。高峰就是高峰,要仰望。
《雷雨》的故事會不會發生在今天?如果會,故事的情節又會有什么不同?這個問題是曹禺先生的女兒萬方提出來的。這個問題很有趣。
《雷雨》的故事要是發生在今天,周樸園就是企業家,周萍、周沖就是富二代,早就會被娘老子送到歐美去留學鍍金。這兩個紈绔子弟,要泡妞也不會泡繼母,泡家中女傭,而會另有所圖,別有所愛。
《雷雨》的故事要是發生在今天,魯大海打工的煤礦是不會鬧什么罷工的。不想干,請走人。可是,農村來的魯大海并沒有幾條路好走。他來自農村,回去就是種田,而種田是不能讓魯大海活得像個人樣的。要是城市發展,將他的村子變成了工廠、高爾夫俱樂部或住宅樓,這個過去的挖煤工就成了失地農民,估計還得重返煤礦下井賣苦力。
《雷雨》的故事要是發生在今天,周沖根本不會暗戀四鳳,更不會自掏腰包贊助四鳳上學識字。周樸園是煤老板,在今天,這是個特別有錢的階層,他會在小兒子七歲時就將他送到國外上學。學什么無所謂,呆在哪兒才是最重要的。在老爸的培養下,周沖十分嫻熟的就是住別墅,開跑車,出入會所,舉行派對,這都是很費錢的高尚行為,周沖總覺得缺錢,于是不斷張口要,美元,歐元,快點打進我的信用卡!在這樣的背景和需求下,周沖怎么會成為慈善家、施舍人?
在《雷雨》中,周樸園逼迫繁漪喝湯藥,這是冷暴力,這事要是發生在今天,繁漪向婦聯哭訴,周樸園就得寫檢討;要是繁漪發微信,有圖有文,向網絡大V求救,周樸園的下場可能會很慘。
當下版的《雷雨》真還不知怎么安排故事情節、展現人物命運。亂亂的。但曹禺的女兒萬方膽子大,她說她正在改編《雷雨》。會改成什么樣子呢?且等待。
曹禺的姑娘要改編父親的《雷雨》,老舍的兒子舒乙又在做什么呢?他要為父親“平反”,因為老舍活著時曾被左翼主流文學視為另類。
說到左翼文學,我們就會想到十里洋場,三十年代,一些神氣活現的作家,三個一群,五個一派,為口號爭來爭去。那個時候,老舍是個教書匠,在山東一所大學里教文藝理論,教材是自己寫的,叫《文學概論講義》。別看平素老舍溫文爾雅,站到講臺上卻是離經叛道,擁有一些大膽獨特的觀點。比如“文學的使命是解釋人生”,“文學不是消遣品”,“文學是獨立的,不是政治的附庸”,還說“文以載道”不對,“思想性第一、藝術性第二”不對。這些帶著山東大蔥味的觀點,傳到上海,當然和咖啡味的左翼文學形成沖突。老舍勢單力薄,上海幫群聲鼎沸,占上風的當然不會是老舍。老舍就專心致志寫起小說話劇了。理論的是非有什么爭頭呢?作家總是要靠作品說話。后來的事實也說明,老舍比許多許多左翼作家更優秀,而那些擅長理論爭吵的人,至多是那段文學史上的土坷垃。
這時可以說說老舍的那些理論了。說什么呢,說這些理論在今天的現實遭遇,說當今的文學現狀吧。“文以載道”仍然風靡,文學還不是個獨立行走的青年,文學常常要踩著別人的腳印,跟著別人的背影向前,思想性必須排在前面,文學光光解釋人生是不夠的,文學最好是人生規劃師和道德講解員,兼能煲一鍋心靈雞湯。相當矛盾的一點是,文學現在又確實是消遣品。我們不能誤以為這是老舍理論的失敗,也不能誤以為這是左翼文學的勝利,我們寧愿用多元、用寬容來解釋。你可以左,你可以右,你可以守舊,你也可以創新,你可以是連喝一星期的雞湯,你也可以是一分鐘的消遣品,各行其是吧。
舒乙大聲疾呼:“過去對老舍的認識可以來一個大逆轉。”不知這是不是很有必要?我們這些蝸居小城市的人,其實很想請托舒乙辦一件事,到北京人藝幫我們疏通疏通,帶上一應的名角,到鎮江來演一場《茶館》。
算了,還是帶臺《雷雨》來吧。為了紀念《雷雨》問世八十周年,北京人藝專門為大中學生演出了一場《雷雨》。誰知整場演出,學生不斷哄笑,讓臺上的大藝術家們不知所措。笑什么?笑劇情可笑,笑演員的表演夸張。一夜情也好,家庭亂倫也好,始亂終棄也好,在年輕的觀眾看來,并不值得去尋死覓活,臺上的演出太不真了。有人說學生不懂經典,學生反唇相譏,悲劇也要允許我們發笑。這條剛發生的新聞讓我改變了想法,就請北京人藝來演《雷雨》吧,無法料想的是,在劇場里,鎮江人是不是也會笑成一團。
為了紀念《雷雨》問世八十周年,北京人藝專門為大中學生演出了一場《雷雨》。誰知整場演出,學生不斷哄笑,讓臺上的大藝術家們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