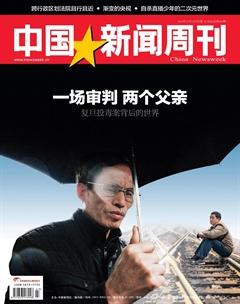讓俄羅斯做俄羅斯
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長,現為托萊多國際和平中心主任。著有《戰爭傷疤,和平傷口: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劇》
在1947年出版的名作《X》中,喬治·凱南(GeorgeF.Kennan)指出,蘇聯對美國的敵意基本上是不可抑制的,因為其根源不僅有超級大國之間的典型的利益沖突,也包括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和不安全感。目前普京的俄羅斯與西方的沖突也是如此:從根本上看,這是一場西方持有的普世價值與俄羅斯所追求的獨特身份之間的碰撞。
一國為身份而作的斗爭可以左右它的戰略行為。例如,美國文明中的傳教士精神有助于解釋它身為全球超級大國的行為;伊斯蘭教的重新崛起,本質上是被現代性挑戰所壓制的古老文明對其現實身份的追求;以色列對其猶太身份的強調,也成為其與巴勒斯坦實現和平的可怕的障礙。
普京的挑戰性的外交政策是對帝國的恥辱性失落的一種反映——這種反映是借由這個民族的威權政治傳統、東正教的保守原則以及對俄羅斯廣袤領土和充裕自然財富的驕傲來實現的。普京從俄羅斯在冷戰的失敗中,找到了頌揚俄羅斯歷史和傳統中的非西方根基的需要,他實際上是在倒向1812年拿破侖入侵俄羅斯所引起的保守價值——那一入侵挫敗了彼得大帝的現代化大計。
俄羅斯副總理沃洛金在最近在索契召開的瓦爾代辯論俱樂部(ValdaiDiscussionClub)會議上說,“普京就是俄羅斯,俄羅斯就是普京。”他說出了一個意義深遠的俄羅斯現實。沒有哪個國家像俄羅斯一樣,統治者的個人形象可以對國家的歷史產生如此深的印記——從凱瑟琳大帝、伊凡雷帝到列寧和斯大林。
但不能把普京貶低為只是無窮盡地追求權力。普京知道,俄羅斯在世界舞臺上的重新崛起必須以打破“美國例外論”為基礎。
想基礎都和俄羅斯的理念不同。去年,普京聲稱,蘇聯的解體是對俄羅斯的“文化和精神”的“災難性打擊”,隨后“從海外讓俄羅斯文明化的嘗試”演變為一種“原始的效仿”。普京不能期待新的國家意識形態會自我產生,而必須追求和發展獨特的身份,這種追求在普京的領導下進行。
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確保俄羅斯的一席普京的俄羅斯與西方的沖突是一場西方持有的普世價值與俄羅斯所追求的獨特身份之間的碰撞。俄羅斯不需要顛覆已有的全球秩序,它只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美國必須讓它實現這一目標之地是建立這一身份的必要條件之一。在這方面,普京實現了以俄羅斯巨大的油氣儲備為基礎的外交政策價值的最大化,同時也讓克里姆林宮與崛起的亞洲大國(尤其是中國)得以構建強有力的關系。如果像一些俄羅斯官員所提出的,俄羅斯將開始一項大規模的身份構建工程——開發廣袤的烏拉爾山以東領土(包括西伯利亞和遠東),它就有了進一步深化這些聯系的獨特的機會。
更廣泛地來看,普京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可以吸引一些國家和民族的支持,它們共同反對美國施加的價值與國際規范。事實上,對許多國際行動方來說,西方的寬容和政治正確概念——比如接受同性戀等“非傳統生活方式”——用普京的話來說,是對“神賜多樣性”的侮辱。
和繼續動搖烏克蘭的現狀,展現了他更大的野心——重塑俄羅斯在歐亞和廣大前蘇聯地區的文化和政治主宰地位。在普京看來,1945年將歐洲分為蘇聯和西方兩大勢力范圍的雅爾塔協議并沒有死去,只是邊界有所東移。
很能說明問題的是,在最近召開的瓦爾代辯論俱樂部會議上,在討論了大量的全球挑戰后,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將摩爾多瓦首都基希納烏俄羅斯族的游行稱為有待解決的“最重要的問題”。普京的俄羅斯在民族團結問題上毫不含糊。
當然,西方——特別是美國——也需要為沒能找到外交途徑應對俄羅斯最近的攤牌行為負責。在能夠實現持續和平之前,美國需要反思其后冷戰時代霸權主義的錯誤——其單邊軍事行動和新帝國主義野心使其戰線過長、負債累累,還陷入了持續不斷的戰爭。
不進行這樣的反省,美國及其歐洲盟友就有可能繼續依靠經濟制裁來威懾俄羅斯的行動。但是,盡管這一方針能夠限制普京帶來經濟繁榮的能力,從而削弱他的合法性,但也會導致反西方民族主義的反彈。此外,正如俄羅斯副總理舒瓦洛夫所言,制裁或許是件好事,它將迫使克里姆林宮實現俄羅斯基于大宗商品經濟的多樣化。
民族身份不可能通過談判來解決,但外交可以“稀釋”民族身份帶來的侵略性。俄羅斯和西方領導人應該就東烏克蘭問題做一筆超過明斯克協議的大交易,以促進雙方在敘利亞內戰和伊朗核計劃等問題上的合作,從而解決全球安全和武器控制問題。
俄羅斯不需要顛覆已有的全球秩序;它只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美國必須讓它實現這一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