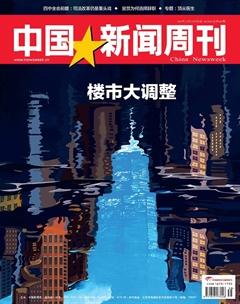季加孚:什么才是好的醫療
下午3點,北京腫瘤醫院特需門診室,滿滿當當都是人。季加孚進來了,診室隨之騷動起來,他瞬間就被二三十號病人和家屬包圍了。
每周的掛號名額只有10個,但是面對等待加號的病人,只要時間允許,季加孚總是很大方——“加、加、加,全部加!”很多病人從外地過來,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只是為了讓他看一看片子,聽他的幾句意見。在這個大約20平方米的診室里,病人最緊張的時刻就是季加孚皺著眉頭看片子,他突然間的沉默,或者拿起病歷發出“嘖”的一聲,都會讓他們的心顫抖一下。
“他就像是我的老天爺。”接受過治療的患者群英這樣形容季加孚。手術做完以后,群英才知道自己患的是晚期胃癌。剛開始化療的兩個月,她總怕自己會突然死掉。一天晚上,突然出現嚴重的腹瀉,她越想越害怕,忍不住給季加孚發了短信。凌晨兩點,季加孚回復她:“放心,你不會死掉的,我們這么多人在看著你呢。”后來,害怕的時候群英就會翻看季加孚的短信。“看他的那些話,能給自己信心。”

季加孚的態度常常是積極樂觀的,但是,治病要花錢,而癌癥治療,有可能是個無底洞。如果季加孚非常謹慎地說,“可以手術,但風險很大”,那么癌癥基本上就是晚期,手術也無法保證能徹底清掃。如果出現術后并發癥,治,就是持續地花錢;不治,就是等死。在錢和命之間,季加孚無法替病人抉擇。他說,“如果為了治病,使這家人傾家蕩產,合適么?好的醫療,是病人能夠承受的醫療。”
季加孚記得,在美國讀書的時候,老師經常問,如果這是你的父母,你怎么做決定?現在,他也拿這個問題問年輕大夫。
季加孚的學生大李,已經是科室的副主任。2012年他剛來的時候,胃腸外科只有季加孚一個固定大夫。那時候,醫院附近沒有那么多賓館,外地來的病人對北京不熟悉,季加孚就讓科里的年輕大夫開著車拉著經濟情況不好的家屬找便宜的旅館。大李說,“那些都是素不相識的人。”
全世界每10名胃癌病人中,有5名來自中國。中國每年大約新增46萬胃癌患者,同時,有30萬人因胃癌而死去,這意味著,平均每2分鐘,就有一人死于胃癌。季加孚積極參加健康教育活動,每次他都會特別強調篩查:50歲以上的人或者高危群人,每3到5年做一次胃鏡和腸鏡,保證在這期間發現的胃癌和大腸癌不會太晚。他說,“癌癥是分期的,一期病人的治愈率在90%以上,但到了四期,治愈率就會下降到10%以下。”
現在很多病人都會通過互聯網,獲取和自己病情有關的信息。但是有很多人斷章取義,一知半解。季加孚認為,在醫院,不需要討論發病機理,需要告訴病人的,是得了什么病、處于什么期、好不好治,讓他們明白患者的權利和義務。而這,需要建立醫生的權威性。“權威性的基礎,就是要讓患者信任你。”對此,他打比方說,“坐飛機,你關心是哪家航空公司、準不準時,這很正常,可是你沒必要和飛行員討論飛機怎么飛上天的、有幾個發動機。 ”
十年前,季加孚是個有爭議的人。那時他還是一名普通的腫瘤醫生,想在全國推廣標準的胃癌根治術D2,教那些已經有十幾年、二十年經驗的外科大夫如何做一臺標準的胃癌手術。但那時候沒人理他。十年后,標準胃癌根治術已經是醫療界的共識,中國進展期胃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提高了10個百分點,沒有人再質疑D2對進展期胃癌患者的療效了。
季加孚不愿意多談自己,“沒意義。每個人的成長歷程都不一樣,有困難自己解決,我從來不和別人說。”
季加孚沒有“工作之余”。平常上班,周末開會。他說,我的職業病,就是整天想著工作,不想其他事情。他的額頭,天生有一道很深的皺紋,像二郎神的第三只眼。群英說,那是因為他老在思考,皺眉頭,“琢磨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