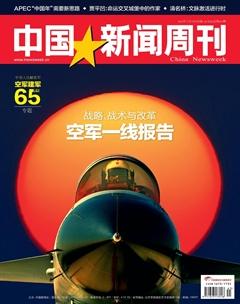最高檢出臺新規保護“深喉”
韓永
十八屆四中全會剛結束,最高檢的一份文件開始受到關注。其主題指向了中國司法的一個軟肋——對舉報人的保護。
該文件是最高檢修訂的《人民檢察院舉報工作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外界對其寄予厚望,希望借此改變舉報人屢遭報復的處境,并激發更多的舉報動力,由此推動中國反腐進入更良性的軌道。
但在另一方面,基于舉報人保護涉及面寬,而此文件只是最高檢出臺的規定,法階較低,業內又對其實施的效果存疑。
更具操作性的保護規定
這是《人民檢察院舉報工作規定》的第二次修訂。該文件制定于1996年,曾在2009年做過一次修訂。
對比前后三個版本,可以看出中國在舉報人保護方面的制度變遷:前兩版保護的重點,是要求相關人員對舉報人的信息保密,以及對報復舉報人行為的懲罰。1996版較為宏觀,而2009版則更加具體。比如,1996版的表述為“舉報的受理、登記、轉辦、保管等各個環節,應當嚴格保密,嚴防泄露或者遺失”;而2009版的表述則是,“舉報線索由專人錄入專用計算機,加密碼嚴格管理,未經授權或者批準,其他工作人員不得查看”,以及“舉報材料不得隨意擺放,無關人員不得隨意進入舉報線索處理場所”。
到了2014版,2009版中的“未經授權或者批準”,變成了“未經檢察長批準”;“舉報材料不得隨意擺放”的表述,也變成了“舉報材料應當放置于保密場所,保密場所應當配備保密設施”。
一位受訪的刑訴法學者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表述的細化,意味著可操作性的提高。而在中國,困擾舉報人保護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如何讓寬泛的法律規定,變得更有操作性。
2014版所帶來的變化,除了上述表述上的差異外,還有兩個方面:一是首次規定舉報人有向檢察院申請保護的權利。《規定》第八條列舉了舉報人享有的6項權利,其中第4項為:“舉報人舉報后,如果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威脅,有權請求人民檢察院予以保護。”
其次,2014版帶來的另一個變化,是規定了上述權利實現的路徑:一是“人民檢察院受理實名舉報后,應當對舉報風險進行評估,必要時應當制定舉報人保護預案”;二是“舉報人在人身、財產安全受到威脅向人民檢察院求助時,舉報中心或者偵查部門應當迅速查明情況,向檢察長報告。認為威脅確實存在的,應當及時通知當地公安機關;情況緊急的,應當先指派法警采取人身保護的臨時措施保護舉報人,并及時通知當地公安機關”。
這兩條規定,前者體現事前預防,后者則體現事中預防。此前,在舉報人保護的相關制度中這兩者均是空白。在1996版和2009版《規定》中,主要內容是對報復舉報人行為的懲罰,其邏輯是:在舉報人被報復之前,檢察院不管;只有在舉報人被報復之后,檢察院才負責善后。
“這其實已經不能叫‘保護舉報人了,因為它根本沒有提供保護,只是善后。”前述刑訴法學者說。
大量舉報人遭到報復
只注重事后懲罰而不管事前預防和事中干預的一個后果,是大量的舉報人遭到報復,而相關的法律規定形同虛設。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丹紅,曾經在自己的文章《舉報人法律保護的實證研究》中援引最高檢的數據說,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每年檢察機關受理的打擊報復舉報人的控告在千件以上。《法制日報》在2010年曾報道稱,最高檢的材料顯示,在那些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的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這一報道遭到最高檢否認。
中央編譯局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所長何增科也曾經提供過一個數據,說由某機構評出的改革開放30年10個反腐名人中,有9個曾經遭到報復。
而吳丹紅的上述文章同時指出,發生在舉報人與被舉報人之間的報復性案件,在現實中很難立案。2001年,全國檢察機關初查打擊報復舉報人案件有289件,其中立案偵查14件,占比5%。
1999年最高檢發布的《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對于《刑法》第二百五十四條報復陷害案的立案標準,規定了三個條件:一是致使被害人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或者其他合法權利受到嚴重損害的;二是致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殺的;三是手段惡劣、后果嚴重的。也就是說,只有發生了舉報人的權利受到極其嚴重的損害,檢察機關才會對打擊舉報人的行為進行立案。
舉報人遭到報復的比例居高不下,還有人分析其背后有一個必然的邏輯:對于被舉報者來說,報復舉報人的心理需求自不必說,此外,因為被舉報人大多是舉報人上級,因此被舉報人又通常具有報復的能力。
對舉報人保護不力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相應的法律規定太過寬泛,相關部門很難對號入座。中國保護舉報人的相關規定,散見于從《憲法》《刑法》《刑事訴訟法》,以至最高檢、監察部的部門規章等各個位階的法律中。但上述法律規定,均沒有解決一個分工到戶的問題。《刑事訴訟法》第85條規定:“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應當保障報案人、控告人、舉報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這一規定,將公檢法均列為保護舉報人的主體,卻沒有進一步劃分三者之間的關系,造成的結果必然是“三個和尚沒水喝”。一位省檢察院反貪局的檢察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舉報人保護問題上,檢察院有時候會感覺無從下手。
這位檢察官說,在《決定》的新一版修訂中,提到了舉報人向檢察院求助時,檢察院認為威脅確實存在的,應當及時通知公安部門。“這涉及到公檢兩家的配合問題。需要更高層次的法律規定,不是檢察院一家就能做主的。”
保護舉報人等于提高審判質量
與舉報人保護不力形成悖論的是,中國職務犯罪案件的辦理,對舉報的依賴程度很高。
最高檢副檢察長柯漢民曾在2010年表示,在檢察機關立案偵查的案件中,群眾舉報或通過群眾舉報深挖出來的職務犯罪案件,占立案總數的70%以上。他說,離開了群眾舉報,反貪污賄賂和反瀆職侵權工作將成為無源之水。
群眾舉報既然是檢察機關調查職務犯罪的源頭,保護好舉報人的重要性按說不言自明。但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家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舉報雖是檢察機關破案的最重要的源頭,但就檢察機關整個工作來說,舉報仍處于一個附屬的地位。“檢察機關不是拿到線索就行了,拿到線索后還要去查,還要去找證據,錄口供。”何家弘是最高檢的專家委員會委員,曾在2006-2008年掛職最高檢,任瀆職侵權檢察廳副廳長。
檢察機關對群眾舉報的態度,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即成案率,也就是最后立案數占全部舉報的比例。前述省高院檢察官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對于群眾舉報,檢察機關內部還會分個三六九等,普通群眾的舉報大多成案率不高,成案率較高的,通常是同案犯或者是知情人的舉報,而成案率最高的舉報,是從“案中案”中得到的線索。“現在,通過‘案中案找到的線索,已占職務犯罪線索的一半以上。”
此外,在貪腐比例很高的中國官場,對舉報人的保護就意味著對官員的威脅。也就是說,中國官場的大環境,是不利于形成對舉報人的良好保護的。如果貪腐官員進入了決策層,就更不易形成對舉報人的良好保護。
但在中國推進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舉報人保護正迎來非常有利的時間窗口。何家弘認為,依法治國,必然要求以審判為中心,這就要提高證據的質量,而掌握著證據的證人,有相當大比例來自于舉報人。所以,保護好舉報人,就等于提高了案件的審判質量。
11月2日,十八屆中央紀委常委、最高檢副檢察長邱學強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經中央正式批準,最高檢將成立新的反貪總局,局長由一名副部級檢察委員會專職委員兼任。此前一天,何家弘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透露,新反貪總局是由原反貪總局、瀆職侵權檢察廳和職務犯罪預防廳三個局級部門合并而成。其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整合檢察機關內部的資源,以便在將來的依法反腐中承擔更重要的責任。
“過去,職務犯罪偵查的問題就是力量過于分散,至少有三個部門在管這個事,即反貪局、反瀆局還有職務犯罪預防的部門,他們的一些職能是交叉的,每個部門又都有自己的部門利益,這對職務犯罪的偵查是個削弱。”何家弘說,如今這三個部門整合在反貪總局旗下,更利于工作的開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