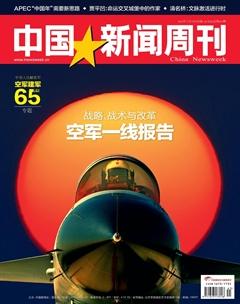APEC期待“中國方案”
徐方清

時隔13年,中國再次主辦APEC會議。上次主辦的2001年,適逢中國剛剛加入世貿組織、并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之后不久,此后的十余年中國迎來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在全球的地位發生了巨大改變,并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再次主辦APEC會議,中國亦有責任將APEC進一步升級,發揮第二大經濟體對全球經濟的引領作用。
11月9日至10日,來自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1500多人進入位于鳥巢和水立方北面的國家會議中心,參加在這里舉行的2014年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峰會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美國總統奧巴馬等多個APEC成員的領導人也確認與會。
《中國新聞周刊》從負責籌辦此次峰會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以下簡稱貿促會)獲悉,參會的1200多家企業和機構來自APEC的21個成員以及其他16個國家和地區,世界500強企業中,有130家赴會。
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國際組織處處長孫曉希望,工商領導人峰會能為APEC的重頭戲——2014 年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開一個好頭,“工商領導人峰會,最大的特色就是領導人和工商界人士間的直接交流。還沒有哪一個平臺,能一下子有這么多的領導人和工商界人士聚在一起。”孫曉說。他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這次峰會的與會人數創下歷屆峰會的新高。此次峰會的贊助商總數亦達到39家,遠超過往屆的不超過30家,“以跨國企業為主的贊助商數量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全球對工商界認可度的高低”。
2014 年APEC領導人會議周從11月5日開始,11日結束。其間,除了2014 年APEC 工商領導人峰會,還將舉行2014 年APEC 最后一次高官會、2014 年APEC 外交和貿易雙部長會議、2014 年APEC 領導人與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2014 年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等多場重要活動。
13年前,“中國聲音”開始響亮
孫曉第一次參與APEC是在13年前,在2001年中國首次作為東道主舉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他擔任會議翻譯。如今,身為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國際組織處處長的孫曉已經參加了各類APEC會議數十次。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簡稱亞太經合組織,成立于1989年11月,澳大利亞、美國、加拿大、日本、韓國、新西蘭和當時的東盟6國在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舉行了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屆部長級會議,標志著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的成立。兩年后,中國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簽署一份“諒解備忘錄”,以主權國家身份加入,并出席了在漢城(現名首爾)的會議。1993年6月,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改名為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已成為亞洲——太平洋地區級別最高、影響最大的區域性經濟組織。亞太經合組織是經濟合作的論壇平臺,其運作是通過非約束性的承諾與成員的自愿,強調開放對話及平等尊重各成員意見,不同于其他經由條約確立的政府間組織。
2000年,貿促會第一次組織中國企業家代表團參加當年的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一年之后,貿促會接到了籌辦在上海舉行的2001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的重任,“當時貿促會還沒有太多承辦大型活動的經驗,只好盡可能地借鑒其他APEC成員之前的經驗,邊做邊摸索”。
當年的峰會晚宴,按照中國的習慣,設了很多圓桌,與會者圍坐在一起。“這樣交流起來很不方便,要是都站起來去串場就亂了。”孫曉回憶。之后多次參與其他APEC成員舉辦的峰會晚宴時,他才發現,晚宴多采用自助餐的形式。讓很多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美國夏威夷舉行的2011年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晚宴,主辦方將海邊的幾家酒店打通,可隨便進入任一家酒店,游泳池、健身房等設施都向全體與會者開放,多家餐廳也提供著風格各異的種種美食,“走到哪兒吃到哪兒,交流到哪兒”。
今年是APEC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也舉行了25次。中國前駐APEC高官王嵎生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從戰略層面觀察,這些年來,除了“茂物目標”外,還有兩個主要成就引人注目:1993年西雅圖會議,領導人莊嚴承諾要“深化APEC大家庭精神”,這是在政治上引領APEC 發展方向。1996年在菲律賓蘇比克舉行的會議上制定和宣布了“APEC方式”,即承認APEC 成員的多樣性(經濟發展水平和發展階段不一樣,社會制度、文化歷史和宗教等都不一樣);允許靈活性和漸進性;遵循自主自愿和協商一致原則,平等互利;集體制定戰略目標,各成員按照自己的實際情況制定達標措施。
“茂物目標”來自于1994年APEC會議,印尼做為東道主,會議宣布要實行APEC 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出了兩個時間表,即發達成員要在2010年完成,發展中成員要在2020年完成。因會議舉辦地是茂物,這被稱為“茂物目標”,是APEC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王嵎生回憶稱,1993年宣布要深化“大家庭精神”時,并未來得及探討具體什么是“大家庭精神”。而“APEC 方式”實際上解決了這個問題,成了“大家庭精神”的靈魂,豐富和發展了APEC價值觀,使其成為“新時期國際合作的全新方式”。
今年已經85歲的王嵎生是中國第二任APEC高官。1993年至1998年,他以中國APEC高官的身份連續參加過6次APEC會議。“這些年,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在APEC平臺上,我對此深有體會。”王嵎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他的記憶里,最初幾年,中國雖然也參加了APEC,但“人家并不怎么重視你”。隨著中國的國力日漸增強,加上對APEC也越來越了解和熟悉,在APEC中的影響力開始變得不一樣,“到了2001,中國首次作為東道主,‘中國聲音就比較響亮了”。
2001年,中國第一次舉辦APEC會議,會議發表了“上海共識”,進一步明確了實施“茂物目標”的戰略。
參與規則制定
“2000年貿促會第一次組織中國企業家代表團參加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時,只有幾十家企業參加,近幾年代表團人數都超過200人,每次都是亞太經濟體中最大的工商界代表團。”孫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人數大幅增加的同時,中國工商界的參與度也在提升。“剛開始,有企業家去APEC就是去看個熱鬧。”孫曉說。在他看來,這一方面是語言受限,在以英文為主的會議上,中國企業家會擔心自己能否表達得清楚;另一方面也和文化有關,相比國外多數企業家的能說會道,中國企業家在公開場合發言的意愿不強。但在最近幾年的會議上,中國企業被邀請做發言人的機會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多的人愿意主動站起來提問。
孫曉的另一個身份是ABAC(APEC工商咨詢理事會)中國秘書處執行主任。ABAC是APEC框架下代表工商界的常設機構,由APEC21個成員每家選派3名工商界代表組成,共計63位。ABAC每年召開4次會議,討論和撰寫工商界的建議報告,在每年一度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交給領導人。此外,APEC領導人與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在參加對話會時,領導人為交流便捷,往往只帶一名翻譯,而不是通常情況下的“前呼后擁”。
身為貿促會國際聯絡部國際組織處的處長,孫曉參與了G20峰會、金磚國家峰會、亞歐會議等很多多邊機制。在他看來,APEC的獨特之處在于其組織架構搭建得很好,保證了工商界的深度參與,是一個比較民主和公正的對話平臺。APEC從一開始的定位,就是加強經濟合作,突出工商界的地位,被視作是PPP模式(“公私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的典范,現在其他的多邊機制,在這方面也在向APEC學習。
中國代表在ABAC的話語權也在不斷增強。2012年,在ABAC工商界的聯合會議上,美國代表提議與政府一同建立糧食安全政策伙伴關系,本意提高自己在糧食安全問題上的話語權。但最終,代表中國的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被選為主席。APEC是協商一致原則,無論成員大小,只要有一家反對,決定就不能通過。而中國更加中立的立場,也更能代表占多數席位的發展中成員的立場,受到他們的歡迎。
“早期的一段時間,中國工商界處于被動守勢,往往提案由別人來提,我們只是對不利于我們的方案‘SAY NO。現在,我們自己也提訴求、建議和提案,主動參與各種對話機制。”孫曉說。中國工商界已經不再等著他人把規則制定好了再進去,“我們也在參與規則的制定”。
此外,APEC作為中國“邊學邊實踐”的平臺的功能依然存在。2012年,在俄羅斯舉行的APEC會議通過了APEC環境產品清單。列入清單的產品,將在APEC地區享受關稅減免的優惠,因此在前期談判過程,各方均試圖在清單中加入更多本國產品,導致談判很膠著。某國家一談判代表索性直接將企業家帶到談判現場,在提到為什么它們的產品要進入清單時,讓企業家自己現身說法。“由于企業家說得非常專業,讓現場其他成員的談判代表很難反駁,畢竟在產品的專業知識上和企業家相差甚遠。”孫曉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這個案例至今讓孫曉難忘。他表示,這值得中國借鑒,以加強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并推動企業參與政府談判形成到機制化。
中國主場的焦點議題
在參與APEC已有十幾年的孫曉看來,從目前工商領導人峰會的議題設置、參會人數和分布來看,今年和往年最明顯的區別是,中國更加自信了。“在議題的設置上,我們充分利用自己的‘主場優勢,主動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比如亞太自貿區,互聯互通,改革創新,這些都更符合APEC國家和企業的利益”。
“而且,我們的利益訴求也能得到其他成員的積極響應和反饋。這也說明,我們和其他成員的‘利益交集也在擴大”。孫曉說。
中國工商界代表在ABAC中的地位提升,亦是中國在APEC框架中影響力提升的一個縮影。在落實“茂物目標”兩個時間表方面,中國采取了實質性行動亦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是今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的主題。圍繞這一主題,今年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確定了三個核心議題,即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促進經濟創新發展、改革與增長,以及加強全方位基礎設施與互聯互通建設。
10年前的APEC會議上,建設亞太自貿區的概念被提出,但在付諸實施上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此番中國在“主場”將這一概念再次激活,是要為“茂物目標”的實現奠定基礎。此外,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亦是為促進區域內硬、軟件和人員的互聯互通,促進經濟持續增長尋找出路。
但目前,硬件設施連接不暢、政策法規規制不協調帶來的物流、人流不暢、人文交流不足,是橫亙在亞太地區互聯互通進程中的三大瓶頸。對此,中國社科院亞太戰略研究所所長李向陽認為,中國提出設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亞投行),意在尋求解決當前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難題之道。
10月24日,21個亞投行首批意向創始成員國的財長和授權代表在北京簽署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備忘錄。作為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亞投行將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區域合作與伙伴關系。亞投行總部將設在北京,計劃2015年底前投入運作。正是在一年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東南亞并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提出了籌建亞投行的倡議。
10月29日,在中國外交部舉辦的第十屆“藍廳論壇”上,外交部部長王毅在發表了題為《北京APEC:中國準備好了》的主旨演講后回答記者提問。針對記者所提關于今年APEC期間中日領導人是否將進行雙邊會見的問題,王毅表示“我們會對所有的客人都盡我們必要的地主之誼。至于影響中日關系正常發展的問題和障礙,這是客觀事實,不可回避。我希望,日本領導人和日本方面,能夠正視問題的存在,拿出解決問題的誠意”。
今年3月,針對俄羅斯向烏克蘭境內派遣軍隊的行為,美國曾代表G7(七國集團)國家組織發表聲明說,抵制原定今年6月在俄羅斯索契舉行的G8峰會,并威脅將俄羅斯“開除”。而APEC再度展現它的包容性。在APEC的21個成員間,存在諸多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等障礙,但一年一度的APEC會議機制保持正常運行,總能為各成員領導人提供一個對話的平臺。本次會議上,除了中日領導人如何互動頗受關注外;美俄領導人是否能打破芥蒂進行實質性溝通亦受矚目;“習奧會”,中美如何商討新型大國關系?習近平和普京今年的第五次握手,是否將給中俄帶向更緊密的關系等等,上述問題在會議上能否出現針對的“中國方案”,更成為外界關注和期待的焦點。如今的國際規則寄希望于多邊合作平臺,而現在主要大國的戰略都在發生變化,開始從多邊合作轉變為區域合作,這也讓APEC的地位更加重要。中國提出的區域經濟合作也將成為這次APEC會議最大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