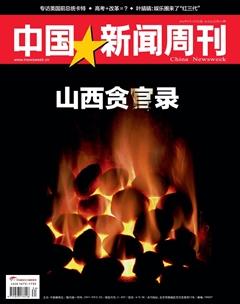大昆明,你煩惱嗎?
劉子倩

2014年8月末,《昆明日報》上的一則消息令人充滿期待,昆明規劃5年后基本建成“智慧城市”,其中一項誘人的內容是,市民出門用手機設定目的地,即可收到系統即時、便捷的交通方案。 然而,一個難解的現實問題是,如果全城皆堵,再便捷的出行方案又如何派上用場呢?
726萬人口,190萬機動車保有量的昆明,在人口增長、城市擴張、千樓一面、歷史文脈斷裂中急速膨脹,也概莫能外地承受如約而至的種種大城市的綜合征:人口快速膨脹,城市布局缺乏前瞻性規劃,基礎設施承載力嚴重不足,交通擁堵,環境污染,秩序紊亂,運營低效……
事實上,在這一系列病灶前,五年后所謂的“智慧城市”似乎更顯得微不足道。曾經“無處不飛花”的春城經歷了數年“無處不飛灰”反復的市政建設之后,盡管一座特大城市的發展輪廓似乎更為清晰,但大城市沖動引擎驅動下的版圖,在瘋狂擴張中,正吞噬著這座城市獨有的性格和傳統。
不斷折騰的規劃
從事54年建筑和規劃研究的朱良文都已記不清昆明市的城市總體規劃變過多少回。在他的印象中,新來一任領導就換一個主意。“一個規劃方案要多次討論、征求意見,意見也只有兩種,一種是堅定地支持的,而另一種是理性反對。”這位77歲的建筑學教授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從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昆明規劃發展來看,昆明的規劃更像是一部缺乏前瞻性的規劃史。1957年,昆明完成了《昆明市城市初步規劃》方案,兩年之后,出臺了《昆明市城市總體規劃》,奠定昆明早期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之后,大變動開始了。昆明市提出了《昆明市城市總體規劃匯報提綱》,在此基礎上編寫了《昆明市城市總體規劃綱要》,并于1982年編制完成了《昆明市城市總體規劃(1981—2000年)》,報請國務院批準。然而,僅5年之后,由于規劃與經濟發展已不相適應,昆明市對此規劃又進行了調整修改。
2002年,昆明對1999年國務院批準的《昆明城市總體規劃1996—2010》再次進行了調整,規劃確定了軸向開拓、自然分隔、組團發展的動態城市布局結構。這次調整的理由是實現新昆明城市定位與發展戰略目標。
實際上,按照此規劃到2010 年, 昆明建成區面積將達到170 平方公里, 而2002 年統計時, 昆明建成區面積已達到180 平方公里。除此之外,規劃另一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就是滇池治理。兩方討論的焦點是遠離滇池發展還是更為靠近。這個規劃的出發點最終基于城市污染源在滇池污染源中占比例相對較大,遠離滇池成為優選方案。當然,最終圍繞滇池發展已是后話。
在2003年之前,昆明一直以“攤大餅”的方式演進,城市建設集中在市中心,人口密度不斷增大,由于昆明只擁有一個商業中心,也就使這座省會城市對周邊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大打折扣。
2006年起,昆明又開始新的一輪修編工作,制定了《昆明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在昆明市人大審議后于2009年上報國務院審批,2011年8月通過了住建部審查。但在國務院批復前,昆明市情再次發生變化,使得這份規劃又一次進行調整,名稱也改為《昆明市城市總體規劃(2011-2020)》。
曾任昆明市規劃局副局長的葉建國曾向媒體感嘆,昆明經濟的發展速度超出想象,而規劃只是跟著開發商的項目走,心中無數。而作為專家,朱良文多次參與規劃征求意見的討論,但最終采取何種方案專家并不知情,“最后結果有時還是非專業人員透露給我們的。”
學者們發現,1982 年、1993 年和2008 年版《昆明城市總體規劃》沒有提出完整的城市空間形態的內容。只在2002 年《昆明城市總體規劃調整》中初步提出了“昆明主城區空間景觀初步概念規劃”,但未獲批準。2008 年初步完成編制和審批的《昆明主城55 分區控制性詳細規劃》,雖完成了道路、重要公共與市政基礎設施體系和用地控制規劃,但沒有完成系統的城市空間形態控制專項規劃,僅依據2002 年版“昆明主城區空間景觀初步概念規劃”對主城建筑高度、容積率的布局和分區做了研究。
2004年任昆明市市長的王文濤也看到規劃存在的問題。他曾直言不諱指出,自上世紀90年代起,昆明進入城市化高速發展期,因為不科學的發展觀,造成了城市諸多問題。
消失殆盡的城市性格
1982年,昆明成為中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傳統建筑和老街是其獨有的特色和景觀。在昆明的傳統建筑中,大致分為古建筑、民居建筑和近代建筑,其中古建筑多為寺廟及道觀, 布局規整, 有嚴謹的中軸線, 院內有花園庭院,傳統民居也很講究,平面設計緊湊合理, 內院小巧, 在全國傳統民居建筑中獨樹一幟。
但此后的近二十年中,或大或小的拆遷更像是昆明的自我告別。曾任昆明市城鄉規劃建設專家咨詢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組的召集人的朱良文還記得,在拆除頗有代表性的武成路前,曾經經過大量的論證,仍未有定論。然而,當他得知要拆的消息,第二天帶著研究生們奔到現場時,老街已經沒了。
事實上,傳統街道街坊是構成城市特色和景觀風貌的重要基礎,它在傳統風貌與現代風貌中能起到重要的過渡作用。而在昆明,體現城市形態的四個方位的城門早已拆除,古城墻早已蕩然無存,而昆明傳統中軸線上的建筑也已不復存在,唯一存在的地標性建筑金馬碧雞坊也是1998年仿建的。
“城市發展面臨著交通等多方面的壓力,老街不是一點都不能動,但要權衡利弊,選取一個折中的辦法。否則你把真的老街拆了,再新建假的,還有什么意義呢?”朱良文感嘆道。
老昆明保護研究者、云南歷史學者雷強曾通過一個政協委員朋友遞交提案,即便老街和建筑無法保留,也應盡量保存老的街名,或者在某些消失的建筑和歷史發生地,樹個紀念牌。“這是沒有辦法的辦法,還能怎么樣呢?”雷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若干年前,昆明市規劃局的一位局長曾對雷強說,如果當年規劃時,不拆武成路等老街,如今的昆明或許是另一個樣子。雷強清楚,這只是局長私下感慨而已,在轟鳴的推土機和吊車面前,錯綜交織的利益以及強心劑般的GDP驅使下,這注定難以實現。
上海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規劃師朱琳為昆明的城市化進程頗為憂慮。他在“2012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上曾發文指出,昆明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 城市特色似乎黯淡, 特色危機令人擔憂。“由于種種原因, 古建筑己趨破壞殆盡, 府城內現代建筑風格各異,辦公、商業、住宅建筑襲南繼北, 根本不能與古城原有建筑風格相協調, 建成環境的特色不明顯, 昆明正從一個歷史悠久、城市特色鮮明的古城變成一個缺乏地域特色、千城一面的城市, 城市魅力在喪失。”
他建議,應充分地保護好圓通山、五華山等山體山貌, 嚴禁任何形式的山體破壞, 城區的建筑的高度應該進行一定的控制, 避免作為城市天際線的山體的破壞。
然而,昆明的高樓卻屢創紀錄,從早期的150米,升到200米、300米,再到456米的樓王,如今近20座150米以上的高樓將在2015年封頂。在一線城市的摩天大樓熱的躁動之下,昆明似乎并不想置身事外。
另外,昆明位于云貴高原中部,三面環山,一側臨水,氣候四季如春。城中盤龍江等河流穿城而過,倚山面水,是典型的山水城市格局。
然而,這種鬼斧神工般的山水格局也遭受著人為破壞。環滇池的高速在滇池西側部分緊貼滇池而過,甚至建有跨橋。這使得原來山與水的聯系完全被割裂,整個山水環境以及動植物的生態環境都會受到嚴重的破壞。
在雷強看來,昆明規劃亂象更多的源于錯誤的城市定位,揚短避長,領導好大喜功,拼命把城市做大,反而這座城市特有的東西漸漸丟失了。“所以,昆明的總規劃師不是什么專家學者,永遠都是市委書記。”雷強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如何遏制大城市沖動
盡管昆明的城市特色漸漸消失,但在對外宣傳上卻頗下功夫。2000年1月1日,央視在黃金時段播出中國第一個城市形象廣告:昆明天天是春天。一時間,這也成為昆明旅游的宣傳語。2004年的旅交會上,昆明街道的路燈桿上,又打出了讓人耳目一新的廣告標語“您昆明了嗎 ?”引發全國熱議。
事實上,從那時起,昆明已摒棄了“攤大餅”的發展模式。2003 年5 月底,云南省委、省政府召開昆明城市規劃與建設現場辦公會,提出以滇池為核心的“一湖四片”(主城片區、呈貢片區、晉城片區、昆陽-海口片區)、“一湖四環”(環湖截污、環湖生態、環湖交通、環湖新區)的現代新昆明發展戰略。按照此戰略,昆明城區面積將從原有的180平方公里發展到460平方公里,人口將由245 萬發展到450 萬。
新增的城市與交通用地約為288.5平方公里,而滇池的水面為300平方公里,這就意味著新增的建設用地將與滇池的面積相差無幾。由此,滇池也將成為城市的中心。
朱良文對于這一戰略并不太贊成。“本來滇池已經被污染了,圍繞著它來建設,人口壓力越來越大。”朱良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此之前,已有權威的數據表明,人口增長對水質有著極大的影響,“數據很有說服力了,你還要圍繞它來發展,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原來還征求我們的意見,后面就無聲無息了。”
盡管十余年來,昆明實施此項戰略發展迅猛,但雷強仍憂心忡忡。如今昆明人口迅速增長帶來最為棘手的問題就是水資源的匱乏。從2009年開始,昆明正式成為一座名副其實的“缺水之城”,位列全國14個缺水城市之一,其中人均只有約300立方米,與嚴重缺水的以色列極為接近。
以2013年清明節為例,三天假期,市長熱線的撥打量為個4025個,停水停電、疾病預防控制、交通擁堵、噪音等成為焦點問題。而停水主要原因是昆明持續干旱,水壓較低。
在“一湖四片”的規劃中,呈貢新城的建設最引人關注。2008年起,云南多所高校遷至呈貢大學城。2011年,昆明市行政中心也遷于此。
根據統計數據,大學城有超過10萬名師生,行政中心的人數達七千多人。教師與公務員均在市區居住,距呈貢15公里,這就造成了早晚上下班的人流“鐘擺”式移動。按昆明交警部門統計,呈貢新區機動車交通出行總量約在15000 輛/ 天,出行時間、路線集中,造成主城區與呈貢的道路嚴重擁堵。而據《2012昆明城市交通發展年度報告》,昆明晚高峰一環內平均車速為9.42公里/小時,甚至低于北上廣等一線城市。
顯然,如何緩解交通壓力,已成為完善昆明城市規劃的重要一環。
新昆明城市規劃中提出要把昆明打造為“東方日內瓦”。然而,日內瓦州的面積為282平方公里,全州人口只有37 萬人, 日內瓦市人口18 萬人。與此相比,昆明城區面積為212公里,但常住人口就已經超過600 萬,兩者很難相提并論。“我很反感這種提法,昆明就是昆明,你要打造自己的特色。”朱良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2013年9月,在一次會議上,云南省委書記秦光榮亦對昆明規劃建設提出六點批評,大山大水空間格局被破壞,城市缺乏個性,基礎設施建設缺乏統籌,城市管理缺乏戰略眼光,歷史文脈被割裂,對昆明歷史文化造成毀滅性打擊。
實際上,早在2009年4月,昆明市規劃局副總工程師周杰曾在《昆明日報》上撰文指出,與內陸大城市相比,昆明滇池盆地空間尺度和環境容量十分有限。昆明城市形態、特色、風貌定位,不應以城市規模、宏大的現代化城市中心區等方面取勝,應針對昆明城市特點,大力塑造時尚儒雅的城市形態及風貌,以時尚的湖濱山水環境特色提升昆明的知名度和競爭力。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以及各種交通設施的日益完善,昆明作為橋頭堡的作用日益顯現。2014年7月,由昆明市規劃局制定的《昆明城市區域發展戰略與遠景規劃》日前出爐,將昆明城市總體定位最終確定為:“中國面向東南亞、南亞開放的門戶城市,世界知名旅游城市和宜居城市,西部地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這更像是一種回歸。
但在這之前,一組數據似乎已表明市民對于這座城市現狀的不滿。由首都經貿大學與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聯合成立的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發布的“中國35城市生活質量報告”中,昆明的生活質量滿意度(主觀)指數排名,從2012年起每年下降一位,由2012年的倒數第四降至2014年的倒數第二。
時間回到2003年,在點評昆明主城核心區概念規劃國際征集方案時,國際知名建筑師埃里克森當時的一句話,如今看來更像是說給十年后的昆明:“對一個城市來講,它的精髓是什么?不是你建了多少高大的建筑,城市迷人的東西是居民自由自在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