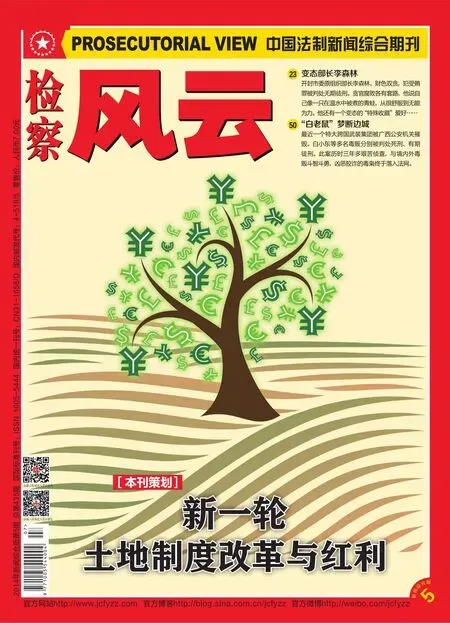傷及官場生態的圈子文化
文/四賓
現象:“拔出蘿卜帶出泥”
近些年來,社會上流行一句話:“進了班子還要進圈子,進了班子不如進圈子,進了圈子等于進了班子。”從某種程度而言,官場頻頻出現“圈子”現象已成為常態,圈內以“核心人物”為中心,以利益、權力為考量標準,排除異己,踐踏法律法規。
國家有關制度對于“圈內人士”并“不適用”,因為,圈子中有圈子中的“潛規則”,他們稱兄道弟,通過“政商勾結”“官官相護”將金錢與權力掛鉤,使權力依附金錢,進而破壞法律法規,為圈子內部撈取社會資源。
似乎從人來到這個世上,就無形中需要某種結合,單槍匹馬對于每個生命體而言略顯單薄,結合也不失為一種生存之道。從古至今,社會各階層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想方設法來搭建自己的“圈子”,上自“達官顯貴”“社會名流”,下至“販夫走卒”“三教九流”皆不例外。的確如此,在各自的圈子中,每個人以不同的紐帶為半徑,通過各種方式來經營自己的圈子,在中國人看來,圈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關系第一,原則第二”很多時候是官場“圈子”辦事準則。只要關系好,原則可以放棄,制度可以變通。別人辦不成的事,圈子中的人可以破例。山東政法學院教授李克杰認為:“領導干部搞‘圈子’的特殊性在于,一旦濫用權力或搞權力尋租,就會給自己及其圈子內的人帶來某種政治或經濟利益,從而使這個‘圈子’改變性質,成了‘小圈子’。”
圈中的人物關系十分復雜,不僅囊括血緣關系,也涵蓋社會關系。例如,2008年12月8日,安徽省淮南原市委書記陳世禮(正廳級)因索取或收受賄賂款物達600多萬元,被該省阜陽市中級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死緩。據悉,陳世禮就有自己的“圈子”,“圈子”的圓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他的家人和親戚;二是他那幫搞建筑工程和房地產開發的老板朋友。這兩種人互為利用,互相關照,共同“結盟”在陳世禮的麾下。
此外,一些地方的官場“圈子”涵蓋的人數多、地域廣,而且牽扯的部門也不少。2011年4月28日,東方網報道,茂名原市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羅蔭國網羅200多名官員,在當地交織成一個“權力共有、財富共享”的相互庇護的關系網。茂名重大系列腐敗案涉及省管干部24人,縣處級干部218人,波及黨政部門105個,市轄六個縣(區)的主要領導全部涉案。
2012年5月22日,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涉案總金額高達3.7億余元的溫州菜籃子集團原董事長應國權等16人腐敗窩案作出一審判決,其中包括董事長兼總經理應國權、黨委書記兼副董事長郭洪遠以及九名副總經理、三名總經理助理、人力資源和財務部門處長各一名。
2013年8月底開始,中石油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反貪腐風暴,相繼有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王永春、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等四位高管,涉嫌嚴重違紀,被組織調查并免職。9月1日,這輪反腐大戲再掀高潮:國資委主任、黨委副書記、中石油集團原董事長蔣潔敏亦告下馬。據悉,王永春、李華林、王道富、冉新權四人,與蔣潔敏關系密切,四人幾乎都是在蔣潔敏執掌中石油時得到提拔的。
當然,類似的“拔出蘿卜帶出泥”的現象在官場中并不少見,從以往已經曝光的窩案中我們足可窺探一斑。誠然,官場圈子文化并不是在任何一個地方都有,但是,其并不少見。圈子的出現,將原本處于職能需要的正常隸屬關系異化為稱兄道弟的哥們義氣,在利益和權力的誘惑下,彼此間結成了打手、幫兇。此景無疑會傷及官場生態,損害國家機構的形象和公信力。
官場圈子文化的運行規則
人民網曾做過一項調查,在8200多名調查對象中,85.04%的受訪者認為身邊的領導干部有自己的“小圈子”,而且相當普遍。75.70%的受訪者認為“小圈子”里的“小兄弟”是“心術不正、趨炎附勢的人”,87.16%的受訪者相信,結交“小兄弟”是因為“具有某種共同利益”。
誠然,大大小小的“圈子”要么處于利益的誘惑,要么處于權力的牽絆,以核心人物為圓心,以其權力的影響力和影響范圍為半徑結成了一個集團。在這個集團中,集團內部的人無論是在職位升遷還是物質回報等方面都享有特權。這是官場圈子之所以能夠做大做強的原因,在核心人物的“庇護”下,圈子成為了進可攻退可守的“碉堡”,成為了權力場上拼殺的戰車,由于碉堡中、戰車上的所有人看中了這種“圈子”割據的“安全性”,以及對于權力、金錢的調動能力,所以他們千方百計要么通過血緣關系、要么通過社會關系躋身圈中。
正如有的社會學家認為的那樣,“圈子腐敗”之所以受到貪官們的青睞,主要原因是它能給圈內人帶來更多的安全感,具備優于其他作案方式的特點。當然一旦官場圈子面臨外來力量的“挑戰”,他們會以核心人物“馬首是瞻”,以此應對外部風險。
此外,因為官場圈子具有隱蔽性,所以往往是不能放在臺面上來說的,圈中人物之間通過權力關系、經濟利益結成了“死黨”。他們通過自己手中現存的權力或者金錢“入股”,從而為彼此謀取利益。當然圈子內部也可能會因為利益問題產生矛盾,但是在圈子核心人物的影響下。圈子依靠潛規則往往能夠達成“和解”,畢竟只有對外的權力擴張、財富聚斂才是整個圈子的“生存之道”。長期行走于官場而不敗的每個個體,諳熟此中的真意,在官僚文化的浸潤下,圓滑處世的為官之道似乎成為了圈子中的潤滑劑。
從整個官場來看,官場圈子無疑會形成“權力割據”,大大小小的圈子自有運行規則。一些地方、單位內部圈子之間往往“官商勾結”“官官相護”,致使帶有公共屬性的國家權力成為官場“圈子”之間拼殺的戰利品。在權力的誘惑下,官場圈子很容易擯棄理性,摒棄人性,摒棄法律、道德。一切來自“圈子”外部的約束將會被視為“肉中刺”“眼中釘”,地方與中央通力合作的政治格局會在潛移默化中被異化。
其實官場圈子最大的特點是它的等級性。在官僚科層制下,每一個官員都可以在不同的等級中找到與其權力對應的位置。在權力為核心的官場中,官場圈子以核心人物為中心,按照權力大小、財富比重、社會地位等將圈內的人分成“三六九等”。這種以權力為內容結成的隸屬關系在官本位思想的浸潤下,使得圈中的成員失去了衡量是非的標準,對與錯、好與壞并不重要。核心人物怎么說,就怎么辦,核心人物說什么,就是什么。
同時,即便是圈子內部資源的分割也是以等級高級來分配的,權力大的,資金足的,地位高的就分的多。當然這種方式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圈子內部的矛盾,克服了圈中因分配不均而產生的諸多內耗。加之,有核心人物的掌控,圈中的運行有條不紊,然而一旦核心人物出了問題,那么圈子中以往積壓的矛盾便會在瞬間爆發,圈子的體系瞬間崩塌。
總之,官場圈子文化的運行規則是以權力、財富入股,在核心人物的領導下向國家法律法規叫囂,圈內利益的最大化是圈中成員行事的最終目的。在圈子文化的影響下,圈中的個體會喪失自己最初的公仆意識,哥們情結成為他們最高的“操守”。
官場圈子文化危害不少
2013年1月,檢察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地方官員進京潮揭秘:只有融入那個圈子才有提拔機會》的文章:湖南某市秘書長說,來北京辦一些會、跑一些項目,無非是想讓組織部門、部委和一些領導看見自己的政績、認識一下,在地方人事格局尚不明朗的情況下,借會議來探探路,也是人之常情、常規手段。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在人情社會關系復雜的今天,官場圈子的出現無疑開辟了一條官員晉升的“潛規則”,在正規的人事晉升渠道不暢通的情況下,通過圈子核心人物的提拔,獲取晉升機會,并為核心人物充當“小弟”便成為官場惡生態。
然而,如此一來,官場“逆淘汰”就會因為“潛規則”而發生。一些政績卓著的官員,本來按照規定可以晉升,但是因為官場圈子文化的出現,官員的晉升往往使用“自己人”,有好處也是給“自己人”,是非標準往往會被顛倒。此舉不但影響官場風氣,而且會影響行政的運作效率。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教研部副主任、教授趙豐指出:“領導干部一旦產生‘小圈子’意識,那么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就會首先圍著自己的‘圈’內人的利益轉,選人用人首先考慮的是自己圈子內的人。你是我這個‘圈子’的人,不管你德才如何,都委以重用。不是這個‘圈子’的人,不管你多有才干,就是不用。”
誠然,官場圈子文化就是官員之間“拉山頭”,在一些單位,往往存在多個“山頭”,不同的領導往往為了角逐權力,采取在機關單位內部搞“小團體”,從而導致機關內部出現“近情關系”,甚至“人身依附關系”。對于核心人物而言,其或者依靠縱向的血緣關系將公權力私有化、家族化,通過潛規則安插“親信”進入不同部門,攫取公共權力和公共資源。或者通過橫向的姻親關系將不同的官場圈子黏合起來,實現權力聯盟,或者通過圈中的姻親關系調節圈中矛盾,強化個體之間的“依附關系”。對于圈內的非核心人物而言,他們通過同學關系、同鄉關系、同事關系、戰友關系……想方設法參與其中,力圖以此在權力內部分得一杯羹。
然而,有些干部坦言,進圈子是身不由己,現在官場競爭這么激烈,有人幫忙或者關照的話,仕途便會順利一些,有時候遇到難題,能有個志同道合的人商量,幫著出主意,也是好的。如果完全置身“圈”外,很可能被排擠、邊緣化。
從圈子建立的那一天起,其使命就是指向權力或者財富的,所以在這種目的統合下,圈中個體不再是“人民公仆”,他們對內拉幫結派消解行政資源,對外權力自肥聚斂財富。這樣一來,就為行賄受賄者提供了契機。行賄者在官場圈中尋覓適合的人選,手握公共權力的“圈子”變成了權力尋租的平臺,“官商勾結”“官官相護”成為必然。近年來窩案、串案便是佐證。橫向聯成一“窩”,縱向結成一“串”。一案帶出一窩,倒下一人牽出一片。蔣潔敏如此、劉志軍亦如此。
正如趙豐教授所說:“‘圈子’本身并無大錯,但‘圈子’一旦成為官場腐敗交易平臺時,其破壞力相當驚人。從現實暴露出的許多案例可以看出,搞‘圈子’腐敗的人,輕者是非不分,重者貪污腐敗。‘圈子’的本質就是利益聯盟,利益是‘圈子’的潤滑劑。結‘圈’之人心態各異,但目的無非是為了從‘圈里’獲得好處,達到權力的利益共享。”
確實如此,一些地方出現官場“圈子文化”的危害是顯而易見的,他們使公共權力異化為私權,成為自己的囊中之物:或在任職任免中稍稍傾斜,或在地方撥款中私開綠燈,或在工程建設中閉一只眼……圈中的“照顧”不但成了圈中人物權力自肥的契機,同時,也成了“大哥”與“兄弟”之間隔閡、摩擦的潤滑劑。就這樣,圈子文化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生根成長。
如何治理官場圈子文化
如何整治官場圈子文化?筆者認為首先是要從核心人物下手。眾所周知,官場圈子的形成或崩盤往往是與核心人物的命運息息相關,核心人物手握什么樣的權力,權力的大小,權力的重要與否決定著這個圈子的人數,圈子的輻射范圍,以及圈子危害的大小。即便是整個圈子內部的秩序也是由核心人物所維持,如果沒有核心人物的存在,圈子的向心力便會喪失。因此消除官場圈子文化必須從核心人物下手。
核心人物之所以核心就是因為他長期身處官場,對于官場文化了如指掌,并且建立了一系列錯綜復雜的官場、社會關系網絡。最為關鍵的是,他手中握有的權力已經足以形成對一定社會資源的調動力,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弱、下級監督太難”的監督格局下,權力濫用便成為了必然。所以,必須加強對領導干部權力行使的監督力度,要防止領導干部權力濫用。
此外,除了在監督上下工夫外,制度建設也需要及時跟進,要堅決執行官員回避制度。近年來,從一些“火箭”提拔的案例中不難看出,一些機關單位權力近親繁殖的現象日漸嚴重。以血緣關系、社會關系為紐帶搭建官場圈子的事情并不少見,其中尤其表現為三同一戰(同學、同事、同鄉、戰友)。很大程度上與官員回避制度執行不夠有關系。須知,一些地方、單位如果同學、朋友、親戚扎堆,必然會形成官場圈子,很容易導致徇私舞弊、公權私用現象的發生。即便是“一把手”守身如玉,但是畢竟領導干部是社會性的人,其社會關系、人情世故往往使其在公與私之間很難抉擇,稍不留意便會誤入歧途。
同時,干部之間、官商之間不能“勾肩搭背”,要杜絕利用同學會、培訓班等形式“拉關系”“套近乎”。謹慎交友,要分清什么樣的人可以交往,什么樣的人不能交往,不能結交一些沒有原則、沒有黨性的“小人”。現如今,人與人社會關系的發展越來越多樣化、復雜化,隨著社會利益的多元化,很容易被一些心懷叵測的“小人”所以用,有的人費盡心思、絞盡腦汁通過親戚找親戚,通過朋友尋朋友,目的就是拉關系,就是結“圈子”。所以,作為領導干部要潔身自好,認清誰才是真兄弟,誰又是“偽君子”。要樹立交友的標尺,要結交益友、良友,不交無德之人、不交無義之人、不交無恥之人。同時,要分清楚交到什么程度,要分清楚那些是私事,那些是公事,不能將酒肉關系、哥們義氣帶到官場,帶到自己的工作中去,避免身陷泥潭,不能自拔。
從一些落馬貪官的懺悔中,我們不難看到他們在交友中的悔恨,有的人交友是為了進“圈子”,有的人交友是為了將別人拉進“圈子”,一旦成為圈中之“物”,其仕途、人生、家庭便在不由自主地與圈子“共進退”,注定成為人生的敗筆。
正如江蘇省泰州市委組織部研究室主任陸彩鳴所說:“領導干部要破除‘小圈子’的關鍵在于加強黨性修養。一個領導干部,如果能夠自覺地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不搞‘小圈子’,那些溜須拍馬、投機鉆營之徒又怎能近得了自己的周圍?自己又怎能陷入‘小圈子’里而不能自拔?所以,領導干部要加強黨性修養,做一個‘高尚的人’。”
總之,官場“圈子文化”說到底是一種為了謀求權力、金錢而結成的權力聯盟,它給官場生態帶來嚴重的危害。為此需要領導干部廉潔自律,需要加強權力監督,需要健全制度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遏制官場圈子文化對公共權力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