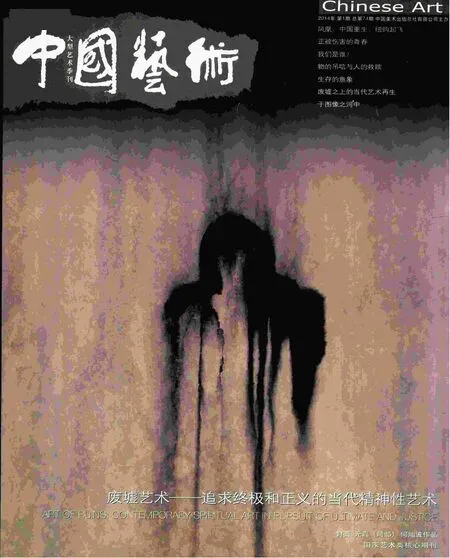于圖像之河中——赫爾加·麥斯特對話比亞特·斯特魯利
王文婷/譯
(注:由于篇幅限制,采訪內容有部分刪節)
編者按:攝影藝術家比亞特·斯特魯利1957年出生于瑞士小城阿爾特杜夫(Altdorf),曾在羅馬、巴黎和紐約生活與創作,現主要工作、生活于蘇黎世、杜塞爾多夫和布魯塞爾。赫爾加·麥斯特與藝術家在布魯塞爾見面并進行了對話。正是在布魯塞爾,藝術家創作了作品“世界圖像”系列,展示了一些對鏡頭渾然不覺的人們。這次對話從藝術家的生平、習畫經歷進入,進而談到設備、技術,最后進入時間、記憶與生活的哲學層面,由遠及近地展現了這位攝影藝術家的創作思路及藝術思考。《藝術論壇》雜志總第214期(2012年3—4月)刊發了此次對話,本期“域外傳真”將二人的對話翻譯成中文,以饗讀者。

圖1 比亞特·斯特魯利在布魯塞爾的工作室中 2011年 攝影者:Helga Meister
赫爾加·麥斯特(以下簡稱H):我們從你的履歷開始聊吧。你是瑞士人,1957年生,生于阿爾特杜夫,請問此為何地?
比亞特·斯特魯力(以下簡稱B):在瑞士中部,就是威廉·泰爾(譯注:瑞士自由斗士W ilhelm Tell)中用弓箭射中放在他兒子頭上的蘋果的地方。
H:你來自怎樣的家庭?你的父母和藝術有什么關系嗎?
B:沒有,我來自一個普通的瑞士中產階級家庭。不過我只有在很小的時候住在阿爾特杜夫,之后就搬到蘇黎世附近。最近我在老家阿爾特杜夫為當地一家藝術療愈中心做了一個公共藝術項目,用透明的大幅兒童肖像裝點這家藝術療愈中心的窗戶。在創作這個項目的過程中,我才得以和童年時期的家鄉風景重逢。
H:你在1977年進入蘇黎世和巴塞爾的美術學校上學,但前后只上了三年。你當時學的是什么?

圖3 Retiro Bs As 亞克力盒子上有色印刷 150cmx200cm 2011年 比亞特·斯特魯利Beat Streuli

圖4 曼哈頓09 廣告版數碼印刷 150cmx225cm 2009年 比亞特·斯特魯利?Beat Streuli
B:我先在蘇黎世美術學校讀自由藝術預科,主要學習繪畫——這是當時在瑞士德語區學習藝術的唯一選擇。我的老師是弗蘭茨·費迪爾(Franz Fedier),一位抽象畫家,他的繪畫從沒有形體發展到有清晰明確的形狀和色域。
H:這種形狀清晰的抽象藝術對你的創作有影響嗎?
B:對我來說美國的極少主義藝術更有影響力。我當時仔細研究了唐·賈德(Don Judd)和索爾·勒維特(Sol Lew itt)的雕塑。對我而言,關于載體與表面、邊框與實體的基本問題更加重要。
H:邊框和你的作品有什么關系?
B:我們必須隨時記住,照片也是一個實體,可以說是一種非常平面的雕塑,因此內部和外部的邊界是清晰可辨的。
H:也就是說,在你轉向攝影之前,先把20世紀的前衛藝術學習了一遍?
B:是的,對我來說經典前衛藝術的終點就是美國的極少主義藝術,比如羅伯特·萊曼(Robert Ryman)的白色方形。在此以后,年輕藝術家已經不能再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前行了。在此背景下,我認為攝影就是開拓新道路的理想工具。攝影的歷史與前衛藝術史不同,它是平行于前衛藝術發展史的另一條線索,藝術家從中能學到另一套東西。
H:你當時是怎么作畫的,都畫了些什么作品?
B:我學習了素描、水彩和拼貼,此外還用現成品進行創作。比如格哈德·梅爾茨(Gerhard Merz)對我就有很大的影響。當我上學的時候,他的綜合材料和字牌作品正好在蘇黎世展出。他的純粹主義構圖在當時令我耳目一新。當我感到在瑞士已經無法繼續深入地學習藝術時,我就到柏林藝術學院(HdK)訪學,并開始了一段四處漂流的歲月。
H:你是怎樣受到人們注意的?
B:那時在瑞士的各大藝術展覽館里有所謂的“圣誕大展”,每個人都可以送自己的作品去參展。我在讓-克里斯多夫·安曼(Jean-Christophe Amm ann)任館長的巴塞爾藝術展覽館參加了圣誕大展,此后他就開始資助我的藝術。我在他那兒展出的是一組黑白照片拼貼,由字跡、碎片和一些具象元素構成。我在藝術博物館的第一次展出是在1986年的阿爾高爾藝術博物館(Argauer Kunstmuseum),當時的館長是比亞特·維斯莫爾(Beat Wismer),他現在任職于杜塞爾多夫的藝術殿堂博物館(M useum Kunstpalast)。
H:但今天你的藝術履歷是從30歲才開始的,當時你在巴黎、羅馬和紐約居住和創作。這是怎么回事呢?
B:當時我想繼續探索國外的生活,也想繼續待在大城市。我30歲時在一筆畫室贊助金的資助下來到巴黎和羅馬,有機會在那兒作豐富的攝影探索。之后我出版了關于羅馬和巴黎的攝影集,其中有很多建筑元素,也有電影式的——公路電影風格的圖像。這本攝影集幫助我獲得了紐約P.S.1的贊助金。
H:我讀到,你15歲時得到一部相機,17歲得到一部長距鏡頭。是這樣的嗎?
B:是的,我有一間小小的暗房,攝影是我青少年時期的愛好。
H:長距鏡頭的原理是用望遠鏡片把遠處的物體放大,從而達到視覺上拉近距離的效果。它的焦深很淺,只有當試圖銳化主要對象時才會使用這種鏡頭。你為什么對長距鏡頭產生興趣?
B:對我來說,比起將遠處的物體拉近而言,長距鏡頭焦深很淺的特質更有意思,它使得畫面的背景變得非常模糊。這種視覺效果更貼近于人類的肉眼和大腦功能,因為它們總是立刻把不重要的事物忽略不見。人們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人們與之對話的對面之人的臉上,因此透過中等長距鏡頭的觀看模式更貼近于人類的目光。

圖5 比亞特·斯特魯利2009年的燈箱裝置《La Voie publique》是根特市圣彼得站永久裝置的一部分Beat Streuli
H:當你用長距鏡頭創作時,你和對象之間明顯有很多的空間。你是否試圖通過這種方式制造某種“軟性”的效果?這樣的圖像和托馬斯·魯夫(Thomas Ruff)的人物肖像所具有的那種銳利的質感顯然不同。
B:對我而言,對現實進行可觸可感的重現一直很重要。極度的銳化,即人們可以看到照片上的每一處細節,是有悖于我的這一目標的。觀眾不會因此而獲得對外部真實的銳利觀看,而是正好相反。這樣的畫面仿佛在眼前樹立了某種過于光滑的表面,觀者很難透過它看到真正的外部世界。我們肉眼所見的真實并不像照相寫實主義所表現的那樣。肉眼的觀看永遠存在某種介于清晰、不清晰和運動之間的區域,正因如此才使觀看具有了感官的愉悅。這樣所見的真實才顯得那么近,那么具有觸感。
H:你的照片誘使我走進圖像里,也包括走進圖像所展示的內容里。
B:我想要在攝影中達到一種開放性,通過這種方式,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感受投射在我的作品里。同時,我也不希望對觀者的視線作過多的引導。
H:現在你是用相機還是攝像機創作?
B:我從很早開始就一直在使用相機之余也使用攝像機創作。現在我們到了一個有趣的時間點:因為相機和攝像機越來越成為一體,所以人們可以用相機拍出同樣好的視頻。這對于攝影來說具有革命性的意義,雖然看起來這不過是技術上的一個小進步。自此以來,我的作品就處于運動畫面和靜態畫面之間的交接點上,而二者也因此變得更加彼此接近。由此產生的是一種全新的視覺思維方式。
H:你會使用視頻中的截屏嗎?
B:視頻截屏的表現力還是遠遠遜于照片,它的圖像質量不足以達到我的目標。但話說回來,視頻圖像比從前更接近于照片,因為它是用同一臺相機、同樣的傳感元件拍攝同樣的對象。從所有的圖像參數——色相、景深等等來看,它都非常接近照相出來的圖像,所以我就可以實現圖像和影片的無縫融合。除此之外,我可以在一兩秒鐘之內用一臺相機拍出十張連續畫面,從中選出我認為最優的。但我估計,再過兩年人們就可以直接用攝像模式拍攝這樣的連續影像,并從數百張靜態高清畫面中挑出最好的。這樣,一張張靜態的圖像又將重新融入時間的河流,這簡直太神奇了!至于到那個時候,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攝影是否還作為一種取像技術繼續存在,我是不知道的。而這對未來的視覺語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實在是一個令人興奮的問題。

H:這樣的發展和你的創作是相對立的,你一直在捕捉動態的瞬間。
B:我從來不認為作為技術媒介的攝影或者錄像截屏是個問題。我從來就可以使用一切合適的工具,只要它能幫助我轉化和再現真實。
H:你的照片序列有一種音樂的韻律感。運動的瞬間,停止和前進。這種時間性總是默默地發生。時間的運轉、運動過程的放慢對你來說重要嗎?
B:節奏是一種基本的東西,它為一件作品提供了結構性的基調,與人類的感知體系形成平行和共振。我常常在創作中使用慢動作,不過它始終只是達到目的的工具而已。它是為了更好地用視覺方式呈現流動性的東西。話說回來,的確有這樣一個問題:當人們把一部影片無限放慢時,它最終會不會變成照片?
H:何謂定格,它算是一幅單獨的圖畫,一張照片嗎?
B:我們可以把照片視作時間的停留,或者對時間的截取。這是兩種不同的視角。對時間本身的認識也可有兩種不同的角度,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可以認為,人們通過時間從開頭走到結尾;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認為,人們是靜止的,而時間從人的身邊呼嘯而過,好像一列火車那樣。有趣的是,照片在我們的視覺世界里總是具有一種極大的精確性,盡管隨著多媒體科技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時間性的記錄工具可以供我們選擇。
H:你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呢?
B:如果照片足夠好,它就可以包含拍照這一刻之前與之后的信息,以及許多其他信息。它是感官圖像,也就是有靈的圖像,或者適合于我們記憶生成的圖像。也就是說,它將許多個瞬間和許多種角度融匯凝結成一個綜合體,這種綜合體顯示出一個情境或一個人的整體面貌。在這點上,照片和電影相比而言更加集中、更加有效果。此外就和繪畫一樣,照片也能使創作者的視點得到具象化的呈現。有一些照片因此可以成為一個時代的圖標,或成為某種圖騰,這就遠遠超越“凝固的瞬間”這一意義了。

H:在談論你現在的作品之前,我還是想先了解你是怎么走到今天這一步的。回頭看來,你好像一開始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似的。但現實幾乎不可能這樣發展。你沒有受過系統的攝影教育,也不屬于所謂的“貝切爾的門生”(譯注:即“新客觀攝影”發起者、攝影藝術家貝切爾夫婦——Be rnd & Hilla Becher——在20世紀末培養的一批攝影藝術家)。正因如此你能夠發展出自己獨特的東西。請問你是什么時候去杜塞爾多夫的?
B:20世紀80年代末。但我當然不認為自己是所謂杜塞爾多夫“學派”的成員。換言之,杜塞爾多夫也不只是貝切爾師生的天下。2009年在巴黎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杜塞爾多夫攝影展就展示了這一區域攝影作品的多樣化。
H:人們可以分辨出你照片的地域性嗎?生活在紐約、哥本哈根和塔拉戈納的人們在照片上分別是怎樣的?
B:在哥本哈根和塔拉戈納我都拍過學校的課堂,拍過青少年。如果要簡單地回答你的問題的話,我會說丹麥的孩子都金發,面色蒼白;塔拉戈納的孩子則皮膚黝黑,具有南部民族的魅力。但這顯然太膚淺了。事實上我覺得不同地域的人們的共同點更有意思。在布魯塞爾,我想用鏡頭關注這兒的摩洛哥—非洲人聚居區,而當我拍攝他們時,我的目光將和我在拍攝蘇黎世的銀行家時別無二致。
H:你不會真的要拍蘇黎世的銀行家吧?你的作品里絕大多數都是年輕人,還有許多女孩子。
B:從20世紀90年代起,我開始關注相對年輕的族群。在大城市的市中心,人口構成總是以年輕人為主的,而我拍攝的就是我四周所見。在過去十年中,我的作品越來越關注不同的生活片段——時不時地也會在我作品里出現銀行家的生活片段……就像拉里·克拉克(譯注:Larry Clarke,因拍攝20世紀六七十年代青年人放縱生活而出名的美國攝影家)說過的那樣,我為之著迷的并非青春,而是社會。
H:在你位于杜塞爾多夫儲蓄銀行玻璃立面上的作品中,那些人物肖像的形象和你今天的作品完全不同。
B:我在20世紀90年代嘗試過一種新的創作方式,即不再抓拍,而是先和路人攀談,再請求對方允許我為他們拍照。我當時想要更多地認識這些面孔,而這是偶然路過的抓拍無法達到的。此外,為銀行大樓立面而作的項目無論如何也必須征求拍攝對象的同意才可以。所以人們在觀看這些照片時,有時候會感覺到這種不一樣的情景。
H:你當時有刻意和托馬斯·魯夫的學生肖像區別開來嗎?
B:不,當然沒有,這從一開始就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覺得托馬斯·魯夫的學生肖像系列很棒,因為它們雖然被一絲不茍地導演和策劃,但與此同時它們所展示的情景又非常具有即時感。我從來沒有要和“貝切爾的門生”們刻意劃清界限的意思。相反,我和他們之間也有一些共同點。此外,像杰夫·沃爾(Jeff W all) 或君特·弗爾格(Guenter Foerg)等“貝切爾的門生”的早期作品在當時是有重要影響力的。
H:你是如何被杜塞爾多夫的藝術圈接受的?
B:20世紀90年代初一切都很酷。如果你不是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學生,而想作為一個保守的瑞士人而被杜塞爾多夫的藝術圈接納,那確實會有點難度。不過這終于還是發生了。
H:人們喜歡將街頭攝影和偷窺癖這一概念聯系起來,也就是在對某人的觀察中產生的快感,盡管這種觀看是在一定距離之外的。你對此怎么看?
B:我的作品顯然和一般意義的偷窺癖毫無關系。至于我照片中出現的年輕女性,我想是馬蒂斯在被問及他為什么人到老年還為漂亮女孩所吸引時曾經回答道,就算時光流逝也無法阻止人們欣賞夕陽之美。可惜在我們這個很容易陷入新保守主義的世界里,這樣的觀點偶爾還是被批判的。

H:你的攝影作品從一開始就特別重視片段性,亦即從一個運動過程中截取某個完美的瞬間。你是如何確定片段的?
B:當畫家描繪一個情景時,他自己設計一切。每一個動作、每一個人都按照畫家的構思組合起來。而當人用鏡頭面對未經設計的真實世界時,會發現真實總是抗拒成為藝術家設想的樣子。畫家用畫筆建構或修改的東西,攝影師要通過對現實的篩選獲得。第一步是從大量材料中精確地擇取可用之材,而或許還有第二步即通過截取畫面的某個部分。但我極少使用第二步,就像我極少使用后期修圖一樣。
H:關于肖像權,當你拍攝某位不知道自己被拍的人物時,法律上是怎么處理的?當人們不期然看到他們自己出現在你的作品中時會作何反應?
B:在我的作品里認出自己的人不少。但以我的經驗來看,這些人大多聯想到的是在電視劇里以路人身份偶然出境并因此“出名五分鐘”的情況,所以對此的反應多半是覺得有趣或者好奇,而不會立刻想到肖像權的事。畢竟人的臉受之父母,而不是自己創造出來的,所以肖像權其實是種奇特的想法。不過考慮到一張照片可能被用于政治宣傳或商業廣告,肖像權的存在也就可以理解了。
H:你在拍完某人以后也不會問那人要拍攝許可?
B: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為我拍的人有數千名,如果要完成這個動作,我得雇傭一大群助理來幫我確認照片里的人是誰。
H:街頭生活總是有某種平庸感,或者說某種不言而喻的感覺。你對這種直接的、在某種條件下顯得平庸無奇的現實有何看法?
B:有很多攝影師都有意將平庸作為平庸本身來呈現,這不是很有趣。如果我只是拍攝一處毫無內容的街角,而且也按照其毫無內容的本相呈現出來,那在我看來就不是足夠的。為什么馬奈描繪福烈斯—貝熱爾酒吧的女孩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品?不是因為畫中有酒吧,也不是因為它特別漂亮,而是畫家對鏡子的巧妙處理帶有某種藝術理念。但使它真正成為標志性的偉大作品的原因,是極其微妙難說的。正是平庸的綜合體中多出來的這一點點微妙之處,才能流傳永世、感動觀者。
H:你能想象你的藝術中沒有人嗎?
B:不能。
H:在關于你作品的文章中常常提到,你從人群中抽出某些個體。但我現在和你在布魯塞爾,從窗戶看出去根本沒有能供你“抽出個體”的大批人群。
B:我的攝影作品里很少出現人群,主要是個體或數個人,其背景也多半不是人群。大量人群更多出現在我的影像作品里。
H:在你的作品中,形式要素常常很重要。當我在蘇黎世看到你拍攝的一位身處充滿裝飾的金屬大門前的女孩,她的倒影出現在玻璃窗上時,我發現畫面本身就制造了一種電影場景的瞬間。這種取景是怎么產生的?
B:人群的移動是迅速的。我會快速拍攝連續畫面,再從中選擇最好的,這個過程混合了有意的構圖和完全的意外。微小的敘事性是蘇黎世展出的作品的特別要素,比如另一幅照片中的男子正看著前幅照片里的女孩,或者同一張錢幣在另一幅照片里從一只手換到了另一只手中。
H:關于光線:你的照片通過對自然光的運用獲得了活力,這種光線常常會改變事物的結構。你會在創作中使用閃光燈嗎?
B:不會,閃光燈屬于極少數我從未嘗試過的東西。
H:時間和時間性總是指向一個結束。而你對時間的詮釋是更加積極的,并不只有線性的指向。
B:羅蘭·巴特說過,一張照片展示的是確定發生過的——同時也是確定已經逝去的。這一表述非常精彩,也是對這一命題的最佳表述。不過我在作品中并不會想到過去,我并非作為宏大的人類歷程的記錄者而創作我的作品的。
H:最后的問題:你也曾經以時尚攝影和政治選舉宣傳海報為例,說明非語言交流的不言而喻性以及其類型的不同性是并存的?
B:這些視覺世界,當然也包括電影,是對我最初的影響。當我剛開始街頭攝影時,看到街上有奧利維歐·托斯賈尼(O liv ie ro Toscani)為貝納通拍攝的巨幅商業廣告,它們令我印象深刻,因為它們的美和智慧并不遜色于純藝術,但它們發生在公共空間,是每個人都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