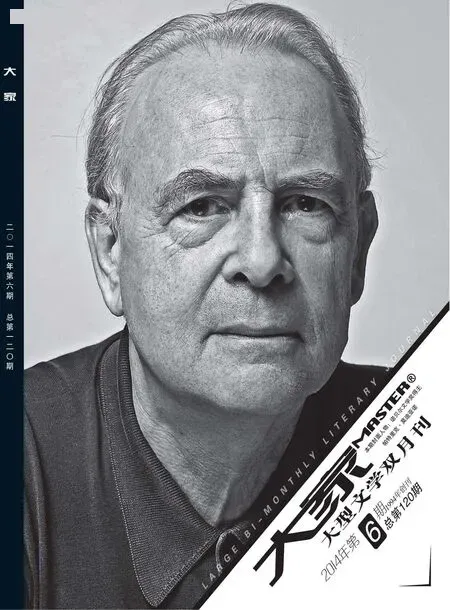關于女性意識與女性寫作的對談
∥張莉
∥趙玫
關于女性意識與女性寫作的對談
∥張莉
張莉,1971年3月出生,河北保定人,文學批評家,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出版學術專著有《浮出歷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魅力所在:中國當代文學片論》。曾獲第三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第三屆婦女/性別研究優秀博士論文獎。

∥趙玫

趙玫,滿族,生于天津,已出版《朗園》《武則天》《上官婉兒》等長篇小說,《歲月如歌》《我的靈魂不起舞》《尋找伊索爾德》等中短篇小說集,《從這里到永恒》《左岸∥左岸》《博物館書》等散文隨筆集,《阮玲玉》等電視劇本,計900余萬字。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中國作家協會“莊重文文學獎”、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
“我自己心里有很獨立的空間”
張莉:我對你的散文《愛的交換》印象特別深刻,上課時還和學生討論過。我們講“傷痕文學”時,討論到“文革”時常有年輕人與父母脫離關系的事情。之后,一起讀了你的文章。在這篇文字里,檢舉不存在。父親為了你的前途,簽字承認自己的“反動”,主動寫信給你,要你和他劃清界限,因為他不愿意牽連你,希望你有好的前途。但是,你拒絕了。在當時,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你那樣做出如此決定,這一方面是因為親情使然,另一方面也使人認識到,作為孩子的你,在當時也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畢竟你的選擇和當時主流價值觀太不一樣了。
趙玫:那件事,對我本身來說特別重要,它是人性本身特別強烈的東西。我父親是比較耿直的那種人,對于他來說,已經被打倒了、到鄉下、被開除黨籍,但是讓他簽字,我父親完全不同意。但他為了我,毫不猶豫地簽了字。這里有深刻的人性的東西,后來只要一想起這件事我就特別難過,就是說他為了我可以做出任何犧牲。
張莉:你在那篇文章里說,你和父親之間,原諒這個詞根本不存在。“這是親人之間最可悲也是最殘酷的一件事。何以要讓父親在女兒面前批判自己?我當時唯一的念頭就是寧可不留在城里,寧可上山下鄉,也要讓父親回家。”這篇文章不長,卻令人動容。后來你初中上了一年后沒去下鄉,直接去鋼廠工作了,那段經歷對你寫作經驗有幫助嗎?
趙玫:那一年我們沒下鄉,我們那屆畢業生全都留在了城里,因為工廠里已經沒有年輕人了。當時我只有16歲。我覺得自己是個很努力的人,和從小的教育培養有關,總是很努力。一開始在鋼廠的氧氣站當學徒,離家很遠,每天三班倒。因家庭背景不好,所以要特別努力,讓自己努力追求進步的東西。那段時間我一直和工人在一起,就這樣度過了整整八年。但我每天都很快樂。鋼廠的人都說天津話,但我始終說不好。小時候在劇院里,說的都是普通話,也許這讓我和他們有了某種距離。當然,我和他們都很友好,但心里始終擁有自己獨立的空間。
張莉:獨立的空間很重要。你知道我最近兩年為什么選擇做孫犁研究?原因之一是我很想知道他作為外地人,如何融入天津這個陌生城市。當然,我發現他沒有融入。您父親跟孫犁先生認識?
趙玫:我父親很早就認識孫犁,孫犁當編輯的時候,在《天津日報》上發表過父親的很多文章。后來他們一道創作京劇《蘆花蕩》的劇本,一起去白洋淀“深入生活”。那時候父親每到春節都會去看望他。后來我想要寫孫犁,父親說好,后來就寫了那篇《孫犁印象》。當時這篇文章在文壇挺有影響。
張莉;孫犁扶持天津本地作家很少,大概是他沒有把自己當作天津人。當時他在天津很有影響力嗎?
趙玫:孫犁對本地作家也有耳提面命的時候,但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影響。作為后輩我們很敬仰他。他很有風骨,不同流合污。一個人能寫好東西,他一定不會有太廣的朋友圈和江湖氣。孫犁去世的時候我們全家都去了,我認為他是很令人敬重的人。真正的大師永遠是后來者的楷模。
張莉:作為作家,孫犁的文字是有超越時代的魅力。他晚年寫評論也很有成績,他給莫言、賈平凹、鐵凝寫評論鼓勵他們,這成就了另外一個孫犁。我寫過篇《晚年孫犁——追步最好的讀書人》,講到他晚年嗜讀古書,他是以返回古代的方式表示自己不與當代同流合污,那是他的生活態度。
趙玫:那次開孫犁的紀念會,鄭法清說,孫犁說誰好誰就會好。孫犁欣賞的作家都有了相當成就。孫犁的眼光很準,很有見地,他看不上誰,誰寫得不好他也會說出來。孫犁生活在天津,是天津的幸運。
張莉:同意。我們回過頭來說工廠生活。我沒讀過你寫工廠生活的小說。在此之前,我也不知道你去過工廠那么多年。因為實在不能想象你和工廠有關系,而且呆了八年。
趙玫:我寫過一些,但那是很早的事了。我仿佛始終沒能真正融入到工廠的生活中。不過我和工友們很好,到現在依舊經常來往。我走到哪都會和大家友好相處。但我就是難以融合進那種冰冷的機械中。但鄉村對我來說就迥然不同了,“文革”中,我們被送回老家的時間并不久,但卻對那里的青山綠水充滿了迷戀。覺得那里是唯一能讓我感動的地方,于是才能寫出一些關于農村的作品。所以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鄉村的女兒,只有在這種感覺中才能獲得靈感。我記得一進工廠就去拉練,我們去了河北省的玉田縣,好多女孩同住在一間屋。旁邊住著一個農婦和她的女兒。記得她們母女特別喜歡我,總是偷偷地把我叫過去吃包子和雞蛋。這些東西讓我一生都不會忘記。我后來寫《漫隨流水》中鄉村的那一部分,親切自如。那種感覺,金色朝陽、棉花地啊,都是最美麗的意象。
張莉:一次有個上海朋友來天津,我陪他逛意式風情區,他很感慨地跟我說,天津特別像上海,是以前的安靜的上海,很洋派。“洋派”這個詞我覺得很有趣,洋派在你作品評論里也常被提及,比如《朗園》。恐怕批評家們都在文中感受到那種西洋的或大都市的氣息——是不是這個城市的建筑帶給了你這種想象?
趙玫:對。比如我忘不掉兒時的那片法國墓地,比如我出生在教會的婦產科醫院。我剛剛寫完一篇關于教堂的散文,題目是《遠逝的鐘聲》。維斯理教堂的牧師曾是我父親讀匯文中學時的老師,后來從科學救國轉而投向宗教。可惜那座教堂已被拆毀。街區中到處遺留著殖民地的房子,這也是我喜歡的那種城市風情。這些東西無疑深深地浸潤著我,等你要寫的時候,這些東西就會撲面而來。
張莉:天津在作家筆下有好幾個面向。每個作家筆下的天津都不一樣,因為每個人吸取的養料是不一樣的,和作家內在的血液有關系。
趙玫:總之小時候的東西永遠都不會忘。俱樂部原是英國人的跑馬場,他們在此修建了天津最早的游泳池。我父母1953年從部隊文工團來到天津,記得那時一到周末,父親就帶我們去干部俱樂部玩。幸好俱樂部的英式路燈至今保留著。
張莉:我知道你是1986年開始寫作的,一開始是寫作家的印象記。
趙玫:對,還寫了一些理論文章。我當時給張潔、劉索拉、鐵凝等寫過評論,那時大學剛畢業,還不曾立刻進入小說寫作。1985年底《文學自由談》創刊,因為編輯工作需要,我寫了很多理論文章,其中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先鋒小說的自足與浮泛》,據說也曾小有影響。這個過程中我結識了很多作家,慢慢覺得,純粹的理論已不能完成我真正想要表達的東西。我父親對古典文學極為熟悉,他身為劇作家和導演,對我的創作有著很大的影響。我后來進入小說、散文的創作,雖然跟戲劇沒有特別多的關聯,但許多場景化的表述,依舊是某種自然而然的潛意識使然。
張莉:后來是什么契機讓你突然寫小說了呢?我對這個轉變特別感興趣。
趙玫:其實我一直想寫小說。離開工廠到南開大學上學的時候,當時讀了張潔《沉重的翅膀》、張承志《北方的河》,那些作品對我們來說有一種特別強烈的感覺。上大學的時候包括畢業后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覺得革命浪漫主義和革命現實主義相結合的這種方式對我不合適,所以肯定寫不好,或許因自己修煉不夠。大學畢業后,20世紀的現代文學被翻譯過來,那時候就做了一些惡補。比如大量閱讀法國小說,包括羅布·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以及杜拉斯。同時大量讀美國作家福克納、英國作家伍爾芙等,從他們的小說中我突然覺得自己會寫小說了,顯然是他們調動起我想要用不同的方法寫作的沖動。我看重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篇小說《河東寨》,因為《河東寨》給了我一種很有新意、寫起來也很愜意的感覺。然后就這樣一發而不可收了,從此便開始了這種所謂現代方式的寫作。
我們家族的女人
張莉:80年代有很多西方的作品涌過來,催生了中國的先鋒寫作。你應該是那個潮流里的作家,而且一直堅持這樣寫作。《我們家族的女人》是很著名的。是什么契機,使你意識到自己是滿族人,要去追溯家族?我覺得這個意識特別重要。
趙玫:《我們家族的女人》是我寫作中比較重要的作品。因為文化大革命中父親遭批判,母親就把我和弟弟送回老家,那一次我在農村呆了很久。當時只有十二三歲。老家是河北省樂亭縣,你看,我們兩個都是河北人。我們家族自關外來,“跑馬占圈”擁有了這塊富庶的地盤。我喜歡老家,所以,鄉下在我筆下總是充滿眷戀。只要是寫到的鄉下,便永遠是最美好的,充滿了溫情的。在老家的時候,我慢慢地知道了關于家族的歷史,我們家族的女人,有很多不幸,很多的傷感與無奈,慢慢地將這些東西連綴起來,便覺得這是一部家族女人的歷史。這些滿族女人身上有著特別堅韌的一種精神。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依然用了一種比較現代的寫作方式,中間還穿插著當代的故事。那種家族的血脈、滿族女人的那種堅韌,都是從我奶奶、我姑媽身上發掘的,都是真實的。后來查閱家族的族譜,才知道我們的滿族姓氏,叫伊爾根覺羅,所以我的名字,很可能就是伊爾根覺羅·玫之類的。所以我們這個家族的長相,比如我爺爺那張瘦長的臉,看上去完全就像康熙的樣子。這種家族和血液的東西極為頑固,只是有時候你意識不到罷了。總之它是你生命中極有力量的元素。堅韌、不放棄,是滿族女人普遍的一種精神。
張莉:有些民族的人,我們很快能分辨,因為衣服以及飲食習慣的不同。滿族現在被同化得很厲害,所以,我覺得,你意識到自己是個滿族人時應該是在某個時刻,突然認識到自己的民族身份。當然,你作為少數民族寫作者的身份沒那么清晰,意識也沒那么清晰,你不是特別敏感。
趙玫:也許文字中的表現沒那么清晰,但骨子里一定流淌著家族的血。比如我父親身上的那種執拗。但滿人和滿人也不一樣,家在北京的和家在外省的滿人也不一樣,雖然大家都是滿族,但形象上也是千差萬別。雖然是滿族,但我從不曾強調自己的族裔,因為我覺得沒有刻意凸顯的必要。
張莉:我想到阿來有篇文章,他說,一方面他愿意用藏族身份去寫作,去思考,但他也意識到,單獨強調這個人是藏族,可能還有另外的意思在。有時候他覺得那種普遍性很重要。所以他說:“我借用異域、異族題材所要追求和表現的,無非就是一種歷史的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認同,即一種普遍的眼光,普遍的歷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
趙玫:民族身份對我來說也有益處,比如我能由此而感知到民族異化的悲哀,這些感知還是在美國得來的。那一年我參加美國政府的“國際訪問者計劃”,去了新墨西哥州的圣菲,那里居住的大多是印第安人。然后去落基山脈看了印第安人的部落。他們講了許多完全不同的對世界的認知。我覺得很多民族都有只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并慢慢意識到這些東西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它會帶給你很多不一樣的眼光。我雖然并不特別強調民族對個體的作用,但覺得民族身份無疑會為你帶來好多不言而喻的東西。
張莉:我讀研究生的時候,一個老師用很長時間給我們講族群問題,她說少數民族這個提法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民族和民族之間不能以多數和少數來區別。這很有啟發性。一位作家以滿族的身份來發聲的時候,其實和漢族是一樣的,并不因為她是少數才需要關注,需要特別照顧。現在關于族群的寫作在全球化時代很重要。我覺得關于家族和民族的作品是可以再寫下去的,那是屬于你的寶藏。回過頭,我想說說《朗園》。我小的時候讀你的《朗園》,印象特別深刻。那是“布老虎叢書”,當時還有鐵凝的《無雨之城》,我都很喜歡。你是怎么想起要寫這個小說的?
趙玫:當時說《朗園》賣了四五十萬冊,好多家影視機構來找我談影視改編權。后來,拍了十幾集電視連續劇,陳凱歌擔任總監制,費翔、李鳳旭飾演男女主角。一些人看后說拍得很唯美,但是對演員的表演評價不一。我始終沒看過。寫《朗園》之前我已經寫過很多作品了,包括《我們家族的女人》。“布老虎叢書”找來一些作家來策劃,有鐵凝、洪峰和我,還有莫言、馬原,但他們好像沒有寫。那時候我已經很在意天津的文化。我對天津城市文化有著特別親和的感覺。雖然我父母是從外地來的,但我出生在天津,城市中種種兒時的記憶,不僅僅是景觀,也是世界觀。比如在一座老房子里,既有很老的民族資本家,亦有后來的“進城”干部,將原本住在二樓的資本家攆到一樓,然后再到“文化大革命”,又是一些工人搬進來,于是就有了這樣一個小說的結構。我親身經歷過“文革”,所以寫起來很順暢,卻始終沒想好小說的名字。因為整個故事纏繞在一座房子里,然后,有一天就突然想到了“朗園”。
站在女人的立場想象歷史
趙玫:寫《朗園》的時候,還是文學很繁榮的一個狀態,大家都特別積極地寫作,也有很多讀者。現在想起來,《朗園》和“布老虎”的合作還是很成功的。我記得當時有兩件事:一是《朗園》得了在當時算很高的稿酬,二是張藝謀要拍《武則天》,這兩部作品幾乎前后完成。先后跟“布老虎叢書”、跟張藝謀簽約。然后就是1994年秋天去美國。那時美國文化參贊想讓我去“愛德華寫作中心”,后來又說給我一個更好的項目,就是美國政府的“國際訪問者計劃”。這三件事在九十年代初對我來說特別重要。
張莉:我記得《朗園》的新聞,聲勢很大,小說發行量也大,它也算比較早的商業化、市場營銷成功的案例。去美國是什么樣的項目,它影響了你后來的寫作追求吧?
趙玫:我的項目一個是關于女性,一個是關于寫作。從頭到尾會有一位翻譯全程陪同,后來我和翻譯儀方成了很好的朋友。抵達華盛頓后,他們已為我安排好了行程,但儀方說,你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于是我便說,我要去南方,去福克納的家。因那時我已經看過了福克納許多作品。我還經常參加翻譯界的會議,翻譯了《喧嘩與騷動》的李文俊先生和北大的陶潔教授都是我尊敬的好朋友。于是我執著地說,就是想去看看福克納的家。或者我對福克納的執著打動了他們,他們很快就為我重新安排了行程,從曼菲斯沿密西西比河一路向南,直到新奧爾良,其間包括住在南方莊園,拜訪黑人家庭,以及終于如愿以償地走進了福克納的家。這些對我來說都非常重要,每到一個城市你都會和這個城市的作家交流。這對于我來說具有雙重意義,一個是我看到了美國作家是怎樣寫作的;同時,對于女性生存,也有了極為強烈的感知。因為在九十年代初,中國的女性對自己的生存狀態還不敏感,當時的國人也沒有那么強烈的女性權利意識。當然,也不能說沒有這方面的理論,但它基本上束之高閣,僅僅作為某種學問,與現實不搭界。可當你真正地去跟那些美國女性接觸的時候會發現,她們都明白自己的權利是什么,自己要什么和不要什么。
張莉:而且,當時也有個契機,1995年的世界婦女大會,對你這代人和當時整個中國社會都應該是一個刺激。
趙玫:對,我從美國回來后的1995年,剛好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們有了一個關于女性文學的NGO論壇,和北大的陶潔老師、社科院的朱虹老師,以及冰心的女兒吳青老師等這些專家,一起參加了這次大會。這次參會對我來說很重要,不僅加深了在美國體驗的那些關于女性的理念,又感知到了世界婦女大會對所有女性的愛護與支持。在“國際訪問者計劃”中,我還結識了佛瑞丹,她是美國婦女界最重要的人物,也在北京的世界婦女大會上了做專題演講。因為相識,佛瑞丹便在世界婦女大會之后專程來到我家。我們對女性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其實,我當時就有一種要為女性寫作的意識,雖然還不是很明確。后來我寫完《武則天》,一些評論家說我是女性意識,女權主義。其實并不是這樣的,畢竟武則天本身就擁有權力,所以寫她,自然也要寫她的權力意識。女性意識,我當然有,但絕不偏執。
張莉:《朗園》之后,你開始寫《武則天》,是張藝謀邀請的。我印象中他請了當時最先鋒的青年作家加入,你、格非、蘇童、須蘭等。現在看來,那個電影雖然沒拍成,但你受益頗大,開啟了你的另一個創作系列。
趙玫:這段過程很有意思。我當時寫了《天國的戀人》《世紀末的情人》《我們家族的女人》,也算是當代愛情的三部曲。后來簽約《武則天》的時候,他們給我一周時間考慮。我也在糾結寫還是不寫。顧慮是我從未涉獵過歷史小說的寫作,但我得益于父親書架里那些書,《新唐書》《舊唐書》,以及《資治通鑒》。在閱讀了這些史書后,我覺得我可以寫,而且我覺得自己的寫作應該有些變化了。我是一個特別希望有變化的人,比如一種題材或某種感覺,你寫完再重復一遍,會覺得一點意思也沒有。但你的變化是否能成功就很難說了,但我寧愿顛覆千篇一律的自己。所以我簽了約,覺得可以嘗試一下。一開始那些資料看得我昏天黑地,想想看,那些《新唐書》《舊唐書》幾乎沒有標點,幸好就得益于大學的古代漢語,為此我一直感恩于大學的教育。
張莉:我看到一個資料,說你寫《武則天》之前,帶著女兒去走了當年武則天經歷過的地方,洛陽呀,長安呀,我看到這兒的時候想,你一定感觸深刻,有強烈的動筆欲望。
趙玫:記得將史書讀得天昏地暗,是我父親提醒我:“你看得差不多了,你應該走出去。”我覺得父親的提醒很重要,那時剛好是夏天,趕上女兒正放假,我們就安排好一路從洛陽到長安,走過的都是武則天曾經生活過的地方。其實那時心里已經有數了,但如果沒有真的到達那些故地山川,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地理地貌,心里終究很沒底。所以,這一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從洛陽一直到長安。一路上看過了白馬寺,以及武則天在洛陽的宮殿遺址。有當地朋友陪著我,甚至幫我估量過皇宮和白馬寺之間的距離。在朋友的幫助下,我親身走過了那條路。包括洛河,武則天登基的地方,那些固有的山川走勢以及由此而生的情感氛圍。盡管世事變遷,但山川依舊,這讓我的寫作突然變得立體起來。
張莉:我的感覺是,走出去對于當時的你寫作《武則天》意義重大。你站在那看,會感覺到武則天她當年看到的也是這樣的。那種感覺很實際。在屋里想象一個女人怎樣進行皇權爭奪和走到山川之間去感受是兩回事,后者會讓人感受到她的氣魄有多大,那些山川和自然風景如何刺激她的斗爭欲望。
趙玫:對,在那片土地上,想象著古老的長安城,便頓時有了文字的感覺。所以行走的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極為重要,包括種種實在的風貌、物件,包括那座由郭沫若題寫的陜西博物館,甚至長安所特有那種浩大的屋檐。記得我還去了法門寺,印象是那座寺廟安靜極了。墻邊搖曳著一些小花,屋檐上玉石的風鈴,叮叮當當地響著,就仿佛走進了舊時唐宮,這無疑讓我的寫作充滿了感覺。
張莉:我們看到的天和她看到的天某種意義上是一樣的,法門寺和小花也是一樣的,以及風鈴。這是一種歷史認知,《武則天》的電影雖然沒有拍,但后來關于武則天的各種電視劇出來很多。老實說,你的小說對后面的影視創作應該幫助很大,你是最早對作為女性的武則天的心理世界進行探討的作家。
趙玫:寫武則天之前,我看的那些史書全都是男性寫的,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我真的是有了一種女性的意識。我覺得,我是站在一個女人的立場在寫一個女人。比如,史書上說,武則天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兒子,這一點,歷朝歷代的史書中都對她充滿斥責。但對我來說,你要設身處地為她去想,她為什么要這么做,而她這樣做時的內心又是怎樣的。總之,這個女人的復雜性和單一性是并存的,她做所有的事永遠是一擊即中、一擊即了,通過這些我就覺得武則天這個人真是太了不起了。
張莉:她和那么多男人,那么多擅長玩權術的人一起玩,自己還沒有被玩死,她到晚年也算是善終。有人在她童年時代預測她未來要成皇帝這個事是真的嗎?我很懷疑,哪個算命的敢在一個人小時候預測她是皇帝呢?這是犯忌的事情,也是超出想象力的事情。很可能是必須要造這樣一個理由,因為她要當皇帝,所以要制造這樣一個理由。如果傳說是真的,她根本進不了宮啊,李世民也不會讓她進宮吧。
趙玫:這種事情要是從現實層面上來說,可能不是真的,但那時的人就是迷信這些,我覺得是后人在附會。后來她成功登基,是借助于宗教。有人說我的小說寫得好,可能就因為是站在女性的立場上,顯得新穎一些而已。本來,小說只寫到武則天登基。但后來,我還是完整地寫完了女皇的一生。我覺得她晚年的那些故事不寫就可惜了,就不完整了。最后,我還是增加了十萬字,頗具規模地完成了這個女人的整個人生。
張莉:你面對的史料并不豐富,所以很有挑戰性。之后你寫了《高陽公主》和《上官婉兒》。寫《高陽公主》其實是你在給她翻案,從某種程度上說是這樣。比如說武則天,之前也有人認為她很有魄力,但高陽公主算是一個創新。
趙玫:《武則天》之后就寫了《高陽公主》,因為高陽公主的故事,是我在寫武則天時發現的。我覺得這個人物非常有意思,在“唐宮三部曲”中,我覺得《高陽公主》是最輕盈、最飄逸,文字也最自由的。因為它不是宮廷和權力的書寫,而是一個充滿了血腥的愛的故事。記得在《唐書》中一看到寥寥數語關于高陽公主的記載,就興奮不已。當下便決意將這個公主的傳奇寫成小說。有人寫過武則天,也有人寫過上官婉兒,但高陽公主只有我一個人寫過。其實是她的愛情,才堪稱那種唯美的故事。史書中就這么幾行字的記載,我便繁衍開去,故事結構、人物關系、情感糾葛,等等等等,都是我的原創。后來一些影視作品,其實都是照搬。
張莉:史書中,對高陽公主的介紹少之又少,介紹得少也意味著給你的空間很大。傳者認為這樣一位大唐公主的所作所為有傷風化。但你從一個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和認知她。我覺得在三部曲中,《高陽公主》對你很重要。
趙玫:其實寫《高陽公主》時,就不那么艱苦了,因為這三個人物基本上都是在一個時期中,這點很重要。所以我擁有的資料,前后的銜接,都是相互關聯的。有意思的是,寫完《高陽公主》后,長江文藝出版社的吳雙找到我,說你為什么不寫寫上官婉兒呢?我說太累了。他們說,你一定得寫。然后就動筆了。奇怪的是,我在寫《武則天》的時候,竟然一個字都沒提到過上官婉兒。一般來說,寫武則天,就必然要提到上官婉兒,包括郭沫若的戲劇。于是我擁有了一個更為廣闊的關于上官婉兒的空間,最終以四十萬字完成了《上官婉兒》,里面反倒涉及了很多上官婉兒和武則天的關系。
張莉:去年有過一個很大的新聞,就是上官婉兒的墓被發現了,我們看到了她的墓志銘,墓志銘里講述的她很令人驚訝。她被封過唐高宗的才人,做過唐中宗的昭容,和武三思私通,和武則天的男寵們鬧過緋聞,最后還被唐明皇殺死。從墓志銘中可以看到,上官婉兒跟我們想象的差別很大,她固然有才,但也很性情,跟很多男人有曖昧,她身上那種倔強和彪悍都太戲劇性了。而且,特別奇特的是,這些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和你小說的講述很相近。這太重要了。只有女性站在女性角度去想象歷史上的女性才可以做到。在此之前,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上官婉兒居然是這樣的女人,完全不會想象到這個事情。包括歷史學家也不能推測出來,因為這些都超越一般人對歷史人物的理解,或者說,普通人難以超越某種框架去想象歷史上真實的那個女人。但是,你寫的上官婉兒的書里全有,去年發掘的墓志銘證明你想象的準確性,這太有意思了。
趙玫:是的,我也注意到了那個新聞,后來一些朋友拿來碑文給我看,事實上碑文上的內容在我書中都涉及到了,這讓我很愉快。
張莉:十多年來,讀者可能會覺得你的小說就是對歷史的一個想象嘛,并沒有人以為是真的。也可能讀者會問,上官婉兒怎么會這樣呢?不是吧?可是,為什么不能?墓碑文字便是一個證明。你知道,我看到那個新聞的第一時間就想到你的小說,想到你寫作中的女性意識與歷史寫作的某種關系。這種站在女性立場上對歷史的想象和書寫是重要的,我認為,它對我們書寫和想象歷史做出了獨特的貢獻。
趙玫:還有最后她的死,那個當然也是真實的,等于是唐明皇要殺她嘛。她走出來,秉燭,讓他們殺。這個從容不迫、視死如歸的女人,真的很了不起。
張莉:可能宮廷里的政治已經使她意識到自己活不了了,所以她走出來。這真的是一場政治,殺了她,又死后哀榮。一般的歷史小說都是講故事一樣,情景再現。但你的是心理,是情感,不一定是那種栩栩如生的場景。
趙玫:寫歷史小說不能太現代,但又不是去做那些“老黃歷”。所以我寫的時候是把歷史的東西和現代的東西融合起來,這尤其體現在《高陽公主》上。它雖然是歷史小說,但基本上看不出章回那種感覺,所以我覺得說這三部作品是站在女性的立場上的寫作很對。臺灣人不也喜歡歷史小說嘛,我們有一次在一起研討,他們也覺得我的小說在歷史小說中是很另類的。這部書在臺灣有兩家出版機構出版過。
張莉:有一句話: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其實你是用當代人的眼光重新回到歷史。當時你寫作的時候,流行一個詞,叫“新歷史主義寫作”,我想,張藝謀請你們寫的時候是有考慮的,他們挑選的這幾個人都是有先鋒色彩的作家,他很可能也是希望用現代的眼光來重新演繹歷史。我覺得這三部作品很完整地呈現了一個現代女性怎么去看古代的女性;那些古代的女性呢,又因為這樣一種關照重新活了過來——你的文字通過想象抵達了一種真實。
趙玫:這三本書前后寫了十年,加起來有一百萬字,已經有七八家出版社出版過,有的出版社已前后三次出版。但之后再沒有寫過歷史小說。有人說你再寫寫這個那個,我說不寫了。是這樣的,在你年輕的時候,有體力的時候,完成了規模大的作品,就可以罷手了。如果硬寫,反而適得其反。
“我喜歡不做實的寫作”
張莉:好多研究者都提到你小說中的“性”,因為你書里關于“性”的內容令人印象深刻。在你的性書寫里,幾乎不寫行動,只有感受,一個女人的感受。這種書寫“性”的方式在整個中國女性寫作里面并不普遍,我覺得,這種寫作在某種程度上屬于拒絕觀看,但同時,作為作家,你又很愿意表達那種女性感受,你愿意進行一種精神感受的分享。
趙玫:首先,“性”本身就是生命過程中的組成部分。我覺得在新時期文學中,“性”是一步一步向前突破的禁區。對于“性”,我們一開始諱莫如深,但伴隨著開放的程度,慢慢地,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入與“性”相關的寫作。我的小說同樣跟著社會往前走,就有了一些這樣的描寫。

《無畏》 布面油畫 160cmx90cm 2008年 張煒
張莉:那你是看別人的東西感受到的,還是自己慢慢意識到的?
趙玫:都有,主要是自己的意識,因為我覺得在文學中忽略“性”,你的書寫就不夠完整。所以在寫作中,我一直覺得這個部分是不可少的。后來有人說到我小說中的“性”描寫,認為是美好的,甚至是一種精神的享受。包括我的《冬天死于秋季》也有很多關于“性”的內容,我同意你對我書中性描寫的解讀。
張莉:在整個當代文學中,作為讀者我會看到不同作家寫“性”,也會看到性書寫在中國文學中的發展過程。你小說里邊有內斂的精神性的東西。現在小說跟以前小說書寫性有了很大的不同,更自然,更日常。這是不同時代作家對人的不同理解,比如有人認為人本身就是動物,而另外一些作家則認為“性”是情感的一部分,是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年輕作家寫更火爆的“性”,也算上對當代文學的沖擊。
趙玫:我喜歡棉棉的小說,還給她的《糖》寫過書評。年輕的一代寫“性”和我們肯定不一樣。最不同的地方就是時代變了,當下的“性”已變得很自由,很隨便,所以很輕。不同的時代對“性”的理解也迥然不同。記得在舒婷邀請我參加的中韓論壇上,每位作家都要朗讀對方作家的一段小說。我摘取了《銅雀春深》的最后一章,其間包含了“性”。然后韓國女作家朗讀了這個段落,說既不好意思讀,卻又覺得很美,我覺得這種感覺確實挺有意思的。
張莉:你的作品里經常會有男人和女人,沒有名字,你只說男人和女人,你不愿意特指。這樣可以理解為兩個人,也可以是泛指,有普遍性。
趙玫:我的小說中,經常是一個人有名字,另外的人沒名字,我是有意識這樣做的,我不愿意讓一個小說里全都是名字。我喜歡用“他”或者“她”,有一種廣義在其中。有時候我就是喜歡這種不確定的東西,不喜歡那種做實的感覺。覺得在虛無飄渺中,反而能得到某種普遍性的東西。
張莉:先鋒派之后,寫實主義是大受讀者歡迎的。你剛才強調你不喜歡做實,你的作品一直不是寫實的。如果有一天要你寫一個寫實主義的小說,你的讀者可能會更多。但你會嘗試嗎?
趙玫:我不喜歡“現實主義”這個詞。我覺得自己肯定寫不好完全寫實的小說。不過有人說我的小說是心理現實主義,這個說法我可以接受。總之每個人都要各取所長,無法獲得感覺的時候,就無需去嘗試。每個作家的感知點是不一樣的。同樣的事物,有人喜歡描寫這一部分,有人則可能喜歡描寫另外的部分。我們所面對的日常現實,已令人感到瑣碎、疲憊,甚而被困擾。所以我有意表現出一些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意象。包括人物、環境、情節,盡可能地與尋常的“日子”疏離一些,給人另一種精神層面豐富些的“現實”,事實上,一些讀者也很喜歡。
張莉:我喜歡你這個答案。那你這種獨特的寫作方法是從上大學開始,還是從接觸西方文學開始,或是像你說的杜拉斯和伍爾芙對你的影響?
趙玫:還有福克納。我覺得西方文學的影響對我是非常重要的,好多人不愿意承認自己受西方影響,但我不會寫寫實主義,不會寫浪漫主義,這些人的作品對我就像是救命稻草一樣。當然我對外國的作家也是有選擇的,比如一部分是我要知道他,但我真正親和的就是福克納、伍爾芙和杜拉斯。他們的出現對我很重要。
張莉:伍爾芙和你有很相近的地方,比如她也寫評論。我特別喜歡她的《普通讀者》,隨時隨地都會帶著。
趙玫:在女性里我最早是喜歡杜拉斯,前些天我還在北京參加了她百年的紀念活動。我最幸運的是我沒有第一個看《情人》,我最早看的是《琴聲如訴》。八十年代初剛寫小說的時候有人建議我讀杜拉斯,說我的風格和她很像,很幸運我讀的最早的作品是杜拉斯最先鋒的作品。那個時代是一個先鋒的時代,比《情人》還早的是法國新小說派最實驗性的作品,所以我最早接觸的是這個。但比杜拉斯更早的是有一年我們全家去北戴河度假,那有一個小圖書館,第一次看到伍爾芙講真正的現實主義的那個觀念,那些觀念就像紛紛墜落的碎片一樣。所以我當時記得很清楚,就是她所謂的意識流是真實的,而我們在大腦被重新整合的東西反而是虛假的。當時我對這些概念特別感興趣,那時候我已經大學畢業了,我24歲上大學,28歲畢業,30多歲時開始寫小說。
張莉:所以那本書是恰逢其時,等于說把你喚醒了。
趙玫:對,讓我學到很多。還有一個叫做《弗蘭德公路》的作品,還有喬伊斯的小說,他的那種行進感,我當時特別認真地學。我印象特別深,講那個墓地,一點一點往前走,就有了一種行進的感覺。《弗蘭德公路》有一個場景,松林背后是跑馬場。西蒙依次描述跑馬時躍起來,然后是樹林,是騎手背心的顏色。便是這些意象形成了行進的感覺,西蒙讓他的描寫中充滿了動感。諸如此類的寫作對我有特別重要的意義,我就知道該怎么表現這些東西了。我讀了《情人》等作品喜歡了杜拉斯,但我慢慢覺得杜拉斯可能太性感了,她是特別性感的一個人。伍爾芙是我更加應該學習的,因為她可以創造她所謂的意識流,把整個文學的世界都顛倒了。
張莉:很同意你對伍爾芙的理解。我視伍爾芙為學習榜樣。她有很理性的思考和很整體的看法,但她又用很感性的方式來表達。今天,無論是對我們創作也好,對批評也罷,她的書都很有幫助。我個人認為她比杜拉斯更具先鋒性。杜拉斯屬于比較好的女作家,有獨特性,但伍爾芙是開山人。
趙玫:而且她有些概念特別重要。比如有些作家會說,我為什么是女性作家,我們應該是平等的,但伍爾芙不是這樣認為的。她認為女性只有做到最好做到極致才是真正燦爛的。她不是淺薄的女性主義。
張莉:對,伍爾芙的《一個人的房間》里面有一段話我特別喜歡,“如果我們已經養成了自由的習慣,并且有秉筆直書坦陳己見的勇氣;如果我們從普通客廳之中略為解脫,并且不總是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來觀察人,而是要觀察人與真實之間的關系;還要觀察天空、樹木和任何事物本身;如果我們的目光超越彌爾頓的標桿,因為沒有人應該遮蔽自己的視野;如果我們敢于面對事實,因為這是一個事實:沒有人會伸出手臂來攙扶我們,我們要獨立行走,我們要與真實世界確立聯系,而不僅僅是與男男女女蕓蕓眾生的物質世界建立重要聯系,要是我們果真能夠如此,那么這個機會就會來臨。”她一方面意識到女性本身的地位決定她寫作的局限,另一方面她不把女性寫得不好當做一個借口。她是從整體上來理解男性和女性的差距,非常冷靜。她承認女性本身的東西有可能是不足的。但另一方面也認為是可以克服的,好的女性寫作就是怎么能把女性的優長發揮到極致。
趙玫:所以我從不介意別人稱我女作家。我覺得性別本身的存在,讓你無需斤斤計較。
張莉:是的。而且,我們說女性寫作的語言——伍爾芙的語言,那種語感、排列的方式也是很獨特的。比如一句話里面有一個中心,但她繞著說,同時有比喻、有排比,這個完全是屬于女性的。你的表達也很有特點,比如幾乎不用引號。
趙玫:事實上,從我寫作第一篇小說《和東寨》時,就不使用引號了。我記得那是1986年。從此我的小說就再沒有使用過引號,我為此還寫了一篇《我為什么不使用引號》的文章。所以會做這樣的嘗試,是因為我一直覺得在現實生活中,一個人的表情,動作,乃至語言,哪怕一個微妙的眼神,一個無端的手勢,都是不可能截然分開。一個人講話的時候一定會帶上那個特定時刻的表情,而他的動作也會同時出現,甚至他的氣息,他的強度或語速之類。所以在語言中,尤其在比較先鋒的那個時代,便會突發奇想,變幻出各種想法來,其實就是不愿被各種符號所束縛。
張莉:明白。我覺得,伍爾芙一直在努力尋找屬于她的表達方式。比如她寫《一個人的房間》,她要討論學術性的問題,但她要用那種講故事、娓娓道來的方式,不板著臉孔,用協商的語氣,而非高高在上,所以,她在討論女性寫作的問題時,同時也強調了女性語言表達的特色。我很喜歡這樣的表達。剛才你說你寫作沒有引號其實也是一種嘗試和探索,很對。但我覺得,更重要的,你寫作的標識性在于,你的語言是繁復的、緩慢的、一點點著色的,不是那種很輕快的表達,而且,很顯然你并不試圖取悅讀者,你只是在回視自己的情感和內心。這是一開始就有的自然的表達習慣嗎?
趙玫:似乎是很自然的。現在我覺得語言本身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感覺上語言比故事更重要,這只是對我來說。因為有些人更喜歡用語言講故事,而且隨著年齡增長,我更在意語言的推敲,但這也可能是一種錯誤。
張莉:我認為不是錯誤。作家永遠都應該對語言保持敏感性。我覺得語言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就是寫作政治的一部分。比如什么身份的人說什么樣的語言。前一陣看莫言的資料,他講到徐懷中跟他們講,語言就是一個作家內分泌。這話說得特別好,這是一個作家、一個有寫作經驗的人才可以總結出來的。
你有本書叫《她說她有她的追求》,一句話八個字,用了三個“她”,它包含了強烈的女性意識,是那種獨立的、有精神追求的的表達。我喜歡這個書名,這不只是一個朗朗上口的書名,也是一種寫作態度。——當一位作家用繁復緩慢的語言講述時,也代表了她的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寫作態度。當然,每個人的寫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我覺得你最近的寫作也在尋找讓自己更完善的途徑。
趙玫:對,首先我和那種寫實創作是很分離的,我跟它有距離。當然,近幾年我實際也是在發生變化。其實每個作家都不可能一直都是那樣,不同時期總會有各種各樣的變化。
這才是正常的。
責任編輯:王恒騰 夏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