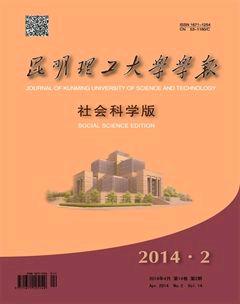商品拜物教:價值關系的矛盾本性及其顛倒幻象
聶海杰
摘要:商品拜物教是附帶于商品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固有性質。由于商品生產本身的二重性,使得商品世界中人與人的關系被顛倒為物與物的關系,并實則被同化為商品之間的價值關系。而商品價值形式自身的矛盾本性,在將商品生產者的主體創造力量凝結為社會化的價值實體之際,其幽靈般的價值對象性之對象化的過程,必然地衍生出一系列顛倒性及與之相適應的拜物教幻象。
關鍵詞:馬克思;商品拜物教;商品生產;相對價值形式;等價形式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1-1254(2014)02-0018-08
Commodity Fetishism: The Contradictory Nature and the
Reversed Fantasy of the Value Relationship
NIE Hai-jie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Institut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Henan, China)
Abstract:Commodity fetishism is an inherent nature incidental to commodity production. Owing to the duality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itself, the human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in the commercial world are reversed as commodity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s, and it is actually further assimilated into the valu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odities. But at the time when the subject creative power of commodity producers is crystallized into the socialized substance value in which its ghostly value configuration is objectified, the inherent contradictory nature of commodity value forms will certainly derive a series of subversive and corresponding fetish fantasy.
Keywords:Marx; commodity fetishism; commodity production; relative value form; equivalent form
“拜物教”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獨特現象,幾乎在遠古時代就已存在。雖然很早就有學者對之進行過研究,然而,馬克思是第一個創造性地將拜物教與商品聯系起來的人。他通過對商品形式即商品生產本身蘊含的經濟關系的形式規定的科學剖析,通過對價值關系本有矛盾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了商品形式中所蘊含著的一系列顛倒關系。正是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中感性與超感性、具體與抽象、特殊與普遍的對立及其發展,不但使得價值形式本身披上了一層“謎一般的性質”,而且由此衍生出充滿顛倒迷幻的拜物教幻象。
一、源于商品生產本性的拜物教特質
從歷史發展進程看,早在原始社會,就已然存在著拜物教傾向。在那時,由于生產力發展水平低下,人們認識和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較小,由此不可避免地產生出對自然界的盲目崇拜。例如,對“樹木、太陽、大象、石頭……等等都曾當作神靈來崇拜,以求獲得庇護”[1]2。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初期普遍存在著的景象,并且在非洲土著那里表現得較為明顯和突出。16世紀在環西非海岸的非洲從事貿易活動的葡萄牙人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當地的非洲土著把小型的祭拜品當做護身符去崇拜。葡萄牙人因此將這種附身符稱為“feitico”——“做”或“制作”,意即“用符號來模仿”。在當時的西方人眼里,無論是何物,非洲土著賦予了它們人的靈魂和性情,人們通過對它們頂禮膜拜或實施巫蠱,并在意念中與其達至合一。這種對物的神化其實已然就是一種拜物教傾向,即他們賦予自己的制作物以神性或魔力,從而將普通的物品當做“物神”去崇拜。事實上,英語中的“fetish”(物神、盲目崇拜的對象)正是發源于此。一般而言,“拜物教到目前為止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指原始人的巫術,是在宗教意義上使用的;二是指宗教意義之外的其他用法,如馬克思的商品、貨幣和資本的三大拜物教,即像宗教崇拜那樣對待社會生活中的各種現象”[1]2。通過對商品形式的科學剖析,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礎上,一旦勞動產品采取了商品形式,商品就成了一個可感而又超感的怪物,并且商品形式本身也因而“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2]88。為了更為形象地闡明商品形式本身的這一特性,馬克思顯然從形式上借用了由法國哲學家夏爾·德·布羅斯所創立的“拜物教”(法語為fétichisme,英語為fetishism)這個概念[3],認為在商品世界中也存在著這種表面相像于物神崇拜的景象,即在商品世界中也存在著人們對他們自己創造物(商品)之宗教式的崇拜現象。
由此可見,拜物教的一個根本的內在規定及其突出特征就是偶像崇拜,即人們將原本是自身本質力量的某種“物”看做獨立于自身以外的神秘力量,從而拜服在這一創造物面前。這一境況在宗教意識領域表現得最為突出和明顯。在那里,“在宗教中,人的幻想、人的頭腦和人的心靈的自主活動對個人發生作用不取決于他個人,就是說,是作為某種異己的活動,神靈的或魔鬼的活動發生作用”[4]160。也就是說,人們將自身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或者外化為一種異己的、充滿神秘屬性的存在物,從而自己跪拜在自己的創造物面前而頂禮膜拜。這種意識形態領域宗教幻象的實質在于,“人腦的產物表現為賦有生命的、彼此發生關系并同人發生關系的地里存在的東西”[2]90。于是,人們就在自己的頭腦里構造出一個彼岸的宗教世界出來,并且沉浸在這個作為現實世界之宗教映射或投射的幻境中,將之視為唯一真實的世界。
在商品世界里,也有著與宗教世界這個幻境相類似的現象。它以人與物關系顛倒的方式蘊含在商品的價值形式中,并集中體現為生產者與他自己的商品之間關系的本末倒置。由于價值關系本身的矛盾,進而在價值表現中衍生出一系列感性與超感性、具體與抽象、普遍與特殊的顛倒性幻象,并滋生出人們的商品拜物教這一主體迷誤。在這個人們自己構筑出來的世界里,他們把自己首先化身為交換價值這個抽象的價值實體,并且將價值表現對象化于一個具體的有用物上面,進而又將價值當做一種天然的屬性賦予這個作為等價物的商品身上,從而為商品鍍上了一層神秘的玄幻色彩。
針對商品世界本身的這種特性,馬克思認為,“這是物質生產中,現實社會生活過程(因為它就是生產過程)中,與意識形態領域內表現于宗教中的那種關系完全同樣的關系,即主體顛倒為客體以及反過來的情形”[5]469。“這只是人們自己的一定的社會關系,但它在人們面前采取了物與物的關系的虛幻形式。因此,要找一個比喻,我們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這其實與宗教世界里人們對自己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及神秘化相類似,“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產物也是這樣,我把這叫做拜物教”,這乃是包括資本主義發達的商品生產在內的一切商品生產形式本身所必然具有的性質,即“勞動產品一旦作為商品來生產,就帶上拜物教性質,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產分不開的”[2]90。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龐大的商品堆積”的世界,不但“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2]47,而且“勞動產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價值形式,就是經濟的細胞形式”[2]48。因此,在商品這里,就內在地蘊含著資本主義拜物教的因子,或者說資本主義拜物教實際上就以萌芽的形式潛存在商品這個細胞形式中。正因如此,對資本主義拜物教的批判,就必須首先對商品形式中所蘊含著的拜物教性質進行深入的剖析。亦因此,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拜物教的批判,首要就是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
人們的宗教幻象實則是對現實世界的一種歪曲的、本末倒置的映現。換言之,意識形態領域的宗教幻象,實則是現實世界自身的矛盾運動,是以一種顛倒的、歪曲的方式在深受這種關系制約和束縛的人們思維中的投射。與之相類似,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實則也是商品世界自身矛盾運動在深受商品生產這一特定生存方式所制約的人們思維中的反映。與人們在宗教意識形態領域更多地體現出主觀的認識論迷誤不同的是,在商品拜物教這里,人們更多地是體現出一種“實踐迷誤”,即人們不自覺地甚至自然而然地將他們自身的本質力量及其社會性質對象化為獨立于他們之外的價值實體,并且進而使得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被轉化和置換為價值關系。“商品世界的這種拜物教性質……是來源于生產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2]90究其根本而言,商品拜物教之謎根源于商品生產這一特定的生產形式本身的矛盾,并且集中體現在價值關系中所蘊含的一系列顛倒本性中。
二、相對價值形式中的拜物教傾向
究其實質而言,價值關系所表征的是兩個不同的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商品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價值關系實際上成了商品世界里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質的規定。在這種生產方式中,人們各自是作為商品生產者和占有者而存在的,“他們必須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2]103,即必須彼此承認各自是自己商品私有者這個客觀事實,從而必須通過商品交換這個渠道和中介才能夠實現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這就意味著,對于任何一個單個的商品生產者而言,他的生產就不是直接地為自己進行生產,而是為別人生產以滿足他人需要的使用價值。換言之,他是把產品當做商品去生產,從而純粹地是為了實現自身產品的交換價值。不僅如此,這些商品生產者和所有者在這里已然無法自我確證自身的社會性質以及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主體只有通過等價物才在交換中彼此作為價值相等的人,而且他們只是通過彼此借以為對方而存在的那種對象性的交換,才證明自己是價值相等的人。”[1]也就是說,他們唯一地只有通過結成一種實則外在于和獨立于他們之外的價值關系,他們才能在確立彼此的社會聯系的基礎上獲得各自的生存生活之需。然而,也正是在價值關系的確立過程中,在價值形式的兩個對極,即相對價值形式以及等價形式那里,自然地滋生出逐步加重的拜物教幻象。
一旦商品生產者唯一地將自己的產品當做商品去生產,就意味著他們將自身的社會性質轉化為一種抽象的交換價值,并且進一步在交換活動中將之對象化。這是通過兩個不同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價值關系來實現的。“最簡單的價值關系就是一個商品同另一個不同種的商品(不管哪一種商品都一樣)的價值關系。”這種最為簡單的價值形式可以用如下這個等式進行表現,即“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馬克思這里是以“20碼麻布=1件上衣”這個最為普通的交換關系作為例子[2]62。這一價值表現本身有著對立統一的兩極。由于麻布要表現自己的價值,因此它的價值在這里表現為相對價值,并處于相對價值形式這一極;而上衣則處于等價形式這一極,對麻布起著等價物的作用。但一個不容忽略的經驗前提在于,麻布和上衣之所以處于相對價值形式和等價形式,這決非自在自為的事情,作為其支撐的是這樣一個經驗事實,即“這只是對同時出現的兩個不同的個人來說,而且只有在同時出現的兩個不同的價值表現上才是這樣”[7]151。因此,對于上面這個價值形式來說,它所表征的或者承載的乃是兩個不同商品生產者和所有者之間的社會聯系。“對A來說,他的麻布——因為對他來說,首先是從他的商品出發——處于相對價值形式,而另一個商品上衣,則相反地處于等價形式。在B看來,情況正好相反。”[7]151這里存在著一個奇怪的現象。顯然,價值關系及其形式唯一地就是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呈現,從而價值關系的本質內容就是社會關系。然而,這在從事生產和參與交換的人們看來,它純粹地是兩種物即麻布和上衣之間的交換關系。正因如此,馬克思認為,“一切價值形式的秘密都隱藏在這個簡單的價值形式中”[2]62。也就是說,即使在這個最為簡單的價值關系及其價值表現中,也蘊含著人與物關系的顛倒,并且隱藏著拜物教性質。
在這個價值表現中,織工的產品麻布自身的價值是無法自我顯示的,“麻布的相對價值形式要求另一個與麻布相對立的商品處于等價形式”[2]63。也就是說,它必須通過其對立面的另外一個商品(上衣)相對地表現出來。因此,在這個價值形式中,就隱然地有一個作為前提的基礎——“不論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個這樣的比例總是包含這樣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為價值量是同一單位的表現,是同一性質的物”[2]64。因此,在這個價值表現中,在織工和縫工他們之間的這個價值關系中,“麻布=上衣是這一等式的基礎”[2]64。這才是價值關系及其等式成立的前提性的關鍵所在。然而,幾乎所有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都忽略了這個“質之同一”而專注于價值量的分析。并且,正如上文所述,這兩個被看做質上等同的商品分別起著不同的作用。麻布在這里是作為相對價值存在的,它需要上衣擔當等價物這個角色。因此,在這個等式中,上衣構成麻布的價值存在形式,“因為只有作為價值物,它才是與麻布相同的”[2]64,它因而就成了價值物或表現麻布價值的商品。兩個不同種的商品(例如麻布和上衣)之所以能夠被看做質之等同,顯然是由商品體自身的二重性決定的,即任何一個商品,它們都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統一體。并且,對任何商品而言,在作為勞動產品而撇除掉自身使用價值的差異后,它們共同地都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或結晶。但把商品看做價值,這其實是我們基于商品體自身的內在規定,即通過分析把商品化為價值抽象,但是并沒有使它們具有與它們的自然形式不同的價值形式。換言之,這僅僅是基于商品自身矛盾規定的一個觀念抽象,“價值”實則被歸結為商品的社會屬性,從而價值形式被看做不同于其自然形式的社會形式。這里已然蘊含著作為商品“幽靈般的對象性”[2]51的價值屬性必然地就是一種社會的價值對象性,即它必須通過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社會關系即交換關系才能被表現出來。
在相對價值形式這里,商品體的這個幽靈般的價值對象性以其獨有的方式表現了出來,也就是說,它是通過對象化到獨立于其外部的另外一個商品身上得以體現的,作為表現自身價值的商品A,將自身的這個相對價值對象化到其對等的等價物B之上,由此確證了自身價值的存在。從而,“一個商品的價值性質通過該商品與另一個商品的關系而顯露出來”[2]65。例如,在“20碼麻布=1件上衣”這個普通的價值等式中,二者之所以等同,根本上顯然是由于它們蘊含著同等的人類勞動。并且,在這個價值關系中,麻布和上衣都是首先被化為這個同質的東西,即被當做同一性質的物,被當做價值。因此,當麻布將自身的價值對象化在作為等價物的上衣之上時,上衣“是當作表現價值的物,或者說,是以自己的可以琢磨的自然形式表示價值的物”[2]67。也就是說,麻布之所以能夠將自身價值對象化到上衣上面,一個前提的規定就是它們都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凝結。因此,在這里物體上衣或作為使用價值的上衣是被織工直接地當做價值了,或者更為確切地說,上衣被麻布生產者織工直接地當做了自身商品價值對象化的承載,從而成了價值的化身,“物體上衣代表著它和麻布所共有的價值實體即人類勞動”[7]153。正是這樣,在麻布生產者織工看來,就出現了如下景象:從使用價值即自然形式這個角度看,麻布和上衣當然是不同的商品,即它們是根本不同的、具體的可感物;但是,當上衣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去充當麻布的等價物時,它卻又成了和上衣毫無區別而質之等同的東西,“即使上衣扣上了紐扣,麻布在它身上還是認出與自己同宗族的美麗的價值靈魂”[2]66。因而麻布就被其生產者織工先在地或近乎先驗地看成了“上衣”。
馬克思明確指出,麻布通過價值等式取得與其自然形式不同且獨立于其外的價值形式,即它的價值存在通過它和上衣相等表現出來,這一點“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過他和上帝的羔羊相等表現出來一樣”[2]66。這個既形象又深刻的判斷,實則充分道明了在相對價值形式這里蘊含著的人與物關系的顛倒及其拜物教傾向。在這里,正如我們已然分析的,作為前提的是兩個不同的商品所有者織工和縫工之間的價值關系,無論是這個價值等式成立的基礎還是其量的規定性,歸根結底都是人類勞動及其勞動時間對象化到商品生產這個特殊生產勞動中的結果。然而,這個作為前提支撐的物質基礎是不為生產當事人所注意和察覺的。在這些商品生產者和所有者眼中,價值關系不是他們自己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和內容,而成了兩個不同商品之間純粹的物的關系。并且,僅就這里分析的相對價值形式而言,當麻布取得獨立于其外的價值表現形式,從而當另外一種商品上衣以自己的自然形式表征麻布的價值的時候,對于作為賣方的麻布生產者而言,上衣就自在地有著價值這個天然的社會屬性,或者說,價值就作為一種自然屬性從屬于上衣。上衣因而就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2]88,一個充滿靈性的東西。這一點對于沉浸在商品世界中、受制于價值關系的人們來說,甚至已然是一個自然而然而又平凡無奇的事情。然而,價值作為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或結晶,原本不過是對具體的、可感的作為使用價值的商品體的抽象屬性。但現在,這個“抽象”卻不但取得自身實體存在,而且對象化到一個具體的可感的物上面。如此一來,具體的東西反而成了一個超乎于其上的“抽象”的化身,這因而就“充滿形而上學的微妙和神學的怪誕”[2]88。在以柏拉圖主義為圭臬的舊哲學那里,有一個眾所周知的經典預設:感性事物只有“分有”作為其“型相”的理念才能確證自身的存在,從而感性事物不過是理念的化身。這在中世紀基督教那里發展為一種濃烈的神學懸設:上帝是人的創造者,人是上帝的肖像。在相對價值形式這里,商品生產者確證自身價值存在的方式,正是通過這樣一種充滿形而上學玄幻而又隱然地帶有神學韻味的方式實現的。
這種拜物教傾向,在相對價值形式的等價形式那里得到了最為明顯的表現。對此,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法文版附錄中,將這個帶有強烈形而上學色彩和神學味道的商品拜物教專列小結闡明,“等價形式的第四個特點: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價形式中比在相對價值形式中更為明顯”[7]161。事實上也確實如此。在價值關系的等價形式這里,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質得到最為集中的體現和凸顯。
三、等價形式中的拜物教性質及其凸顯
仍以“20碼麻布=1件上衣”為例,上衣在這里是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即作為一個自然的物理客體而成為麻布的等價物。“上衣因而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屬性,即處于能夠與麻布直接交換的形式”[2]70,上衣實則是以自己的使用價值這個自然形式成為它的對立面即麻布的價值表現形式。這因此也構成等價形式的第一個特點。顯然,直觀地看(尤其是對于那些處于這個交換關系中的主體來說),等價形式的這個特點在于,“商品的自然形式成為價值形式。”然而與價值關系的確立是建立在兩個不同的人之間的交換活動這個作為客觀前提的經驗事實一樣,這里發生的物體上衣成為價值形式的這個轉換,“這種轉換只有在任何別的商品A(麻布等等)與它發生價值關系時,只有在這種關系中才能實現”[2]71。也就是說,只有在價值關系中,更為確切地說,只有在等價形式中,處于等價形式這一極的某一商品才能作為另外一種處于其對立面(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的等價物,以它自身的自然形式擔當價值存在物這個超感樣態。這一點的玄幻性其實在相對價值形式那里就已然蘊含著,在那里,它集中表現為感性與超感性的對立。然而,商品生產者A使得自己的商品在它之外取得一個同質等量的價值存在,這一點雖然隱藏著形而上學的微妙,但是“這個表現本身就說明其中隱藏著一種社會關系”[2]72,即作為生產和交換的雙方當事人來說,他們雖然意識不到彼此交換關系所蘊含的對立和顛倒,然而他們都清楚這是彼此之間的社會聯系。但在等價形式這里,這種隱約感觸到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印象就被進一步地虛無化和蒸發了。
這種虛無化根本上是由等價形式本身的特性所導致的。“等價形式恰恰在于:商品體例如上衣這個物本身就表現為價值,因而天然具有價值形式。”[2]72雖然從事交換活動的雙方當事人,都不會否認這個“天然價值形式”是在他們彼此之間的社會聯系中確立的這一基本經驗事實,然而,他們其實卻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或者說,由于他們先行地將自身本質力量及其社會性質轉化為價值客體,因而必然導致他們在交換活動中忽略掉這個前提而緊緊地抓住眼前這個結果:商品自在地有著自己的天然屬性“價值”。另外,又由于在勞動產品采取商品生產這種方式下,價值作為商品的屬性“不是由該物同他物的關系產生,而只是在這種關系中表現出來”[2]72-73,即任何一個商品都無法自我顯示自己的價值存在,因此必須通過交換活動及其價值關系,將蘊含在自身內的“幽靈般的對象性”對象化到獨立于其外的另外一個具體物體上。因而,這種帶有強制性的必然性就導致如下錯覺的出現,“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價形式,天然具有能與其他商品直接交換的屬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屬性或保暖的屬性一樣”,“從這里就產生了等價形式的謎的性質”[2]73。這種迷幻進一步體現在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那里。這個特點其實是由第一個特點所直接引發和導致的。當商品以自己的自然形式去充當另外一個商品的價值形式,這其實意味著這個商品的物體形式或者自然形式被當做了價值形式。進而言之,這實則更進一步意味著,它被當成了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即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然而,就制作這個“有用物”或“使用價值”的勞動而言,它并非抽象的一般人類勞動,而是具體的、一定的、有用的某種勞動。因此,一方面,商品的相對價值形式必須表現在不管是哪種有用物、但必須是一般人類勞動的化身的價值體上面;另一方面,充當等價物的商品,即“等價物的一定的物體形式,無論是上衣、小麥或鐵,都始終不是抽象的人類勞動的化身,而是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7]157。例如,裁縫的勞動、農夫的勞動或木工的勞動的化身。正是這樣“因此,生產等價物商品體的一定的、具體的、有用的勞動在價值表現中必然總是被當作一般人類勞動,即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定的實現形式或表現形式”[7]157-158。這就意味著,正如在第一個特點那里,從直觀表現這個角度看,等價物的使用價值直接地就是價值形式;同樣地,在第二個特點這里,一種商品當它作為等價物時,它直接地就是以一種具體勞動充當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由此也就直接地推導出等價形式的第三個特點,即“私人勞動成為它的對立面的形式,成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2]74。
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質或者說商品拜物教的品性,在等價形式這里表現得一覽無余而又極為突出。在以上等價形式的三個特點中,存在著一個貫穿其間的顛倒本性。也就是說,“在價值關系及其所包含的價值表現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東西當作具體的、可感覺的現實的東西的屬性,而是相反,可感覺的具體的東西被當作只是抽象的一般的東西的表現形式或一定的實現形式”[7]158。例如,在作為等價物的上衣那里,包含在它里面的“裁縫”這個特定的具體勞動,作為與麻布的價值表現相對應的存在樣態,并不具有也是人類勞動這種一般屬性,“相反,它是人類勞動這一點被當作是裁縫勞動的本質;而它是裁縫勞動這一點卻被當作只是它的這種本質的表現方式或一定的實現方式”[7]158。就這一轉換本身而言,它實則由商品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矛盾和必然性所致,即只有抽象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才凝結成價值,從而價值只能是一般的、社會化的人類勞動的結晶。然而,價值關系的這一必然性卻是以顛倒的方式表現出來的。對此,馬克思明確指出,“這種顛倒是價值表現的特征,它使可感覺的具體的東西只充當抽象的一般的東西的表現形式,而不是相反地使抽象的一般的東西充當具體的東西的屬性”,并且正是“這種顛倒同時使價值表現難于理解”[7]158。馬克思這里對關于價值形式本身所蘊含的顛倒關系的揭示,顯然是與上述相對價值形式以及等價形式的分析相契合的。在相對價值形式那里,作為等價物的商品直接地是以其自然形式即具體的可感的有用物這個使用價值形態,來充當另外一個商品的價值形式的。或者說,相對價值形式這一端的商品蘊含的“幽靈般的對象性”,是通過對象化到其對立面一個可感的具體的物理客體上面的,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實則就是一種經典的柏拉圖主義的幻象架構。而在等價形式那里,這種顛倒本性及其幻象更為突出。相對價值形式那里雖然已然蘊含著可感與超感的對立,一個商品的價值對象性通過價值關系將之對象化到一個獨立于其外的具體的物理客體身上,這件事情本身雖然充滿了形而上學的微妙。然而,作為生產和交換的當事人,人們還是隱約地能夠體驗和覺察到:這是他們兩個不同的商品所有者在從事著交換活動。但在等價形式那里,這種感覺就徹底消失了。因為,等價物直接地就以可感的具體的物理客體形式去充當抽象的普遍的價值實體的屬性或表現方式。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顛倒本身的形而上學玄幻及其神學特色,馬克思舉了一個淺顯的例子,“如果我說羅馬法和德意志法都是法,這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如果我說法這種抽象物實現在羅馬法和德意志法這種具體的法中,那么,這種聯系就神秘起來了”[7]158。這個例子的指向性在于,如果如此預設的話,實則是意味著存在著一個大寫的“法”(法律本身,法律的Idea,即法律的型相)。從而存在著一個獨立于一切現實中具體法律之外的法律實體,不但如此,這個實體還是一個神秘的主體,因為現實中所有的具體法律條文都是這個作為實體的“法”對象化的產物和結果。正是如此,當在價值形式那里存在著這樣一個質的統一的顛倒品性的時候,商品世界就因而充滿了由人與物顛倒所必然導向的拜物教性質與氣息。通過以上關于價值關系及其形式的分析,這種顛倒首要地就是價值關系本身矛盾的顛倒表現,因而它絕非一種主觀的任意的錯覺,包括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們在內,生活在商品世界中的人們都可以抽象地、一般地意識到,價值或交換價值本質上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系。然而,早已沉浸在一種人與物關系顛倒的幻象中,并且更是根本地在他們自己的商品生產和交換活動中去這樣實踐的這些抽象的人們,他們是無法覺察到這種價值關系本身是被物的外殼所遮蔽和掩蓋著的。
人們之間不是直接地用自己商品的使用價值,從而不是以商品的自然形式去結成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而是只有將自己的商品(具體的有用物)轉化為并當做交換價值才能同別的使用價值相交換,因而“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可以說是顛倒地表現出來的,就是說,表現為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8]426。這種人與物關系的顛倒對于沉浸在商品世界中的人們來說,對于價值關系構成其社會關系的本質內容的人們來說,是一件司空見慣的事情。“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采取了一種物的形式,以致人和人在他們的勞動中的關系倒表現為物與物彼此之間的和物與人的關系,這種現象只是由于在日常生活中看慣了,才認為是平凡的、不言自明的事情。”[8]427由于這種顛倒本身是價值關系自身矛盾必然展開的結果,因此這些處于價值關系中的人們必然產生與之相應的拜物教主體迷誤,“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2]91。馬克思對此作了進一步闡釋:“如果我說,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當作抽象的人類勞動的一般化身而同它發生關系,這種說法的荒謬性是一目了然的。但是,當上衣、皮靴等等的生產者使這些商品同作為一般等價物的麻布(或者金銀,這絲毫不改變問題的性質)發生關系時,他們的私人勞動同社會總勞動的關系正是通過這種荒謬形式呈現在他們面前。”[2]93顯然,這個例子根本不是對一個偶然現象或者經驗事實的描繪,而是對這些生產當事人所采取的“商品生產”這種生產方式本身的矛盾、性質及其獨特的表現方式,從而是對商品生產之內在矛盾及其外部表現的科學剖析。
這種關于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們那里,被進一步夸大為一種意識形態粉飾。在日常生產當事人的意識中,商品內在地具有價值及其價值量的天然屬性,而這一點“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中,它們竟像生產勞動本身一樣,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經濟學對待資產階級以前的社會生產有機體形式,就像教父對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樣”[2]99。馬克思認為,這種拜物教迷誤甚至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優秀的代表人物,例如亞當·斯密和李嘉圖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在他們那里集中表現為近乎統一地“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2]99。他們之所以這樣做,除了由于深受經驗實證主義束縛從而無批判地沉醉在了對價值量的分析那里,而忽略了更為前提和根本的問題;更為根本的原因在于,這是他們狹隘的資產階級視野所致。“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質。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掉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2]99古典經濟學這里將勞動一般地看做價值的創造者,從而部分地實則客觀上揭示了為物的形式所遮蔽和掩蓋的資本生產的內容。但是,在庸俗經濟學家們那里,古典經濟學所蘊含的客觀的科學性就被消解殆盡了,“庸俗經濟學卻只是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它為了對可以說是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為了適應資產階級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復咀嚼科學的經濟學早就提供的材料”[2]99。因此,究其實質而言,“庸俗經濟學則只限于把資產階級生產當事人關于它們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陳腐而自負的看法加以系統化,賦以學究氣,并且宣布為永恒的真理”[2]99。對此,馬克思認為,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可以在他們針對自然在交換價值的形成中的作用而進行的“枯燥無味的爭論中得到證明”[2]100。由于交換價值不過是表示消耗或耗費在物體上的勞動的一定的社會方式,或物化在產品中的社會化勞動,這種將交換價值歸結為自然物質及其屬性的做法,因而就不但荒謬且充滿了拜物教意味。
四、結論
商品生產這一生產方式所蘊含的人與物關系的顛倒,亦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轉化和置換為商品生產者與商品之間的價值關系,并在價值關系本身之內在矛盾的推動下,以顛倒的、本末倒置的方式呈現在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當事人的實踐及其意識中,由此就構成商品拜物教產生的客觀基礎及其主體迷誤。作為一切商品都蘊含的抽象的“幽靈般的對象性”這個價值屬性,基于商品生產這一生產方式內在的客觀矛盾,通過人們之間的交換活動,自我對象化于一個獨立其外的物理客體之上;同時,形成價值的抽象勞動原本不過是具體有用勞動的社會性質及其普遍性規定,在價值關系及其形式中則相應地在一種具體的、特殊的有用勞動中體現出來。商品生產本身矛盾的這種自我顛倒,使得處于商品生產和交換中的那些當事人必然地產生與之相應的主體迷誤。在他們看來,價值不是商品的社會屬性或只有基于社會關系才能確立的屬性,而是商品自身自在地蘊含著的如重量、保暖一樣的天然屬性;價值關系不是他們之間以特定方式確立和運行著的社會關系,而是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價值關系;作為人們抽象勞動凝結和結晶的產物,超感性的東西不但被人們幻化為實體,并且進而被人們自己在他們的實踐活動中賦予其神奇的主體力量,由此使得商品世界成了一個如宗教世界一般的幻境。在這里,人們是商品的生產者和創造者這個主體地位被他們實現自身主體力量的方式所消解和虛無化,商品之間的價值關系運動也成了獨立于人們之外的一種神秘的異己的運動,由此導致了“在交換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2]92。作為整個商品生產方式本身及其價值關系矛盾運動的結果,商品世界又自然地成了被物這一抽象外殼所遮蔽和掩蓋的世界。這種境況和景象僅僅存在于采用商品生產的資本主義社會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里。在中世紀,“正因為人身依附構成該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產品也就用不著采取與它們的實際存在不同的虛幻形式。它們作為勞役和實物貢賦而進入社會機構之中”,“在這里,勞動的自然形式,勞動的特殊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產基礎上那樣,勞動的一般性是勞動的直接社會形式”[2]95。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直觀地體現在他們勞動產品之間的關系中,或者說,他們的勞動產品直接地就體現著他們之間的社會關系。例如,雖然徭役勞動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也是用勞動時間去計量的,“但是每一個農奴都知道,他為主人服役而耗費的,是他個人的一定量的勞動力”;同樣地,“交納給牧師的什一稅,是比牧師的祝福更加清楚的”,這就越發顯得在采用商品生產這個生產方式的社會中人與物關系顛倒的特殊性所在,“無論我們怎樣判斷中世紀人們在相互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們在勞動中的社會關系始終表現為他們本身之間的個人的關系,而沒有披上物之間即勞動產品之間的社會關系的外衣”[2]95。對此,馬克思以原始的或自然經濟狀態下的農村家長制生產以及未來“自由人聯合體”的勞動生產為例,進一步指出了商品生產及其拜物教性質本身的歷史合理性及其限度,“只有當實際日常生活的關系,在人們面前表現為人與人之間和人和自然之間極明白而合理的關系的時候,現實世界的宗教反映才會消失”,而這只有在如下這個歷史條件下才能實現,即“只有當社會生活過程即物質生產過程的形態,作為自由聯合的人的產物,處于人的有意識有計劃的控制之下的時候,它才會把自己的神秘的紗幕揭掉”[2]97。因此,這是需要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和現實的歷史前提的,并且這必然地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甚至痛苦的有著一定限度的歷史過程。
總之,歸根結底,商品世界的拜物教性質是以商品生產為勞動生產方式的社會所必然導向的一個結果及其主體迷誤。這在根本上受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的制約,即一方面是彼此獨立的私人生產,生產資料為私人所占有,而另一方面是社會化的商品生產的日漸拓展。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在私有制條件下最終只能通過日漸擴大和成熟的商品交換這個中介渠道予以解決。因此,價值關系構成商品生產方式下人們之間社會關系的本質內涵、價值形式構成他們之間社會關系的表現方式,這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和客觀的物質基礎支撐。之所以商品生產方式本身內在地有著拜物教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價值規律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所導致的。價值規律在整個交換關系中是以一系列顛倒的方式(感性與超感性、抽象與具體、普遍與特殊等方面的對立)發揮作用的,它自身以這種獨特的方式所呈現出來的自然的必然性,由此必然使得沉浸在商品世界中的人們產生拜物教的主體迷幻。因此,拜物教可謂附著在商品生產上面的一層自然的“顏色”,它的產生是商品生產本身矛盾運動的結果,并且這種顛倒的表現方式必然以直觀的形式投射在處于這一矛盾運動中的生產者那里,從而產生與之相適應的拜物教迷誤。
參考文獻:
[1]高嶺.商品與拜物——審美文化語境中的商品拜物教批判[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2]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Mikhail Lifshitz.The philosophy of art of marx[M].London:Pluto Press,1972:35.
[4]馬克思.馬克思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0.
[5]馬克思.馬克思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9.
[6]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6.
[7]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8]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