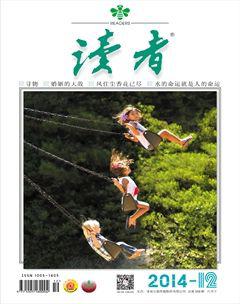尼曼匹克之疾
李茂君
絕癥尼曼匹克
今年45歲的汪永忠頗顯蒼老,同事們多稱其為“老汪”。在長達一個下午的交流中,盡管窗外春意盎然,但難博他燦然開懷。
2001年,汪永忠的女兒汪芯羽出生,不到1歲就喃喃叫著“爸爸媽媽”,身體發育正常。3歲,能用珠心算做20以內的加法,還喜歡跟著電視音樂節目學唱歌,舉手投足有模有樣。在親友眼里,小羽是個十分討人喜歡、天真聰穎的孩子。
當時,老汪夫婦還在家鄉湖南株洲市的國營玻璃廠謀生,中專畢業的老汪被安排進待遇不錯的廠醫院。他一心求學深造,學歷從中專刻苦進修到大專、本科,2005年更是考取了昆明醫學院研究生,隨后獨自去昆明求學。
然而沒多久,不幸猝然而至:小羽握筆寫字時,右手不聽使喚地開始顫抖。
老汪回憶,當時以為孩子年齡小,才4歲,握筆不穩,沒有重視。但1年后,不明顯的顫抖發展成間斷性發抖,連端杯水都不行!
醫院的檢查結果讓老汪迷惑不已——“未見任何異常”。老汪留心觀察,小羽確實變得“異常”了:講話語速遲緩,動作協調平衡差,尤其是做追跑游戲時動作笨拙;就連對以前最愛的看電視、學唱歌她也沒了興趣,注意力無法集中;膽子變得很小,被小伙伴推搡后,會突然大哭或良久發呆……直到有一天,小羽的腿變成了X形,站立時踝關節間隔4厘米,平躺才能并攏。老汪意識到事情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但問題到底出在哪了?多家醫院的診斷結果,不是“未見異常”,就是不明就里,搞得老汪一頭霧水,茶飯不思。眼看時間流逝,孩子進食飲水嗆咳、大小便失禁,癥狀日益加重,老汪心焦得要命。
回想女兒的病情,3次頭部外傷史讓他非常痛心,一度懷疑這是癥結所在,他埋怨自己的粗心大意害了孩子。孩子3歲時被健身器材碰傷了左額,隨之后腦倒地,左額裂開了長達6厘米的口子,因為CT檢查未見異常,匆匆縫合了事;6歲時,小羽玩跳繩時摔傷,右臉和雙眼周圍皮膚立刻變得青紫,但經X線、CT檢查均未見異常;同年,小羽跑進教室后,頭部重重地摔在墻角上,頓時流血不止、昏迷不醒,經過一番緊張地搶救才得以恢復意識。這一次,診斷終于有了明晰答案:腦震蕩、頭皮裂傷、頭皮血腫。

小羽不得不休學治病。妻子辭了職,專門在家照顧孩子,當時老汪最怕愛人打來電話:“手機一響,我的第一反應就是‘孩子出什么事了?精神壓力非常大。”每每聽到孩子病情加重,他便立馬趕乘30多個小時的火車回老家,等親眼看著孩子病情緩解,再拖著疲憊不堪的身體獨自返回昆明。這種鐘擺式的行程,他一年要經歷幾十次。
“為何不把孩子接到自己身邊?”老汪解釋說,昆明海拔高,孩子呼吸很困難,只來過一次便渾身不適。一旦工作能抽開身,老汪就帶著孩子北上南下求醫,一家人走遍了株洲、長沙、昆明、武漢、長春、北京等地幾十家醫院。艱難的求醫之路換回的卻是孩子的病情步步惡化,她已無法站立、抬頭,時常抽搐、眼珠上翻、口吐白沫,整個人瘦得皮包骨頭……
小羽發病5年后,事情總算有了“轉機”。2010年5月,老汪經人推薦到北大婦兒醫院求醫,小羽被確診為罕見病“尼曼匹克C型”。盡管老汪對這個醫學名詞知之甚少,但在那一刻,他卻感到“終于知道是什么病了,沒有疑惑,心里自然輕松了不少”。
老汪深知,確診與治愈之間橫亙著鴻溝巨壑,自己必須時刻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
小羽在2012年安靜離去。“她不用再受折磨了。”老汪木然地說。但留存于他內心的各種折磨,并未消解。
命運的魔咒
如今的老汪很消沉,“做什么都沒勁”。孩子看病欠下的巨款,壓在他的肩頭上,令他喘息不得。電腦桌面依舊是小羽的笑臉,幾年都沒變。盡管極力想忘卻,可一旦無事可干時,他還是會不由自主地翻看孩子的照片。
原本研究職業病的他,當初為了解“尼曼匹克”,光是相關論文就啃了數百萬字,儼然成為“尼曼匹克”專家。老汪告訴記者,所謂尼曼匹克,簡單來說是一種脂質代謝異常的遺傳疾病。過量的脂類累積于人的肝臟、腎臟、脾臟、骨髓,甚至腦部,造成器官病變。這種病分A、B、C、D四種類型——A、B型屬于酸性神經鞘磷脂酶缺乏或活性不足,A型最嚴重,生命期通常小于3年;C、D型則是細胞內膽固醇代謝、運輸障礙。C型多在學齡期發病,癥狀以肝脾腫大為主;D型特指在加拿大東南部新斯科加區域的病患,該地發生率約為其他區域的1000倍。
老汪說,“尼曼匹克”目前尚無治愈方法,特別是對神經系統的破壞無法緩解。“一旦患病,注定是逃脫不掉的災難”。他加入了“尼曼匹克之家”公益群,這里都是陷入絕境的父母。有一定醫學知識積累的他,有空就為其他患者家庭答疑解惑。他推薦記者以志愿者身份加入該群,從早到晚,消息框一直在彈跳,跳出一個個雷同的故事。
不久前的一個燦爛春日,一位母親帶著兒子去濟南某醫院取化驗單,醫生沉重告知:“孩子得了‘尼曼匹克,沒法治。”這位母親走出醫院大樓后,緊緊抱著兒子失聲痛哭……而就在拿化驗單的幾分鐘前,母子倆在醫院走廊碰見一個面目全非的燒傷病人,母親捂著兒子的眼睛催促其快走,怕他因害怕而失聲大叫,傷了人家的自尊。
還有一位叫萌萌的湖南郴州女孩,剛滿9個月,被確診罹患“尼曼匹克”,已在重癥監護室隔離治療1個月。她的肝脾在快速增大,直接影響到肺部呼吸,并引發肺炎,現在她只能靠呼吸機維持生命。萌萌媽哀求醫生用手機拍下萌萌的照片,以解思念之苦。她的嘴唇混雜著熱淚輕吻手機屏幕,泣不成聲。她告訴記者:“醫生說孩子無藥可救了,多數患兒幾歲就夭折。我們眼睜睜地看她受苦卻束手無策,唯一的希望就是醫院能盡快研究出治療辦法。”
另一些家庭,不惜各種嘗試,在生命線上掙扎,尋求轉機。
熊邦鳳是其中一例。這位現年50歲的農婦來自江西省永修縣,1989年生下女兒小舟,小舟半歲時被查出肝脾腫大;兩年后,兒子星星出世,也重蹈姐姐的覆轍,1歲半時也被發現肝脾腫大。折騰了三五年,疲憊的他們抱著最后的一線希望趕赴北京,結果依然一無所獲。到了2000年,小舟“肚子脹得老大”,醫生建議盡快做脾臟切除手術,哪知“脾臟太大,無法切除”,后來醫生臨時決定將脾臟的血管扎死三分之二,以延緩病情惡化。熬到2004年,小舟終因肝腹水離開人世。
星星會逃脫命運的魔咒嗎?他在美國某醫藥公司的資助下,經北京協和醫院確診為“尼曼匹克B型”,但苦于無藥可治。2012年年末,在中國尼曼匹克關愛中心、“愛肝一生計劃”、天使媽媽基金等公益機構和社會愛心人士的幫助下,熊邦鳳在北京武警醫院“割肝救子”。盡管這個家庭因后續治療而不堪重負,但仍堅信愛的奇跡,彼此不離不棄。
罕見病不罕見
“孤兒病”是罕見病的民間說法。國際上已發現7000多種罕見病,約80%屬于遺傳性疾病。盡管單個病種的患病率很低,但由于病種繁多,因此患者群體龐大。以我國14億人口之巨,罕見病其實并不罕見,據統計,總數近2000萬人。
“罕見病是個醫學問題,也是一個亟須解決的社會問題。我們每個人在面臨生命起承轉合時,不得不被動接受幾十萬分之一的風險。”老汪呼吁全社會關注罕見病。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罕見病定義為患病人群占總人口0.65‰~1‰的疾病或病變。在我國,約定俗成的罕見病概念是指患病率低于五十萬分之一的疾病。新生兒發病率低于萬分之一的遺傳病,稱之為罕見遺傳病。約有50%的罕見病在出生時或兒童期發病,病情惡化迅速,死亡率較高。
由于我國對罕見病的研究起步晚,臨床醫生常因積累不足,出現誤診或漏診,不少患者直到病故都未能查清病因。
老汪說,多數罕見病患者對自己的疾病知之甚少,不但不知該如何正確治療,有些人甚至覺得 “自己和別人得的病不一樣”,羞于在社會上呼吁,爭取應有的醫療保障。
數據統計,罕見病的部分治療費用遠超醫保支付的封頂線,哪怕是在醫保水平較高的北京,醫保支付的封頂線也僅為居民收入的6倍,即平均每人每年30萬元,而很多罕見病的年醫療費用超過100萬元。很多患者家庭呼吁建立罕見病專項救助基金。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家族沒有患病史,罕見病就和自己沒有關系,因此不關心、不關注。”全國政協委員、新華醫院消化內科主任、上海醫學會罕見病專科學會李定國教授善意提醒,“事實上,大部分罕見病是由于遺傳缺陷引起的,缺損的基因碰在一起,就有發生罕見病的可能性。換言之,罕見病不是單獨的群體和數字,每個人都有可能遇上。”
(阿 喆摘自《解放日報》2014年5月6日,王 青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