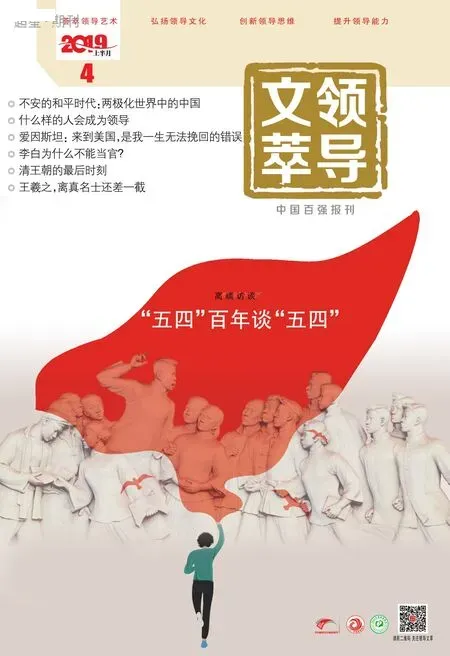泰國政治和解三大障礙
周方冶
兩條國家發展道路的對立
從本質來看,政治就是對經濟社會利益的權威性分配。泰國政治的持續動蕩,很大程度上源于各派政治力量在事關國家發展道路選擇的根本利益問題上,始終無法達成妥協。
從1960年代開始,泰國在軍人威權政府的國家發展主義政策引領下,走上經濟發展的快車道。90年代初,泰國已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并被譽為“四小虎”。但是,長期以來“重城市,輕農村”政策指針,使得泰國面臨嚴重的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問題,并逐漸成為阻礙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的瓶頸。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后,有關國家發展道路的“再選擇”問題,開始成為泰國社會各界的重要議題。
泰國前總理、“電信大亨”他信作為新資本集團的政治代表,提出了進取性的“他信經濟”道路。一方面,通過“30泰銖治百病”、“農民延期還債”、“鄉村發展基金”、“一鄉一特產”等一系列的“草根政策”切實提高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群體的生活水平和生產能力,協調城鄉發展;另一方面,通過深化對外開放,依托東盟一體化和中國經濟“順風車”,加速國內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從而借外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他信執政期間,泰國社會經濟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尤其中下層民眾更是深受其惠,從而為他信派系贏得了農民群體的擁護與支持。不過,進取性的改革道路在取得收益的同時,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由于泰國社會經濟正面臨發展瓶頸,再加上“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因此發展紅利不足以彌補改革成本。于是,如何在存量改革中公正、合理、有效地進行成本分攤與收益分配,也就成為各方政治力量的關切重點。
長期以來被邊緣化的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民群體,盡管占到總人口的近七成,但是相當貧困,根本無力承擔改革成本,至于新資本集團,盡管占有巨額財富,但規模相對有限,并作為執政集團,很容易利用制度和法律疏漏將成本轉嫁。于是,他信式改革的成本,事實上主要由城市中產階級、軍人集團、官僚集團、傳統產業集團等軍人威權時期的既得利益集團承擔,從而引起各方不滿。
既得利益集團更傾向于泰國國王的“知足經濟”道路,要求遵循保守性的改良道路,立足于現有的社會經濟結構,通過“知足常樂”宣傳引導彌合社會裂痕,規避全球化和市場化風險,自力更生地穩步推動社會經濟發展。
2006年“9·19”軍事政變后,“反他信”陣營將“知足經濟”道路寫入《2007年憲法》,使之成為泰國法定的國家發展指針。不過,無論是2007年的他信密友沙瑪領導的人民力量黨政府,還是2011年他信幺妹英拉領導的為泰黨政府,都在沿著“他信經濟”道路繼續前進,從而引起“反他信”陣營的強烈不滿和持續不斷的反政府運動。
政治權力結構的“再平衡”
1980年代以來,泰國政治權力結構始終保持相對平衡的互制格局,王室—保皇派、軍人集團、地方政客、城市中產階級等各派政治力量彼此制衡,保持政治體系運作的穩定和有序。
90年代初,軍人集團以“反腐敗”為由,發動政變壓制地方政客的權力擴張,并試圖借勢掌權,結果引發城市中產階級的大規模示威集會,并導致“5月流血”事件,最終在普密蓬國王斡旋下,軍人集團被迫交出政府權柄,才使得權力結構再次恢復平衡。90年代末,由于地方政客權力擴張,以城市中產階級為首的各派力量共同推動了《1997年憲法》頒布,試圖通過制度建設對地方政客加以規制和監督。從結果來看,新憲法有力約束了地方政客的權力濫用,但卻并未恢復權力結構的平衡,而是促成了他信派系的政治崛起。
作為新資本集團的政治代表,他信派系的成功得益于三方面原因。首先是來自于新資本集團的充裕政治資金;其次是對農民群體的政治動員,促成了新資本集團“資金”與中下層民眾“選票”的有效結合;再次是《1997年憲法》中有利于大黨發展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
由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泰國各派政治力量起初對他信派系的崛起持樂觀態度,認為具有強人特質的他信出任總理有利于引領泰國走出困境。不過,隨后數年間,他信派系迅速擴張,不僅通過2005年大選囊括了眾議院3/4議席,組建了泰國首屆“一黨內閣”,而且通過“銀彈攻勢”對憲政獨立機構加以滲透,使得各派政治力量很難通過正常渠道對他信派系形成有效制約。再加上他信本人的企業總裁式專斷作風,以及進取性改革主張,最終促使各派政治力量在2006年聯手掀起“反他信”政治運動。
對于“反他信”陣營而言,推翻他信政府不過是形式,恢復權力平衡結構才是根本。“反他信”陣營主持頒布的《2007年憲法》增補了諸多權力制衡安排,試圖以此約束新資本集團的權力擴張。但問題在于,隨著農民群體的政治化,泰國的政治生態早已不是少數精英的政治妥協所能主導。
2007年和2011年的兩次大選,他信派系在“反他信”陣營的壓制下,依托占總人口近七成的中下層民眾尤其是農村民眾的支持,不僅成功贏得大選,而且擁有簡單多數的席位優勢。這就使得反對派的民主黨根本無力在國會發揮制衡作用,從而使“反他信”陣營對重建政治權力平衡結構的期望落空。再加上普密蓬國王年事已高,致使長期被視為權力平衡結構重要支柱的王室—保皇派日漸式微。這就使得“反他信”陣營更急于對他信派系進行壓制,以避免他信在后普密蓬時代成為無可制衡的“民選獨裁者”。
憲政體制“有民主無協商”
1990年代以來,泰國憲政體制建設取得明顯成效。《1997年憲法》更被譽為“民主里程碑”。民主選舉與政治監督的觀念在泰國已深入民心,任何不經選舉取得國家權柄的政治企圖都很難成功。事實上,軍人集團在2006年政變后,曾有過恢復軍人總理的提議,結果遭到各派力量的一致反對。選舉委員會、國家反腐敗委員會、憲法法院等憲政獨立機構的設置,更是有效加強了政治監督力度。
不過,泰國現行體制在政治協商方面的機制建設卻相當薄弱,難以有效保證少數派的利益訴求與政治話語權。盡管從政治運作來看,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確實存在非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商人群體的賄賂和游說,城市中產階級的媒體宣傳和學術建議,尤其是普密蓬國王經由樞密院進行政治斡旋,更是在協調各派利益訴求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但是,缺乏剛性的制度保證,卻使得各派力量之間的協商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難以在當前社會經濟大發展和大轉型的過程中,提供可靠的預期。
無論是“反他信”陣營,還是“挺他信”陣營,都在修憲過程中有意無意忽略了民主協商的制度建設。國家發展道路上保守派與改革派的對立,使得雙方都希望“贏家通吃”,而不是在根本利益問題上被迫做出妥協和讓步。這就使得反對派很難通過體制內的渠道與執政派進行有效磋商,如果要滿足訴求,唯有通過體制外的方式進行暴力或非暴力的政治斗爭。泰國能否實現政治和解,所有人都缺乏信心。長達8年的政治亂局并不是一場選舉能平息的,如果“利益—權力—制度”結構關系中存在的問題無法得到有效化解,那么新一輪的政治沖突將無可避免!
(摘自《南風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