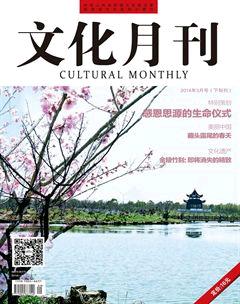藏頭露尾的春天
齊東



從南方回到北京,最大的感受便是春天的姍姍來遲。南方已是春意漸濃,而北京卻仍然春寒料峭。走在路上,突然發現樹上的枝芽都已長出來了,特別是院子里的一排柳樹,遠遠地望去,有一種朦朧的綠色,真是像那首唐詩里說的“草色遙看近卻無”。這種初生的綠色,是一種似有若無的綠,隱藏在一片枯黃中,非要遠望而不可近觀。嫩芽似乎還沒有從冬眠中完全蘇醒過來,只是探探頭,試探一下外面的溫度,稍稍感覺寒冷便又縮回頭去。因此這綠也就不明顯,仿佛還在等待著什么。詩人韓愈的觀察真是到位,換了我,啰嗦半天也說不清這種初生的綠意。但這就是北方春天的景象,雖春意萌發,卻乍暖還寒。
已到了清明時節,走在外面,風變得不是那么刺骨了,雖然還有些涼意,但涼意中隱隱地有了一些暖意,涼雖涼卻不是那么地冷了。
每當春風拂過,傳來一陣陣清脆的鳥鳴聲,三兩根線,數十只鳥,構成了一幅春日的剪影。黑白相間,勝過萬紫千紅;簡單顏色,不懼五彩繽紛,大自然的隨意勾勒,便勝卻人間無數。小鳥飛翔時的優雅自得,駐足時的左顧右盼,猶如一頁樂譜當空展示,每只鳥便是一個音符,撲面而來的便是一曲悠揚的春之聲。不用看大地吐綠,不用聽蟬鳴蛙叫,單是小鳥們的交頭結耳、竊竊私語,以及晚來者的振翅晙睨,就如一首優美的詩、一幅鮮明的畫展現在眼前,配之一曲輕聲合唱,悠揚而清亮。
在我的心目中,小鳥是自由的象征,每每看著小鳥在天空中自由地飛翔,都會讓人對自己雖然可以“坐地日行八萬里”,但卻無法扶搖直上而自慚。鳥的那一份風姿綽約,讓整個天空成了它搔首弄姿的背景。飛翔是歌,駐足是曲,曲終人未散,滿眼都是簡單的黑白兩色,仿佛中國畫的濃墨點點以及不經意間地留白。小鳥有情,那唇齒間的相依,肌膚間的糾纏,那情深意長,即便是枯木,也會澆灌出無限春色。幾根細線,便成了它們的快樂家園,那你爭我的上下翻飛,那鶯歌燕語的卿卿我我,讓人感嘆,幸福其實就是這么簡單——累了,歇歇;煩了,聊聊;痛苦,那就翱翔吧。那一刻,扶搖,一展出水芙蓉的天然風流;收翅,自有風輕柳斜的自在自得。鳥的世界同樣有百轉千回,同樣有眉目傳情,而其風流、韻味則在振翅欲飛中盡顯。
人類喜歡鳥類,還因為它的鳴叫宛轉清幽、抑揚頓挫,作為大自然奇妙音響的一部分,成為人們生活中的天籟之音。鴉鵲無聲,并非人們所希望的自然狀態,呈現出的是壓抑、是強制、更是了無生命。真正的寧靜,得益于萬物的輕輕自語,而非噤聲吶言。古人更明白其中的道理,“蟬噪林愈靜,鳥鳴山更幽”,只有人類閉上自己的聒噪不休,這個世界才會幽靜深遠。
北京是很難感受到春天的腳步的,它不是那種大踏步地向我們走來的,不是那種人未進門,聲音早已傳過來的北方性格,相反倒有些小家碧玉的羞澀,似乎有些羞于見人似的,總是輕搖蓮步,在人們不知不覺中,感受到春天的臨近。北京的春天,總是讓人不知不覺。
北京的春天通常都是很短的,常常是剛剛感覺出春意,接著便迅速進入了盛夏,幾乎不給人以思考的時間,不給人以享受的時間。所以北京人是不怎么談春天的,女孩子們也很少置辦春裝,北京人更多地是談秋天,談秋高氣爽,談霜葉紅于二月花等等。俗話說一年之計在于春,可北京人似乎并未把它當回事。我想這是有原因的,原本春天應該是充滿詩意的季節,就如古詩古詞中就頗多描寫江南的春意,但描寫北方春天的詩詞卻很少見,看來北京的春天沒有詩意,因為人們甚至還沒有感受到春意的盎然時,春天就悄悄地消失了。仿佛一個許久未見的老朋友,打了照面,未及說話便轉身離去,讓人怔怔地盯著它的背影,在記憶中翻箱倒柜,他到底是誰?來干嘛來了?
人們不愿談春天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北京的沙塵多發生在春天。經過一冬干燥氣候的洗禮,北方的大地早已干透。近些年以來,冬天下雪已成了難得的一件事,更為春天沙塵的肆起埋下了伏筆。我記得小的時候,北京的雪特別大,那時候印象特別深的是,馬路兩邊整個冬天都堆滿了黑白分明的雪,一層一層地堆在那里,舊雪沒有化,新的雪又覆蓋了上去,只是令人奇怪的是,盡管那時雪下得不少,但那時每到春天,沙塵天一點兒也不比現在少,甚至還要多。那時候的北京大街上,婦女們甭管大姑娘小媳婦,常見裝束便是頭上裹著沙巾,五顏六色的,頭埋在里面,看不出個俊丑。如今雖然雪少了,但沙塵卻未相應地增加,我想這應該得益于北京周邊的綠化做得足夠好,盡管雨水并不充沛,雪下得并不如過去多,但沙塵暴發生的次數卻少于過去,讓我們肆意享受這藏頭露尾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