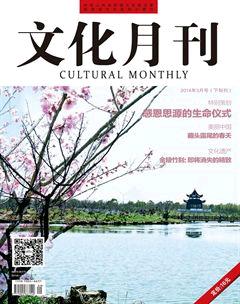嵇康的兩封絕交書
李修建

嵇康一生寫過兩封絕交書。
第一封是寫給山濤的。嵇康與山濤曾經關系密切,二人連同阮籍、王戎、劉伶、向秀、阮咸,曾在山陽縣的茂林修竹中,圍坐一起,忘卻世事,酣暢飲酒。后人稱他們為“竹林七賢”。
七賢之中,山濤年齡最大,城府最深,練達人情,洞明世機。在血雨腥風的魏晉嬗代之際,山濤投奔了司馬氏,依靠高明的政治才能和處事智慧,坐到了高位。比山濤小近20歲的嵇康,顯然缺乏亦不屑于這種與世沉浮的生存能力,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時代里,他固執地堅守著自我。這種堅守,最終導致了他的人生悲劇。
無論從哪方面看,嵇康都是個無比驚艷的人。他身形偉麗,風姿瀟灑,到深山采藥,被樵夫驚為仙人下凡。他是文學家,詩文俱佳,尤擅四言,風格清峻。他工于書畫,草書被唐人視為精品。他精通玄理,富有建樹,所作《聲無哀樂論》和《養生論》,成為清談重要話題。他是音樂家,一曲《廣陵散》,感天動地。他還是一位工藝大師,喜歡掄錘鍛造。他實在是太過出眾了,雖然只做到了中散大夫,雖然長期隱居,卻難掩他成為一代名士。于是,在拉攏不成的情況下,他成為司馬政權的重點盯防對象。
嵇康不是阮籍,他不會茍且于世。他是曹魏的姻親,娶了曹操的曾孫女。毋庸諱言,他是心系曹魏的。或者說,他心系兩漢以來形成的穩定的儒家社會。在那樣的社會里,禮法出于人情,上下井然有序,士人可以一展抱負。魏晉之際絕非如此,那些叫囂禮法的,做的卻是最毀棄禮法的勾當。于是,他懷著滿腔抑郁與憤懣,轉向老莊,追尋自然與自我,希冀在琴詩藥酒的世界中得到解脫。然而,孤峭不群的嵇康,無法做一個自在的隱士,如他詩中描述那般:“采薇山阿,散發巖岫。永嘯長吟,頤形養壽。”他胸中涌動的郁郁不平之氣,難以阻扼,終究以一種激進而奇特的方式,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迸射了出來。
山濤的本意,是想關照昔日的兄弟。在謀得更高官位之后,他任職的吏部郎空缺下來,這是一個主管人事的肥差。他想到了靠種菜和打鐵貼補家用的嵇康。始料未及的是,嵇康非但沒有領他的情,還寫下了一封絕交書。很快,山濤應該對自己未免魯莽的舉動深感后悔和自責。他并不責怪絕交書讓他顏面掃地,他自責的是,這封絕交書間接導致了嵇康的死亡。
在這封長達1700余言的書信中,嵇康表白了他的生活方式、處事態度和人生追求。他提到,自己天性疏懶,常常一個多月不洗頭臉,又受老莊影響,任情恣曠,喜歡做個無羈散漫的人。他剖析了自己與世俗禮法的格格不入之處,指出自己有“必不堪者七”,諸如喜歡晚起;喜歡獨自垂釣行吟;身上虱子很多,喜歡把搔;不喜吊喪;不喜寫信;不喜與俗人交接等。一旦穿上官服,進入官場,便要遵守各種條條框框,讓他不堪忍受。更重要的,是他的“甚不可者二”:一是“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二是“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而發”。對待湯武周孔的態度,使他與朝廷所奉行的儒家意識形態形成尖銳對立,定然為司馬政權所不容。而他嫉惡如仇的性情,使他寫下了第二封絕交書,并直接引發了他的死亡。
嵇康最好的朋友,名叫呂安,不在七賢之列。呂安思念嵇康時,即使遠隔千里,也要駕車前往拜會。于此有了一個成語“千里命駕”,意指朋友之間的篤深感情。其實,嵇康先認識的是呂安的哥哥呂巽,并且將他許為至交。不過,嵇康“好善暗人”,看走了眼。
因為一個荒唐的事件,嵇康卷入了呂安兄弟的糾紛中。事情是這樣的,呂巽垂涎弟媳的美色,將其迷奸。呂安氣憤不已,意欲告官,將這件事告知了嵇康。呂巽亦央求嵇康從中調停。嵇康念及他們兄弟之情,門第之譽,好言勸告呂安平息此事。呂安聽從了好友的慰解。呂巽亦信誓旦旦地向嵇康保證好好做人。孰料呂巽的誓言是假,他做賊心虛,反誣呂安“不孝”。漢代以來推崇儒學,以孝治天下。“不孝”是個很大的罪名,曹操曾以“不孝”之罪殺掉了孔融。呂安被逮入獄。熟悉內情的嵇康悲憤莫名,寫出了《與呂長悌絕交書》。“悵然失圖,復何言哉”,這封絕交書只有300字。嵇康以冷靜悲涼的筆調,簡單回顧了與呂巽的交往,表達了自己辜負呂安的歉意,被呂巽所負的失望與憤慨。
嵇康挺身而出,為呂安辯誣。恰如曹操之殺孔融,并非一時興起。肆言高論的嵇康素為司馬氏所不滿,呂安一案正為除去嵇康提供了借口。因交好籠絡嵇康不成而銜恨的鐘會,抓住這個機會,慫恿晉文王司馬昭殺掉嵇康。
于是,嵇康入獄了。公元262(一說263)年,嵇康被處決于洛陽,時年39歲。臨刑之前,嵇康神氣不變,要來一張琴,彈了一曲《廣陵散》,曲終嘆曰:“《廣陵散》于今絕矣!”
嵇康之死,對他個人而言,或許有點諷刺意味。他信奉養生之道,認為神仙雖不可學,但通過服食藥物,可以益壽延年。持此觀點,他積極地尋道問藥,“采藥鐘山隅,服食改姿容”。或許是受到親戚何晏的影響,他服用五石散。然而,他從來沒有“俯仰自得,游心太玄”。他有養生理論,卻無保身之術。
嵇康已逝,從此歷史上有了一位孤懸蒼穹的文化英雄。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