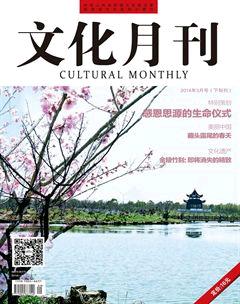文化局長談文化
當前,奉賢正處于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已經到了由蓄勢待發向快速崛起轉變的重要關口。在奉賢區的戰略部署中,文化建設對進一步推進新型城市化,加快城鄉一體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亦對促進全區經濟社會全面協調發展起著積極作用。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應當辦好今年的第三屆文化藝術節,充分展示我區近幾年來的文化發展成果和人民的精神風貌,發揮好文化推進我區“文化名人”、“文化名品”、“文化名城”的建設作用,辦成一屆市民參與、群眾叫好的文化盛會。
——上海市奉賢區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局長金擁軍
《文化月刊》:上海市奉賢區是舉辦文化節的先行者,奉賢區文化節現已有十多年的歷史,請您介紹一下奉賢區文化節最初的創辦理念和奉賢的文化底蘊。
金擁軍:我們當初的理念是一屆政府辦一屆文化節。自2001年奉賢區建區以來,已成功舉辦兩屆。奉賢擁有深厚的文化傳統,“奉賢”這個名字就有一定的含義。奉賢大概在雍正四年建縣,2400多年前,孔子弟子言偃,這個72賢人當中唯一的江南弟子到奉賢講學,為未開化的奉賢帶來了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他教授的勞動和禮儀,使得奉賢的文明程度不斷增加,形成了“敬賢”、“學閑”氛圍。自此,奉賢的歷史文化底蘊和人文環境都帶有和諧、謙虛、上進的特征。如何做好奉賢文化藝術節是我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今年,我們在創建上海市文明城區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共識,就是奉賢各方面的工作推進要保持在“敬奉賢人、見賢思齊”的精神狀態上。這就是我們提出的“賢文化”,也是奉賢的核心價值觀。奉賢區第三屆文化藝術節也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籌建的。
《文化月刊》:本屆文化節和往屆相比,有哪些傳統的延續?又有哪些創新之處?
金擁軍:奉賢區深厚的群眾文化底蘊、積淀,使得她擁有不少優秀的群眾文化創作作品,尤以小戲、小品為最。舞蹈、音樂等方面全面穩步發展,整個奉賢在文化建設的基礎工作層面不斷努力。多年來,每屆政府舉辦文化節,都是嚴格執行中央、市政府的要求,同時結合奉賢的地方特色去做。今年的三中全會,特別是十七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關于文化建設的要求,使我們的文化工作在一種新的背景下去做,我們也不斷思考在不與之前雷同的基礎上,如何反映奉賢特色。本屆藝術節主要是通過活動機制上的創新,來達到吸引更多社會力量參與的目的。
《文化月刊》:那么,本屆藝術節的機制創新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金擁軍:辦活動政府不可能大包大攬,吸引社會力量參與也同樣重要。因此,活動想法、創意只是創新的一個方面,市場運作上的創新才是關鍵。我們現在文化藝術節涉及四個方面的內容,分別是:主題活動、重點活動、系列活動和原來的品牌活動。活動很多,單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夠的,因此,政府會出臺一些激勵政策,提供一定的補貼,由企業、協會等社會組織承辦。
如今,這種購買服務機制的運用已經帶來了較好的效果。比如,我們有一個全國性的學生書法評比活動就是各個方面共同構建完成的。市書法家協會搭建平臺,區書法家協會來承辦,然后企業來出資。再有就是浙商文化在奉賢比較發達,那么我們就發動這些企業,通過冠名的方式運作我們的文化活動。從前,文化活動只有政府的一紙公文,群眾的參與熱情度不高,效果不好,而企業參與這種形式會更好地帶動群眾的積極性,也讓活動更豐富。
《文化月刊》:這次文化節整個經費情況如何?在經費分配方面,市場的創新機制是否起到了積極作用?
金擁軍:整個文化藝術節的籌辦大概需要600萬元左右,政府撥款300萬元左右,那剩下來的錢哪里來?“群文四季歌”一年的運作費用也要100多萬元,政府撥款45萬元。所以我們就只能依靠我們市場的創新機制和以往豐富的經驗來搭建平臺,辦好活動。
《文化月刊》:縱觀本屆藝術節的節目表,活動項目安排緊湊、類別內容廣泛豐富,這是否和奉賢區良好的公共文化設施發展有關?請您結合實際,為讀者介紹一下。
金擁軍:本屆活動的整體安排,重頭戲不是放在具體樣式上,而是致力于怎樣讓活動更加貼近百姓,讓更多的老百姓來參與。我們開幕式不主張大操大辦,藝術節是大眾的節日、文化的盛會。近年來,上海市一直在打造現代公共文化體系。主要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各級政府對公共文化建設的重視;二是體現在我們城鄉覆蓋的工作機制體制;第三在基礎設施建設上也實現了城鄉統籌整體發展,從而建立區鎮村三級的公共文化設施網絡。上海市通過區劃調整,鄉村合并由原來的22個鎮整合成8個鎮,每個鎮、街道都有自己的標準化社區文化中心,功能齊全、設施完善,便于百姓活動參與。
《文化月刊》:現在每個鎮的社區文化中心等基礎設施利用得怎么樣?
金擁軍:現今,所有社區文化中心都是全負荷滿載運行,活動相當豐滿。原本有的地方人氣不足、活動不夠,而區文化藝術節的舉辦便很好地帶動了各個鎮的文化氛圍,豐富了活動內容,讓活動中心更好地發揮了效應。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建立了一套文化配送機制,引起了整個上海地區的重視。首先是區鎮自身的資源充沛,奉賢全區活躍在社區街道里的306支文化團隊,積極參與社區文化活動中心活動才使得整個活動中心滿載運行;第二是區文廣局不斷加強基層工作的指導和考核;第三是不斷開展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就如本次藝術節,其不斷帶動著奉賢的文化氛圍,扎扎實實服務百姓,潤物細無聲。
《文化月刊》:社區文化活動中心在運行上是否遇到過困難?
金擁軍:社區文化中心在建成運行上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們科室的相關工作人員都會定期到各個鎮的活動中心了解情況。一是資源不夠,二是運營時間上和百姓也有沖突。工作日是大多數人上班的時間,而這些人本身的文化修養比較高,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高。雙休日期間活動中心是不開放的,這是鄉鎮經費短缺造成的。為了豐富百姓的周末生活,讓百姓有地方進行文娛活動,我們集中精力做到區級公共文化設施全年開放。我們利用這次的藝術節也把社區文化中心的活動內容豐富起來,從而讓社區文化長效發展。
《文化月刊》:奉賢區的品牌文化活動有哪些?
金擁軍:如這次的系列活動之一“群眾文化四季歌”就是奉賢的品牌活動之一。它是結合一年四個季節開展相對應的演出,分別是“春之聲——巡回下鄉演出”、“相約濱海之夏——廣場文化活動”、“濱海秋韻——高雅藝術進奉賢”、“冬日暖陽——文化拜年”。這個活動雖然沒有成功申報國家公共文化服務示范項目,但是已經成功申報了市一級的公共文化服務示范項目。更重要的是,她真正走進了群眾,受到市民歡迎,這是我們更看重的。
《文化月刊》:奉賢區的整個文化活動在活動設計方面有什么考慮?
金擁軍:我們會在活動設計上適當加入一些市場化的活動,大致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像春節、元宵節這樣的傳統節慶活動。這部分政府參與的還相對多一點。第二部分是基本走市場的活動。就如“梅花節”、“菜花節”(菜花節被列為全國十大看油菜花的重點節日)、“牡丹節”、“桃花節”等春天的節慶活動。第三類是完全市場化的活動,就如在奉賢的海灣“碧海金沙”舉辦的品牌音樂類活動。最重要的是這些國際化、時尚化的音樂節雖然是完全市場化運作,卻不會把資金的壓力轉向觀眾,票價親民。
《文化月刊》:以往的藝術節中有暴露出來的問題嗎?現在是否已找到解決方法?
金擁軍:活動還是需要注重品牌化、系列化。通過多方關注,打造活動品牌,我們有很多活動都是一直在做,已經成功舉辦多屆,影響力逐步擴大,吸引了更多的百姓來參與我們的活動。從而達到我們的最終目的——更好地服務老百姓。
但是,奉賢區在上海各行政區里面綜合實力比較弱,經濟實力屬于中下水平,所以我們各方面投入,包括人才方面都不是很足。也就是說,我們有想法、有熱情,但是層次還是不夠。所以,我們還是要不斷去改造、創新,把活動的各方面都搞得更好一點。藝術節五年舉辦一次雖然很少,但是維持長效機制很重要。除了藝術節之外,我們原來的活動機制也要維系,要做到沒有藝術節,我們也照樣有活動可以轟轟烈烈地舉行。
《文化月刊》:在組織工作上,譬如安保等問題,在活動中是否都有所考慮?
金擁軍:我們希望參與的老百姓越多越好,又不會形成擁擠的局面。這次集中的展示活動,閉幕式可能會做得稍大一些,這個時候可能安保要上去。但一般的常態化活動,是有一定組織的。這個組織不是政治化的,而是菜單化的。全區306個文化團隊,有的鎮特別多,比如南橋鎮就有100多個團隊。你若想進這些團隊,可以經過組織申報,同時,我們在一個月30天時間中,也會協調好所有團隊,解決時間上的沖突,充分利用整個活動中的時段,設施。這樣就可以把每個活動有序安排下去。
《文化月刊》:縱觀全國,現在一些地方、社區的很多活動受眾面都比較窄,奉賢區在策劃這些活動時如何平衡受眾年齡?上海市是外來務工人員較多的城市,這些外來人員是否享受到我們的文化服務?
金擁軍:不可否認的是,老年人亦是我們基礎文化設施里的主要參與者之一,所以,現在辦活動也是以老年人為主。為平衡這一現象,我們請了諸多體制內的團體,面向不同階層、年齡段的受眾多多開展活動,也舉辦了如“藝術之星”這樣的比賽,用以吸引社會上的青年們參加。今年是“藝術之星”的第九屆,只要你有一技之長就可以參與進來。我們會利用廣播、電視等媒介進行宣傳,并和“中國好聲音”等當紅節目合作,吸引更多的群眾參與。在外來人員享受文化服務這一方面,在我們奉賢的圖書館、文化館等文化中心,你只要出示身份證,就可以免費享受到諸多活動。基于以上這些考慮,我們各類群體,小學生、大學生、農民工以及一些企業都有各自的風采展示月。
《文化月刊》:在文化市場管理方面,有些經營場所是要收費的,這方面奉賢的管理如何?
金擁軍:整個奉賢文化的場所有將近500家左右,包括網吧、茶座、KTV等。我們在管理上建立了一個機制,叫文化市場三級聯動工作機制,就是由我們的專職管理員、社會監督員,再加上文化工作志愿者這三支隊伍組成的管理隊伍。每個月我們會召集他們去巡查,宣傳等。對于做得好的志愿者,我們會提供獎勵,這一政策實施后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除了我們文化部門,還有公安、工商,這些部門聯動一起來管理。其次,我們建立了一個平臺,把這500家經營者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叫文化經營者聯合會的組織。同時,建立了工會,把經營者按不同門類分成各個小組,如網吧小組,KTV小組……聯合會成立后,每個季度會召開理事會,讓民間組織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協商小糾紛,有了這么一個平臺,總體管理就很規范了。
《文化月刊》:您如何看待文化產業化?
金擁軍:這是一個大概念,城市發展中靈魂的東西就是文化,文化中除了精神層面的核心東西以外,產業發展、文化發展也是一個重要部分,一方面是經濟價值,一方面是社會精神價值,特別是我們講到的,奉賢區也在推動新城建設。想要使一個城市變得有魅力,就必須注入文化的東西,使之變成代表一個城市產業發展的東西。比如說書城的建設,不是單單為了賣書。還有就是創意性產業的東西,有時候也能帶來人氣.。這方面我們都在思考,都在與時俱進。奉賢有很好的生態優勢,政府在公共文化設施建設中也會考慮到其臨海的環境,人造沙灘和上海最大的森林公園都在奉賢,在森林公園中還建有不同的主題博物館。
《文化月刊》:在文化創意方面,奉賢有什么想法?
金擁軍:文化產業發展最重要的核心就是創意,整個文化創意的發展就全世界來說遇到新的挑戰,但奉賢在這方面還有發展空間。文化產業是要講效益的,而目前大家都在講概念。文化創意產業門類很多,創意這個方面一定要有自己核心的、能復制的東西。以萬達為例,每一個萬達廣場里面的結構都是不一樣的,而他正好抓住了創意的三個方面,世界前沿、中國特色、地方本土化的東西,從而做到,大方面一樣但又有特色,奉賢也同樣要抓住這三點。
《文化月刊》:奉賢區在文化遺產保護上做了哪些努力?
金擁軍:奉賢區的文化遺產保護分為兩個方面。首先是文物方面,奉賢歷史不是很長,因此文物不是很多。擁有“華亭古石塘”等市級文物。奉賢水系發達,橋很多,不可移動的保護點有211處。盡管奉賢歷史不長,但是其開化和文明程度很高,現有非遺項目18個,國家級項目2個,省市級項目13個。這些項目都是跟原來百姓生活生產息息相關的,有記憶類的,也有文化民俗。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有一個暖場活動——“滾燈”,就是用竹片做成的球,男子在地上雜耍,舞蹈,后來又發展出了女子滾燈。其次就是上海吳越一帶的地方戲,地方戲的源頭就是民間的傳唱,山歌中有一段“吳歌”也是非遺中的一項。這些項目在今年奉賢區第三屆文化藝術節上都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