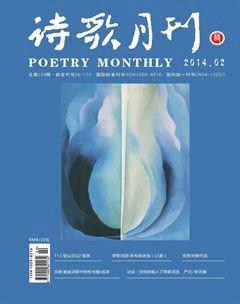莎朗·奧茲詩歌中的性與愛
遠洋,生于1962年,河南新縣人。1995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深圳市作協理事。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200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有詩、譯作見刊于報刊,著有詩集《空心村》。獲河南省“駿馬獎”、“牡丹杯”獎,湖北省“神州杯”獎,深圳青年文學獎、河南詩人年度大獎等。
今年4月15日,2013年普利策獎在哥倫比亞大學公布獲獎名單。7l歲高齡的女詩人莎朗·奧茲(Sharon 01ds)憑借詩集《雄鹿的跳躍》(Stags Leap)摘得普利策詩歌獎。莎朗·奧茲1942年出生于舊金山,在斯坦福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接受教育。她的第一本書《撒旦說》(1980年),獲得了首屆舊金山詩歌中心獎。她的第二部詩集《死人和活人》,入選1983年拉蒙特詩選,贏得國家圖書批評家獎。《父親》入圍英國T·S·艾略特獎,《未打掃的房間》入圍國家圖書獎和國家圖書批評家獎。奧茲在紐約大學教授研究生創意寫作課程,是紐約大學為金水醫院醫生和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退伍軍人創辦的寫作工作坊創始人之一。
在當代美國詩歌界,莎朗·奧茲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詩人。盡管她的詩集銷量不錯,很受讀者歡迎,人氣較高,但長期以來,她幾乎被批評家眾口一詞地指責自戀和膚淺。肯·塔克在《紐約時報》書評里斷言,“對于一個作家,她最好的詩表示出強烈的觀察的力量,奧茲花費太多時間捕捉自己的情緒溫度,”贊揚者如史蒂夫·哥維,強調奧茲“已經成為美國詩歌里的一個中心存在,她的敘述和戲劇性的力量以及她的作品的意象派的派頭,為她在廣大公眾里仍然讀詩的小部分當中贏得了大批追隨者。”而詩集《雄鹿的跳躍》先后獲得久負盛名的英國T·S·艾略特獎和2013年度美國普利策詩歌獎,使她的聲譽如日中天。
一、驚世駭俗而出奇制勝
伊麗莎白·加夫尼稱贊奧茲是“勇敢的”,他指出,“出自個人性的揭示,她創作包含普遍真理、性、死亡、恐懼和愛的詩歌。她的詩有時不和諧的,意想不到的,大膽的,但總是愛和深深的回報。”《詩閃光》評論家理查德·瑟爾伯格贊揚奧茲“呈現以前未寫過或在這些方面不寫的主題……這些詩里最好的詩一行一行地密集著靈感。”請看其短詩《教皇的陰莖》:
它深懸于他的長袍里,一把
精致的鐘錘在吊鐘核心
他動,它也動,一條幽靈似的魚在一片
銀色海藻的光暈中,體毛
搖曳于黑暗和灼熱里——而在夜晚
當他的雙眼閉合時,它便立起
贊美上帝
這樣的詩歌,若在中世紀,可能會被宗教法庭判處死刑;即使在今天,也難免有“褻瀆神圣”之嫌。初讀覺得匪夷所思,為詩人的標新立異而驚愕;再讀令人忍俊不禁,啞然失笑。直寫性器官,卻無色情意味。詩人就像一個調皮而大膽的頑童,掀開道貌岸然的神袍,露出包裹著的赤裸裸的肉體,嘲笑神圣,也戲弄了讀者。這似乎是一場惡作劇,小插曲般戛然而止,卻余音裊裊,余味悠長,把讀者帶入對神與人、靈與肉、世俗與宗教、真與偽的種種對比反思之中。
對于性,問題不在于能否寫,而是如何寫。如果像當代中國曾經出現的“下半身”一樣,僅僅停留在吸引眼球、嘩眾取寵,或者只是宣淫一一欲望的宣泄,甚至污濁不堪,誨淫誨盜,失去了人最起碼的道德底線,那就是詩人和詩歌的墮落;奧茲一系列從肉體出發的詩歌,并沒有停留在性描寫和感官刺激上,卻能從肉體和性的經驗上升到對人與人之間關系、人性和靈魂的追問、探尋與挖掘,有著哲學思辯和社會批判色彩,拓寬和豐富了詩歌美學的疆域。
二、肉體在場而彰顯個性
她的作品被視為繼承了惠特曼頌揚身體的傳統;而且對她來說,身體是一個存在的憑證;肉體經驗是身體接觸和形成主要人際關系的首要模式。詩歌從身體出發,匯聚其所有的快樂和痛苦,所以特別容易引起女性讀者的共鳴。
奧茲寫道:“詩歌更忠實于感覺的現實真實,比任何一種散文更忠實。”在她的沙龍采訪時,奧茲談到她的詩歌宗旨,“我認為我的作品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我不是一個思想家。我不是……我怎樣才能把它放進去?我寫我察覺到的、我推測到的。這不見得簡單,我不認為,但它是關于平常的事物——關于事物、關于人的感覺。我不是一個知識分子。我不是一個抽象的思想家。我對平凡的生活很感興趣,”她補充說,她是“不問一首詩在其口袋中攜帶大量巖石。只是作為一個普通觀察者、生活的人和有感覺的人,讓體驗通過你用鋼筆寫在筆記本上,通過手臂,出自身體,到紙頁上,避免失真。”
我感覺到他的
吻,在蓬亂的胡須中,在因他知
而我知、因他觸及而我見識
的那地方的內部曲線上。從而
被進入,在臀高的桌上,堆滿
成捆毛巾,洗澡和擦手的,
厚絨布的伊甸園,是要在一個人的內部去感覺
一種核心的液體熱度,就像
那個人是地球。
——《贊美詩》
奧利維亞·萊思在《衛報》寫了一篇自相矛盾的評論,宣告“充其量,奧茲唯我論的細讀結下令人驚訝、豐富多汁的語言果實,無人能以如此殷切的精確寫性。在最壞的情況下,她的詩像一個雄辯的自戀者跨行連續的劇情。”
這使我聯想起基督教中的“道成肉身”之說,該教義認為:三位一體中的圣子在降世之前與圣父同體,稱為“道”。后來這個“道”以肉身的形式降世成人,便是耶穌。所以耶穌就是“道成肉身”,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所以他是全知全能,同時也會憐憫、憂慮、饑餓、疼痛。慈愛、憐憫、信實與公義。在道成肉身的主耶穌基督身上,無形的道與具體肉身的統一,靈性與物質的統一,屬天與世界的統一,屬靈生命與行事為人的統一,永恒與歷史的統一,今生與永世的統一。《約翰福音》第1章第1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個“道”是新教的譯法,而公教則譯為“言”;英文是“word”,相當于希臘文“logos邏各斯”。內在的邏各斯就是理性和本質,外在的邏各斯是傳達這種理性和本質的語言。《圣經》里說,上帝有無上的智慧,以言辭創造世界。“道”在《圣經》恢復本翻譯為“話”。詩人如同耶穌,以肉身去感受人世間的磨難,發而為言詞,抒寫苦情,即是詩篇。
三、直面現實而充滿悲憫。
喬爾·布勞威爾在《紐約時報》評論描述奧茲的方法:“奧茲從她的家庭浪漫史中選擇激烈的時刻——通常涉及暴力或性或兩者一一那么它們在相反的方向延伸,在如此著迷的細節中表現它們,以她的親身經歷,它們似乎完全獨特的,而與此同時,使用比喻來強調它們的普遍性。”
我從未見過誰這樣寫吃螃蟹的情景:
十字架,在母乳和肉食之間。背部
甚至呈現一個完美的
毀壞的乳房的形狀,豎起的鱗片
雪白,像肉質的菊花,
看見她在廚房,給肉剝去殼,她的
手臂屈伸——她像一個
魚鷹,野蠻、熟練地撕裂
肉,活出她害怕和想要的生活。
——《螃蟹》
詩人將人類剝奪其他物種生命的殘忍——這血淋淋的場面,呈現在我們眼前。但其中卻飽蘸著母愛親情。冷酷而熱烈,兇殘而慈愛,甜美而辛辣,種種復雜的感覺摻雜攪拌在一起,耐人咀嚼尋味。
詩集《雄鹿的跳躍》以系列詩歌的形式,講述了一個離婚故事,令人驚愕,尖銳而辛酸,包含愛的束縛、性、悲傷、記憶和新的自由。莎朗·奧茲向讀者敞開她的心,以明智而有說服力的講述帶著我們穿越她婚姻終結時的那段時光;分享那種當我們不見愛人的身影時受人忽視的感覺;令人驚訝的身體結合,仍然存在于一對正在分手的夫婦之間;一切都失去了,從丈夫的微笑到他臀部的姿勢。奧茲將這些情形赤裸裸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對于作為她30年的伴侶、如今卻愛上另一個女人的男人,她自信、勇敢,甚至慷慨大方。她在卓越不凡的《雄鹿的跳躍》里寫道:
當任何一個人逃脫,我的心
跳了起來。即使被逃脫的是我
我也廣半站在逃脫者的一邊。
——《雄鹿的跳躍》
個中心態,可謂酸甜苦辣澀五味雜陳,頗為矛盾糾結,但始終不失寬容和優雅。
四、意象抒情而節奏鮮明
奧茲的詩歌繼承了意象派傳統,注重意象和音樂性,并且融入了復雜的敘事技巧和濃郁的抒情色彩。她的詩行總是伴隨著鮮明的節奏、生動的意象,層層推進戲劇性的情節和強烈的情感。大衛·萊維特指出奧茲的“詩歌專注于意象的首要地位,而勝于環繞它的問題,她最好的作品呈現出某種抒情的敏銳,其中是凈化,也是救贖。”
在《我兒子的父親的微笑》一詩中,她這樣描寫嘴唇:“他的嘴唇之薄賦予/它一種單純,像兒童畫的/一個微笑——人行天橋,翻轉過來,或見到/在橋下,在水里——和那射手的/弓呈現出一種彎曲、無偏差的/對稱,一箭穿心。”她的意象之奇妙,聯想出乎意外,涵義雋永,引人深思。如唐司空圖《詩品》中說,“超以象外,得其環中”,仿佛“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撲朔迷離之際,又豁然開朗,恍有所悟。
《雄鹿的跳躍》中借某張加州葡萄酒標簽畫里的一只雄鹿來比喻離異的丈夫,非常貼切,形象有些滑稽可笑,但靈活現,給人的印象鮮明強烈而非常深刻。將花心男人與騷情的雄鹿相提并論,不無嘲諷之意、幽默之感。詩中雄鹿跳躍,為追逐異性縱身飛騰,跨崖越欄,急迫而又倉促;間或駐足佇立,回首返顧,似乎舊情難忘;偶爾躊躇不前,踢踏四蹄,惆悵而迷惘。其節奏明快,疾轉回旋,時而高亢激昂,時而低抑頓挫,如一首騰挪迭蕩的小步舞曲。
艾略特獎頒獎時,最終評審團主席卡羅爾·安·達菲評價詩集《雄鹿的跳躍》說:“這是她的成功之書。在她的悲痛里有一種風度和騎士精神,標志著她成為一個世界級的詩人。我總是說,詩歌是人類的音樂,在這本書中,她真的在歌唱。她從悲痛到恢復的旅程是如此美好的踐行。”奧茲極具推進力的詩行和她富有魔力的意象是如此的充滿活力,并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音域一一有時急速迅猛,有時陷入深沉的冥想。她的嚴峻既貼近痛苦又通往愛情,創作出她已贈與我們的出色的、最強有力的詩歌。
201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