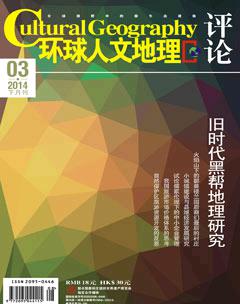美國的原子彈不如關老爺的大刀
宋強
人杰惟追古解良,士民爭拜漢云長。
桃園一日兄和弟,俎豆千秋帝與王。
氣挾風雪無敵匹,志垂日月有光芒。
至今廟貌盈天下,古木寒鴉幾夕陽。
去年我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編輯一部奇特的小說《將軍望》。“望”,乃旗幡之意,臺州地區在近代史上出過很多將軍,僅國軍將官就有70多位。往往是某個家族出了一位將官,宗族就要撥一筆錢修一座將軍第,門口豎起一根旗桿,升起將軍望,讓半個黃巖都能看到。這是浙江籍作家鄭九蟬先生的嘔心瀝血之作,是一部類似于《亮劍》但更具有悲劇色彩的小說,講述了浙江臺州大山中關羽后裔的從軍史和人生沉浮史,時間跨度從清末到20世紀90年代初,地理跨越廣州黃埔、蔣閻大戰的隴海戰場、武漢會戰時期的“大武漢”、臺兒莊、印緬戰區、遼沈戰場……盡管作品具有這么多的元素,但是決不是有的作家寫“大歷史”那樣,歷史與真實事件純是空乏浮薄的“組裝”。主人公的脆弱、好色、天真無邪,與他在戰場上的孔武一樣,都顯得那么真實,又讓人感到心悸。耐人尋味的是,在眾多的將軍之中,唯獨關羽的后代拒絕了國府撥款修將軍望的盛情。小說的結尾沒有讓這個國軍中將很有尊嚴地去死,而是讓這個老頭歷盡了家庭財產分割風波之后,窩窩囊囊地死于二女兒的亂用藥。小說充滿宿命、詛咒、無力空洞和戲弄,像《東山》,也有些像《靜靜的頓河》。
這一部小說不太“亮”,但仍然讓當地的政府和商會感奮,準備投巨資拍成電視連續劇。我疑心此舉的目的,除了弘揚地方文化之外,似還有將“關公文化”的香火延到本地的用意。小說用調侃的口氣說:先祖關羽在三國時期也就是一個部級官員,自古以來部級干部被歷代帝王封為“帝”的,除了他還有別人否?小說敘述道:關家在河南信陽的一支,不知什么原因,要在清朝末年舉族遷往遍地蛇豸的浙南山區。他們忍著饑褐,攀越過高高的麻貍嶺,蛇咬蟲叮也不能阻止他們的腳步。作者留下了這樣一個懸疑:既然關家是望族,是什么原因讓他們背井離鄉?
而這部小說留下的最大懸疑是:主人公被公認為關家的驕傲,也是立志要成為現代中國的第一代“五虎上將”。然而他的行狀、心理卻與祖上大相徑庭,作者為什么要這樣描繪關羽之后?他在軍隊中是一名杰出的指揮官,然而一直為他所信奉的一切感到痛苦、猶疑。更要命的是,他在骨子里居然是一名和平主義者和左傾的反戰論者。一個日本小孩自殺前惡毒的眼神居然會讓他后半生患上強迫癥。還有一宗不堪處:他的半生都為勃勃的色欲所煩惱,然而這種色欲會惡毒地懲罰他,讓他丟盡顏面……
這個關家之后,哪有先祖的影子?然而這個關某人,卻讓我感到他就呼吸在我的咫尺——我從小就懷疑,像關羽這樣地活著就像個神的人是否在現實中存在過。從連環畫頁、從廟宇中的雕像、從戲臺子上的那個背上插滿旗子的偶像,我只看到一個動作僵硬的類人神(包括戲文家和畫家刻意設計的讓關公更“親民化”的捋髯須的動作,看上去都是那樣程式化)。但是這種念頭一冒出來的時候,我會及時調整我的思緒,莫非是我的情感過于卑劣,所以對英雄的高貴之處不能領悟?我曾經跟一個當過兵的兄長談過這種疑慮,他告訴我,也許你確實不能領悟,你沒有出操行軍的經歷,你可能覺得我一絲不茍的舉動值得尊敬,但是不可親近。
這也很正常。
拿這個當兵的話審視鄭九蟬的這部小說,我想,我之所以對這部書感到親近。無他,寫字的人彼此經驗相近,這也正常。也許是因為它具備了眾多的取院于現代讀者的元素,過度豐富的信息,過多的奇詭的情節,讓人感到筋骨發痛的張力……
任何一個試圖描繪“走下神壇的關羽”的努力,在能量強大的歷史演變進程面前都是脆弱的。
任何一種敘事都無法復原什么。某種意義上,最杰出的敘事往往是再建一種新的懸空感,提供新的疑慮。
周作人在《秉燭后談》中寫道:
東坡時已說三國,固是很好的考證資料,但我所覺得有意思的還在別一件事,即是愛護劉皇叔的心理那時已如此普遍,這與關羽的被尊重是很有關系的。那時所講的內容如何,現在已無可考,我們只看元至治刊本新全相三國志平話,可以知道故事總是幼稚得很,一點都看不出五虎將怎樣的了不得,可是有一件奇事,全相中所畫人物身邊都寫姓名,就是劉皇叔也只能叫聲玄德,唯獨關羽去I嘟題日關公,似乎在六百年前便已有點神圣化了,這個理由很不容易了解。至治本平話不必說了,便是弘治年三國志通俗演義以至毛聲山評本,里邊講的關羽言行都別無什么大過人處,至多也不過是好漢或義士罷了。無論怎么看沒有成神的資格,雖然去當義和團等會黨的祖師自然盡夠……是桃園結義的影響,如劉關張之尚義氣而結合,他們也會集了來營商業或練武技耳。關羽正民間所受英雄的崇拜我們可以了解,若神明的頂禮則事甚離奇,在三國演義的書本或演辭中都找不出些許理由來,我所覺得奇怪的就是這一件事。
關公崇拜的發生,也是一種疑竇叢生的歷史進程。可以說,它是中國民間文化的最大的“疑冢”,周杰倫的歌詞這樣寫道:我送你離開千里之外你無聲黑白。
關羽崇拜經歷過怎樣的過程才變成后來的樣子,這是考證家的事情。至于關羽為什么承載了這么多的使命,警察也來膜拜,黑道也來供奉;僧家也來升座,道家也來上香,更加有趣的事,生平中不愛跟錢財金帛粘粘乎乎的關羽居然也是財神的代表,這究竟該從歷史本原性去解讀還是從人們的當下性需要探幽?兩者恐怕都不能偏廢一方。
臺灣宗龍飛先生在《民俗藝術探源》中的解釋是:
在傳說中,關公生前帶過兵,從事過兵站事務,長于數算,曾設簿籍法,發明日清簿。又因為他講信用和重義氣,故為商家所崇祀。商人如果能講信用和義氣,自然生意會一天天發達,所以一般商家皆以關公為他們的守護神,同時還被視為招財進寶的財神爺。從前北平畫店賣的財神畫像,中間是關公,左右兩個是文武財神,前頭還擱著一個堆積如山的聚寶盆,可見關公這位財神,還是眾財神中的頭號財神,他的地位在人們心目中可能高過其他財神。
這即是所謂考據家的探幽。一個不容忽視的歷史事實是,關公是山西人,山西的商人以崇拜關公為榮,晉商的隆昌,難道沒有歷史淵源中一根隱秘的線?
加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各地各種名目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活動,此起彼伏,各種名目的“文化”便應運而生。關羽故鄉運城憑借關羽故鄉的常平關帝祖廟、解州關帝廟獨有優勢,游說上下,熱切呼喚推介關羽為文化品牌。這就是現實需要催生“文化品牌”的絕妙例證。
在市場經濟的今天,也需要這樣的精神原子彈。難怪毛澤東對印度總理尼赫魯說,美國的原子彈不如關老爺的大刀,關老爺的大刀能成千上萬殺人,我們不怕原子彈,我們有關老爺的大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