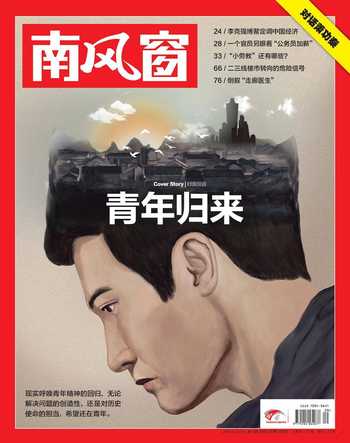新新青年下基層
李克誠
盡管預料到可能會遇到一些挫折,可找工作過程的曲折還是超出了沈之嘉的想象。一年前,她投出了30多份求職信,絕大多數都石沉大海。可能是因為她的求職意向太不尋常了。沈之嘉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但她投簡歷的對象清一色是蘇南一帶的職業技術學校。
總算有一家位于南京郊區的技校通知她面試。她精心準備了PPT等授課課件,自我感覺試講及隨后的答辯也很成功。最后,面試官瞟了她一眼,問道:“你有教師資格證嗎?”沈之嘉搖了搖頭。面試官反問她:“如果你沒有駕照,能在高速上開車嗎?”語氣客氣但異常堅決:學校無法錄用她。
“他們拒絕我,可能是覺得一個清華的研究生來技校當老師這種事太離奇,會想這個人是不是不太靠譜啊。”沈之嘉回憶說。但她仍沒有放棄,她打電話給投過簡歷的另一家南京的職校,接電話的老師聽了她的自我介紹后很重視,稱將向校長匯報此事。幾天后,沈乘坐高鐵到南京參加這所學校的面試。
校長親自擔任面試官。沈之嘉回憶說,校長盯著她看了足足有兩分鐘,那眼神充滿著懷疑,仿佛是想問,你不會是為了騙一個南京戶口才來的吧?在回憶這個細節時,沈之嘉笑了:“我當時差點就對校長說,我老家是杭州的,杭州戶口比南京的還貴呢!”
這一次,她如愿以償,在這家南京的職業技術學校找到了工作。
“靠譜”新青年的另類選擇
若干年后,當研究者梳理這段歷史時也許會發現,沈之嘉無意中加入了一股與社會主流趨勢相悖的“微潮流”之中—自2010年前后,一些接受過國內外最頂尖教育的年輕一代精英們,開始在就業上將目光轉向那些“非主流”地帶,比如最底層的鄉村,以及那些聽起來并不高大上但他們卻喜歡的職業。

當沈之嘉在試圖叩開中國藍領工人的“預備役”部隊—職業技校的大門時,另一位“85后”青年、美國耶魯大學畢業生秦玥飛已在湖南衡陽的一個小山村中默默地當了兩年的“村官”。
在這兩年間,秦玥飛為所在的衡山縣賀家鄉賀家山村募集到了80余萬元資金,幫鄉親們修建了灌溉良田的水渠,新建了一所田園風光式的敬老院,還為周邊4所學校就讀的700多名學生每人籌措了一臺平板電腦。秦玥飛因其出色的“政績”被鄉親們直選為縣人大代表。
但凡對中國農村熟悉的人都知道,上面幾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農村都是一個異常復雜的龐大工程。就以修建水渠為例,賀家山村的村民們渴盼了幾十年卻一直沒辦到。不了解內情的人可能會誤以為,秦玥飛能做成這么多事,可能是借助于他頭頂的光環—耶魯大學畢業生,或者借助于某些強大的人脈關系或背景,才能夠向上級政府爭取到財政資金的支持。但熟悉秦玥飛的人士則向《南風窗》記者證實,秦雖出身于重慶的城市家庭,但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上述資金的確都是靠秦玥飛從社會上“化緣”得來的,只有極少一部分來自上級政府撥款。
與其他大學生村官慣于伸手向政府部門“要錢”的思路不同,秦玥飛更注重搭建平臺,整合各種資源,借助外力“做事情”。在與記者交流時,秦玥飛會不時講一些很有創意的新點子,而“新媒體”、“市場”、“風險投資”、“項目包裝”、“營銷”等詞語更是掛在其嘴邊的高頻詞匯。一個在別人眼中可能是異常艱難的創業行動,在他眼里則更像是一種充滿著時尚感,聽看起來很酷、好玩、靠譜,又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
在為賀家山村修建新敬老院之前,秦玥飛就了解到,村上有一家不足40張床位的敬老院,但村里的老年人不愿意搬進去住。除了傳統觀念外,原因更多的還與敬老院的設計及設施不符合老年人需求有關。如何才能設計出一個更尊重老年人需求的敬老院呢?秦玥飛通過朋友多方聯系,長沙一家設計院得知情況后愿意免費提供設計方案。當這座包含有魚塘、菜地、果樹林的敬老院落成后,附近的老人們搶著去住。
在當選縣人大代表之后,秦玥飛進行了選民走訪,他發現,每家村民的具體訴求都不一樣,但也有一個統一的訴求,那就是校車安全,因為幾乎每個家庭都有孩子去上學。但在當地,二三十甚至三四十個學生擠進一輛準載7人的小面包車是家常便飯,其中的風險不言自明。秦玥飛便以縣人大代表的身份向縣里提出關于推進安全校車的議案,并一直跟進。終于,縣人大通過決議,政府推廣實施安全校車。但這其中牽涉諸多復雜的難題,比如經費來源(政府財力有限,無法承擔全部經費),又涉及多個政府部門(教育、財政、稅務、公安交警、交通等)的協調等,還涉及觸動了個別人的既得利益的調整(“黑車”司機就很不滿),等等,這些都需要統籌協調考慮。但功夫不負有心人,這件事終于“跑”成了。
為了募集資金,秦玥飛有時要帶上精心準備的項目計劃書,自掏腰包坐火車幾個小時去各地拜會企業家。有時在人家辦公室門外一等就是幾個小時,進了門往往談了十來分鐘就被人家客氣地請出來,被拒是家常便飯。而為了結識可能捐資的企業家,秦玥飛經常到各地“蹭會”,參加各種企業家出現的論壇。一旦他有了演講或發言的機會,他總會抓住最后的發言時間,請求在座的企業家提供各種資金幫助。
很多大學生村官發現很難真正融入當地,從最初下村時的滿腔熱情到最后離開農村時的傷痕累累。這些故事則會讓后來者認為大學生村官可能在農村無所作為,遂安于現狀,把村官當作基層“鍍金”的經歷,進而為考取公務員作為跳板,身在農村心在城。相比而言,大學生村官秦玥飛的樣本價值不僅僅在于他為村民們辦了多少實事,更在于他的經歷證明了青年人在農村的廣闊天地里完全可以“做成事”。這在當前大學生村官“治村模式”似乎走向窮途末路的當下,更顯珍貴。
豐裕社會里的新新青年
這兩年,一個由中國年輕人創辦、名為“陽光書屋”的公益組織也聲名鵲起。這家致力于借助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改善中國鄉村孩子教育不公平的公益組織的多名合伙人都是哈佛、耶魯等世界級名校的畢業生或在校生。
“陽光書屋”的志愿者、同樣留美的沈誕琦曾在一篇文章中點出了這家NGO的超強團隊構成:它的聯合創始人和執行總監楊臨風曾就讀于北京四中、伊頓公學,2011年從哈佛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后,先是供職于波士頓咨詢公司(BCG),后辭職投身于“陽光書屋”的營運;劉禹琦,從斯坦福大學大三休學,為“陽光書屋”全職工作;朱若辰,杜克大學畢業,高中畢業時就有一顆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楊歌,高中時獲得過北京“市長獎”,耶魯大學畢業后,繼續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物理博士……
外界也許很難理解,這群出身于優裕家境、接受過最頂級教育的年輕人,選擇的不是代表著財富和權力的華爾街、金融行業、世界500強、上市公司,而是中國偏遠農村的孩子們的教育。然而,這或許正開啟著走向未來的一種新的、規模不大的但新潮的社會趨勢。越來越多成長于豐裕社會的“85后”們,以及更年輕的一代人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開始去選擇一種能把個人的小興趣與這個時代的大責任相契合的生活。他們的選擇變得更為從容,眼光不僅不再緊盯著傳統的熱門領域和只用于謀生的職業,而是開始挑戰傳統世俗的主流標準,開辟更富挑戰性、更有社會價值的嶄新的選擇。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用看似不起眼的行動來推動中國的變革。
而這個“微趨勢”轉變的大背景則是,在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城鄉差距的鴻溝越來越大,人才在鄉村建設中呈現“斷流”。城市像一個巨大的抽水機,不僅將鄉村的藍領勞動力“吸”到城市的建筑工地,也把關系到鄉村未來的年輕一代精英們“抽”到了城市。這是數千年來中國鄉村建設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可怕局面。如今,隨著一批知識精英的“倒流”,中國鄉村的未來有了更多的可能。
“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好一點,但前提是國家好一些、社會上最弱勢群體他們能夠好一些。”在談及為何創辦“陽光書屋”時,楊臨風說。中國現在的城市化率已超過50%了,未來要達到80%甚至更多,也就是說,還有30%的中國人口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去。而目前生活在農村的這些孩子們,將是未來中國變革的一只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良好的教育,沒有足夠的理解力、沒有足夠的創造力的話,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沒有辦法進行下去的。所以他非常關注怎么能在盡量加強整個中國基層教育的基礎上,“讓這些將來會走入到城市生活中的農村學生也能夠站在相同的起跑線上,讓城市的人口跟農村的人口能夠相互理解,共同一起工作,一起把中國變得更好”。
而沈之嘉也告訴《南風窗》記者,她之所以選擇在基層的技校擔任教師,是因為她在大學期間的田野調查和社會實踐中與中國的工人階層有過大量接觸,深感自己作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應為這個群體做出點事情。她因此投身于教育,希望能給中國未來的新工人提供更多的知識上和精神上的支持與幫助,讓他們更懂得維護自己的權益、更懂得團結與合作,讓這個龐大的群體變得更加有力量。
不抱怨的“行動派”
這群充滿著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在面對中國基層的真實社會情景時,又表現出對現實世界的驚人的理解力。秦玥飛在湖南擔任村官后,地方上的一些干部有時會邀請這位耶魯畢業的高材生去做一些經濟形勢的報告,但他婉拒了:“我就是一個很普通的本科畢業生,耶魯是名校這不錯,可一個本科生又懂些什么東西呢?哪有什么膽量和能力來縱論經濟形勢呢!”在與其交流時,你會發現,他的這種清醒不是故作謙虛的姿態表示,而是真誠地發自于其骨子里。
“陽光書屋”的運作模式是,通過免費向農村試點學校的學生們發放平板電腦這個終端設備,將北京四中等名校的教育資源同步“傳送”給農村孩子們。在為農村的孩子們提供課件資源時,創辦者們最初是想提供幫助農村的孩子們提高“素質教育”的內容,但后來增加了對提高孩子們考試分數有幫助的、更為實用的知識。他們在一些硬件設施細節的處理上也頗為用心,比如,為了適應農村學校電源插座少的現實,他們開發設計了充電箱,能把一個教室內所有的平板電腦放在一起充電。而當初為了注冊這家非營利公益組織,楊臨風他們跑了整整14個月,“非常的艱苦,每天各種磨”,但很少有人有過怨言。
沈之嘉到職校求職的目的就是當一名老師,每天和學生們在一起。在工作了一個學期后卻發現,學校不斷拿一些非教學任務向她“壓擔子”,比如參與各種行政事務等,而這占據的時間甚至要超過她的上課時間。記者問她,這種結果是否與她當初來當老師的目的有一些不一致。她回答說:“是不一致啊。但這就是現實,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那樣的話,就真的變成了空想家了。我要做的就是,了解現實是怎么樣的,現實如何能與理想契合、對接在一起。”
去年的此時,沈之嘉剛剛完成碩士論文,在她奔赴南京的職校實習前與導師告別時,導師和她打趣說,你的幸福的時光結束,今后想和朋友們一起喝個小酒啊、吃頓燭光晚餐啊,機會就很少了。時隔一年,沈之嘉若有所思地對《南風窗》記者說,“什么叫做浪漫呢?一支玫瑰花、一只高腳杯,這叫浪漫,沒錯。但是,你也可以這么認為,當你看到社會進步的一個方向,感覺自己跟那么多勞動群眾的命運聯系在一起,你做出一個自己認為比較自由,但在常人看來也許不那么正常的選擇時,這何嘗不是另一種浪漫呢?”
(應采訪對象要求,沈之嘉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