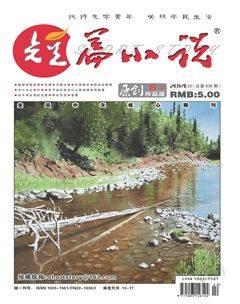簡·德萬尼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一、引言
20世紀初的澳大利亞是父權制觀念主導的男權社會,男性具有權威地位,而女性則被邊緣化,只具有“他者”的身份,缺失作為“人”的存在。男性為控制女性而創造出一種“理想女性”文本形象,即女性除了甘愿接受社會賦予她們的家庭職責,又需保持不現實的貞潔、禁欲的狀態,以自己的人生換取對“愛”的守候。由此出現在男性作者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大都表現為對立的兩極,即“天使”與“魔鬼”。“天使”型女性溫順謙恭,是男權社會價值標準虛構出來的理想女性。而“魔鬼”型女性有著獨立的意識,拒絕無私奉獻,可能對男性的地位造成威脅,因而常常受到妖魔化。這種簡單化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支配著傳統的男性敘事,扭曲了女性的真實形象。
男性文本里的女性形象只是他們想象的投射,女性為擺脫男性的控制而擁有獨立的人格,就需要通過解構并顛覆“理想女性”文本形象,塑造一種有別于傳統的新女性文本形象。正如埃萊娜·西蘇所言,“只有通過寫作,通過出自婦女并且面向婦女的寫作,通過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統治的言論的挑戰,婦女才能確立自己的地位”。
20世紀澳大利亞女性作家簡·德萬尼的作品飽含鮮明的女性主體意識和共產主義思想,一群以多爾西、莉蓮、瑪麗戈蒂、瑪麗金等為代表的具有鮮明性格特征的叛逆女性新形象被訴諸筆端。在男權主義者眼里,她們張揚放縱、道德敗壞。但透過她們的行為,我們看到的卻是洋溢著強烈的自我意識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她們是一群無畏的叛逆者。簡·德萬尼的作品反映了殖民時期澳大利亞女性的多樣性,女性的心態及欲求,理想與希望。
二、叛逆女性類型及其反叛意識的表現
簡·德萬尼的文本把外在的宏觀世界和內在的心靈世界結合在一起,塑造出的叛逆女性形象是豐滿而真實的,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以莉蓮、瑪麗金為代表的以縱欲濫情來表現人格獨立的女性形象,她們有覺醒反抗的一面,行進的道路卻是墮落;另一類是以達爾西、瑪麗戈蒂為代表的傳統女性,在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背叛自己的階級,將自我命運與社會、國家的命運相結合,精明強干的政治女性形象。
第一類是縱欲濫情的女性形象。以瑪麗金、莉蓮為代表的女性蔑視男性、風流放蕩,把追求感官快樂作為人生的目標之一。游戲于男性之間的她們對男性制造出的“理想女性”形象嗤之以鼻,以追求個體最基本的生理需求為手段,追尋失落已久的自我。面對這種女性,男性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得不表現出某種臣服和妥協。縱欲濫情的女性是時代的產物,當女性無法找到有效的途徑來否定社會倫理道德和宣泄自己的反抗意識時,自身的墮落就成為不可避免的結局。如簡·德萬尼小說《可憐人》里女主人公莉蓮,她是一個放蕩的女人,從十幾歲起就跟很多男人有染,婚后仍和情人保持不正當的關系,當地人鄙視她,把她當做恥辱。但簡·德萬尼卻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莉蓮,她贊賞莉蓮的隨心所欲和真實自然,在整部小說里,她更是頻繁地提到莉蓮的“天真”“清純”和“內在美”,還把她比作一朵百合。
簡·德萬尼懷著強烈的女性意識來寫這部作品,她把莉蓮置于一個弱者的地位,對莉蓮受到男性從心靈到肉體上的摧殘深惡痛絕。簡·德萬尼對莉蓮的同情和憐憫與其共產主義信仰和女權主義思想是分不開的,她認為,社會罪惡是資本主義的產物,一個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的女性,如果沒有經濟來源,生活放蕩是不可避免的。在簡·德萬尼的眼中,導致莉蓮現狀的責任不在她自己,真正應該受到譴責的是那些鄙視莉蓮的人,是這個丑惡的資本主義社會。
從現代主義批評的角度來看,簡·德萬尼那些描寫女性婚外戀、性和心理的作品擁有一種值得肯定的女性主義立場:對一直生活在男權專制文化陰影下的女性的叛逆和放蕩,給予一種體貼與寬容。盡管這一類女性表面看起逾越了道德規范,但她們卻展示著人性的真實,是人性的自然流露。
第二類是政治女性形象。囿于家庭的女性,除了生兒育女和洗衣做飯外,在政治上是完全邊緣化的形象。沒有政治權利和政治地位的女性必然在社會生活中處于被動地位,缺乏對自身命運的掌控能力,只能成為無知、可欺的弱者形象。[5]常見的文學作品里,對自我命運的把握和自我價值的追求是叛逆女性的核心形象,此類女性的主體意識發展仍然處于萌芽階段。但是女性的價值不應只是存在于其個體自然屬性, 更應具有社會層面上的意義。
簡·德萬尼對傳統叛逆女性形象進行解構和重建,但并不否定她們的女性特質。她塑造的達爾西、瑪麗戈蒂等政治女性的所作所為常常與社會傳統價值觀相背離,與大多數人的行為格格不入,覺醒的她們向自身的存在尋求幸福。她們獨立、健談、敢愛敢恨,甚至難以置信的完美。如小說《甜蜜天堂》里的達爾西,她本是一個天真的消極的女人,她不理解丈夫和其他人為何要策劃罷工,不愿丈夫卷入,但是隨著罷工活動的進展,她逐漸成長為婦女支持罷工團體的領導,加入了這場“不是為了工資,而是為了生存”的政治斗爭。這些女性形象似乎傳達了簡·德萬尼希望塑造的政治女性之美,她們具有獨立健全的人格形象,溫柔而堅強,并不依附于任何男性,也無需任何男人來解放。
這些叛逆女性形象表達了澳大利亞女性渴望達到在意識形態上與男性平權后,對社會前途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政治權力的認識和思考。這些原本的“理想女性”里沉睡的自我意識一旦被喚醒,追求獨立人格的渴望就無法抑制。但是她們沒有把實現個人價值看成是圓滿的結局,在實現個人價值的同時,她們的個人命運與某種政治力量或社會變革力量結合在一起,在政治斗爭或社會解放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逐漸掌握政治權利。女性命運的探索由此實現了從個體反抗到群體突圍的飛躍,傳統叛逆女性形象被賦予新的性別身份,擁有了更廣泛的社會意義。
三、叛逆女性形象成因分析
所有女性的思想深處都孕育著自由的種子,一旦碰到適合的土壤就會發芽生長。從順從到反抗,從被動到主動,從被壓迫者到解放者,女性形象的衍化實質上反映了一種社會和思想的衍變,具有很強的社會性和指向性。簡·德萬尼的作品主要寫成于20 世紀上半期,這個時期澳大利亞社會正處于重大發展與變革時期,她筆下的叛逆女性群體可謂是緊扣時代脈搏而衍生出來的一類女性形象,包涵社會文化以及作者本身等各方面的原因。
首先,強烈的女權意識。19世紀末期,澳大利亞女權主義第一次浪潮興起。此階段女權運動旨在通過削弱家庭和社會生活中的男性權威來促進女性的進步并進行社會改革,運動的焦點在于女性爭取選舉權。簡·德萬尼的女性文本形象反映了此時期女權運動的時代特點。在女權主義運動的影響下,婚姻不再是兩性關系的唯一選擇,家庭逐漸被看成是一種約束和壓迫的符號而受到批判。簡·德萬尼從傳統男權文化束縛中解放筆下的女性人物,她筆下的女性向往自由、追求人格獨立與完整,反抗傳統道德約束,具有叛逆精神的種種表現恰好折射了當時澳大利亞和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在政治、思想、宗教、道德、習俗等各個領域的巨大轉變。這些叛逆女性形象負載著簡·德萬尼對澳大利亞社會未來走向的深切關注和冷靜思考,同時也表現了她對澳大利亞白人傳統價值觀的挑戰,即如摩爾所指出的“女性的必然、種族關系的必然、性的必然、社會和生活的必然”,而這些所謂的“必然”,實質上就是男權主義對婦女的束縛和壓迫。
其次,作家自身的經歷。簡·德萬尼出生在新西蘭一個貧寒的礦工家庭,童年的回憶只是嗜酒如命的父親和辛苦養家的母親,這段經歷讓她對女性的遭遇有了深刻的認識。加入澳大利亞共產黨后,出于政治宣傳的原因,她采用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式進行創作,將浪漫愛情與革命政治相結合,試圖在文本中建構一種具有顛覆性的女性形象來喚醒女性對自己現狀的認知和承擔歷史變革的責任。對于簡·德萬尼來說,文學作品是宣傳的工具,她的作品里充斥著激烈和煽動的語言,較之傳統愛情文學少了一份傷感和痛楚,多了一種顛覆、叛逆和大膽,
因此她的作品經常是超越禁忌的,常常引起爭議。她的第一部小說《肉店》就譴責了婚姻中女性的性壓抑,大膽地表現了性對于女性的重要性,加之一些不加掩飾的性描寫,最終在澳大利亞、德國等多個國家被禁。
四、結語
毋庸贅述,簡·德萬尼文本中塑造的一些女性形象出于政治宣傳和反男權的需要而淪為一種類型化的符號印象,自身的文學價值多少受到影響。不可否認的是,簡·德萬尼運用手中的筆顛覆了男性中心的話語表達,新的女性話語權得以表露,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有力地推動了對澳大利亞女性文學主題的探討。
[參考文獻]
[1] Jean Devanny.The Butcher Shop[M].New York: Macaulay, 1926.
[2] Jean Devanny.Poor Swine[M].London: Duckworth,1932.
[3] Jean Devanny.Sugar Heaven[M].The Vukgar Press,2002.
[4] [法]埃萊娜·西蘇.美杜莎的笑聲[A].張京媛.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C].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2.
[5] 郭秀媛.后殖民姿態下的混雜性書寫[J].河北大學學報, 2009 (04).
[作者簡介]
劉浩波(1978—),男,江蘇南京人,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西華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澳大利亞女性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