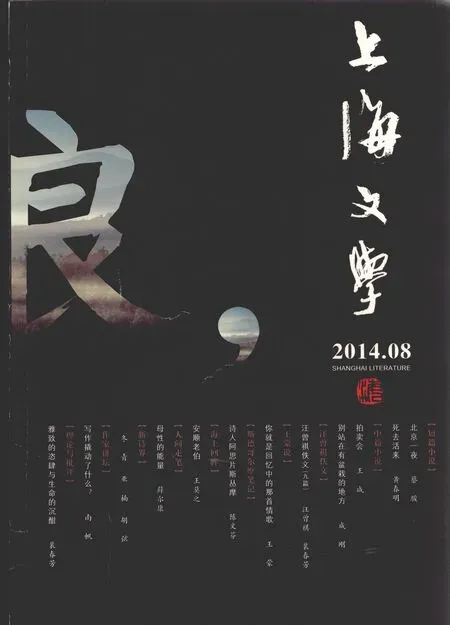安順老伯
王莫之
我們是在阿里旺旺上確認了老伯伯的往生。老板公布其父的病故,唯一的積極意義是平復客戶的發貨催促。一個月前,這招有過不錯的療效。當時他把父親住院的消息掛上簽名欄,外地的舊雨新知只好隱忍。
北京奧運那年,老板終于在安順路凱旋路口搞定鋪面,開了這家唱片店。他起初賣CD,因為這行飯他吃了快十年。他大學畢業后就沒上過一天班,引以為傲的不是在大二賺足了四年學費,而是沒賣過一張盜版。后來生意難做了,別人改行不影響他的堅持。也是緣分,他涉足黑膠,反正都是賣外國唱片業清理的洋垃圾,試試看,沒想到一路凱旋,于是專攻黑膠,轉眼送走了“二〇一二”。
2013年沒有老板設想的那么安順。年初,久居美國的母親加大了催促的功率,一通通電話招魂一樣,盼他早定行程,去紐約發展。也只有這些電話能讓他靜下來。我們蹲在旁邊挑碟,空氣里若無電腦游戲狂躁的背景聲,而他接電話的聲調還是熨平的,那必定是她又逼上門來。那時老板的生意還很紅火,客人打款到支付寶,一個月后能見著發貨通知的都燒過高香。這些人里黑膠新手居多,覬覦整箱八十張品種無重復的兩三百元低價,有撿漏的幻覺。歐美藝人最是緊俏,大碟等于瑞金醫院的特需專家,單曲好比普通專家,唯獨日本音樂(幾百箱的囤積,堆沒了小房間的天花板)親民,當日“掛號”隔天發貨。快遞選配,發貨流程,售后事宜,老板把種種不平等條款打上店鋪的主頁,紅字加粗,語氣蠻橫,可即便如此,每天電腦一開,叮咚叮咚吵得他心煩。
漸漸地,母親運作移民的苦辛成了瞎起勁。他當然沒這樣挑明,只是一拖二延三沉默的腔勢,傷人心。她甚至連工作都打點好了——到布魯克林的物流公司開卡車,月薪四千美金。“我去年光光淘寶收入就有毛三十萬,你講講看,是去紐約當癟三,還是來上海當老板。”老板冷冷地問我們。于是,當父親的就愈加郁悶了,有事沒事嘀咕:
“簽證辦了這許多年,辦下來多少不容易,現在倒好,講不去就不去了。”
他的郁悶還在理財學上找到支持。安順路的門面房子,多吃香。隔壁房產中介三日兩頭跑來搭訕,巴不得老頭子能勸走兒子。我們也算過一筆賬:出租現有的店面,搬到偏郊的社區,一進一出,每年起碼多賺六萬。更極端一點,學這行里的外地人,落戶跳蚤市場,收益更可觀。老板當然也動過貪念。葉家宅路的事久市場,虬江路的電子數碼商廈,襄陽南路的現代電子城,可選的余地并不大。況且,他早先在大自鳴鐘做過,對那伙人的厭薄與生俱來,即便過敏癥狀受外力控制,朝九晚五的工時也會叫他崩潰。這些年我們在安順路淘碟,最早的經驗是下午兩點。常是午休偷閑,我們撥電話,打探今天給不給看新貨,可老板剛從夢鄉驚醒;總是日落黃昏,我們對著透明的玻璃門站禪,上面貼的營業時間是17 ∶ 00-22 ∶ 00。沿街鋪面還有一大方便,裝卸貨物更自由,加之安順路毗鄰虹橋,招惹老外。外國客戶在老板的門面生意里比重不小,貢獻卻有限。“最好的戶頭跟最戇的戶頭全是中國人。”老板有過總結,“老外就是差差過,只有一兩個是大戶。”即便如此,老外就是老外,陪聊伴笑,若是買到積重難返,老板會發動他的路虎,送一段。我們并非這種一單破千的大戶,也很少消費古典爵士這些高價盤,好在勤快,一周光顧兩三回,單人一年也能開銷兩萬多。說起來,線上線下把雞零狗碎的也兜進,上海好歹有一幫人在做二手黑膠,但有實體店還夠噸位的不過三家,安順路是最體面的。這份體面在這個褪色的行業里碩果僅存,老板享受它呵護它,提到三觀的高度:
“可能嗎?哦,你屋里有三套房子,最好的不蹲,住到蹩腳的落鄉地方去,有啥意思!”他父親看得更深:
“他就歡喜這種感覺,所有人統統圍牢他,叫他老板。”
問題是,在我們看來他這個老板當得就像癟三。體力活,高強度的體力活是他每天的功課。一噸黑膠四十箱,拆箱時張張校對,裝箱時精心調配,都是他在忙。他先是把膠體彩色的彩膠分揀出來,再將單曲、EP、大碟、日本這四塊分門類聚,歐美單曲再按封套顏色細分“彩皮”和“黑白皮”,“黑白皮”裹了塑封還得幫它減負(一來省運費,二來可以當廢塑料賣)。有些唱片盤基薄,抽插不當比刀還厲害,因此他上工必戴紗布手套,一雙新的撐不了幾日,不然搞臟封套才叫損失。整個流程讓人想起外地人賣甘蔗汁的流動攤車,看他分揀唱片,仿佛是在碾榨甘蔗,直到它流盡最后一滴。所以,生意越好日子越苦。多少次,我們推門發現老板披頭散發還在忙打包,封箱帶又換一卷。他以為收件員來了,抱怨活太多快遞太積極,回頭見是我們,改口道:
“來啦!今朝少看幾箱哦,昨日一點貨我忙到凌晨兩點鐘才理清爽。”
他累成這樣,完全有理由雇小工,但一趟趟努力都躺倒在他爸那里。
我們最早來安順路就覺得滑稽:如此挺括精神的唱片店,怎么請個老年人來幫工。“老頭子,拿只矮凳讓他們坐。”而老板的頤指氣使,又讓人不敢推斷,蹲坐在門口抽煙的是他的親生父親。出于客氣,我們叫他“老伯伯”。
老伯伯抵制雇工的道理極簡單:他退休在家,什么事不能干?如果說能省則省是他的生存哲學,那么節儉就是他做人的樂趣——這點倒和老板的網上客戶有得一拚。他買菜光是糾結價錢而忽略味覺,殘菜敗肉,關鍵在于吃的人是何心理。他開火倉,飯桌就是市場和天氣的晴雨表,什么便宜吃什么,也不講究烹飪。我們見老板三餐老是吃外賣,難免嘮叨幾句,可是聽他回憶童年,仿佛看恐怖片,趕緊捂嘴。
好在忙亂不是一天造成的。起先,老伯伯就是跟在顧客后面,搬箱倒柜,整飭他們挑完之后的狼狽。當幾次清道夫,包個把快遞,看電視抽煙,這就是他的一天。可是,后來工作量激增,不是加法,而是乘法,他就吃不消了。父子合力還是缺人手。賺錢賺到舉步維艱,本就貧瘠的社交干脆取消。老板一面憧憬小工,一面寬慰自己:
“不過就算請了人,我還是要自家過一遍,這種生活不懂貨哪能做得來?”
他擔心招來外行比他爸還笨,更懼怕內行的私贓,就屈服了,父子關系卻愈加惡化。理貨發貨的煩躁仿佛一座山的干草,稍許火氣就會燃燒。老伯伯是教師出身,上世紀80年代末下海,干油漆買賣,蹬三輪跑單。他苦了大半輩子,手腳已跟不上指令,常幫倒忙。老板沖他兩句,就會聽到花式繁多的推諉或抵賴,結局是無休無止的爭吵。老伯伯原指望兒子簽證辦成,自己能解套,現在夢醒時分,爭吵也多了底氣。他們吵起來比電視里的調解節目更兇殘,當著我們的面相互揭短。一個揶揄對方只會往油漆里摻水,一個嘲笑對方做生意買房的本錢都是自己借的。有些事情也確實令人發噱。好比講,楊浦一家廣告公司訂了幾張黑膠拍片急用,催老板發當天件,老伯伯因為老年卡乘車免費,想賺快遞錢,結果送件延誤,吃了惡評。凡此種種,我們聽多了卻覺得老伯伯可親。偌大的申城,已經不適應這樣純粹的本幫小市民了。新一代的小市民缺乏城市認同感,精刮而懶,毫無生趣。
我們和老伯伯的對話大概就是那時頻密了起來。老板若是不在,話題開放得好似我們在挖隱私,實際我們是聽眾,是訴苦對象。老伯伯的父親還健在,這位百歲壽星也是多個下午的主角。“老早是大學教授,教英文。”講起老爹,老伯伯并沒有太多的驕傲,特定年代,因為父親吃的軋頭也是匆匆掃過。他需要一根接一根的煙釋放足夠的迷霧,讓他回到童年。他歡喜談那段辰光,談吃喝談享樂。無非是沈大成的菜包,凱司令的鮮奶蛋糕,家里那臺電唱機的喇叭像獅子的爆炸頭。他講起老爹的唱片癮:
“買了多多少少唱片呀!老早一點唱片全是78轉,又重又脆,比后頭‘文革辰光的薄膜片子吃相多了。”
說完,他兜進暗室,捧出一疊收藏。外封蠟黃,沒碰都像碎了。十之八九是去年那批“蟲膠”。新世代的唱機基本只有33和45兩種轉速,差不動這些老兵。我們當時建議老板掛上網賣的,原來進了有心人的庫房。就算是懷舊吧。他扣下老板的一臺仿古樣機,放這些“蟲膠”,聲音一塌糊涂,他倒蠻享受。
我們最近也在懷舊。可就是想不起來,是什么讓老伯伯開口講起婚姻。我們沒有刻意打聽,這有違我們的初衷。我們的目的是緩和父子間以暴制暴的情緒,改善購物環境。所以才學老娘舅,為雙方唱頌歌戴紅星。思來想去,大概是那次夸他當過數學老師吧。當時,我們坐在板凳上,一面翻碟,一面敬仰:
“我們只曉得你老早賣過油漆,想不到你還當過老師。”
他來勁了,點起一支煙,回憶昔日的課程,學生如何頑劣,同事差強人意,自己在代數上的造詣。聽他的介紹,基本可以斷定他在學校里人緣夠戧。不過,他的婚事卻是同事促成的。“窮癟三臭老九,啥人肯嫁給你?”當時已是大齡未婚的他其實對相親不抱希望。那一位呢,家里成分更糟。她的父親是資本家,與年級里的領導有過從。領導本著試試看的心態牽條線,沒想到雙方見面也沒互相嫌貶。“沒啥好也沒啥不好!”老伯伯回家和老爹遞話,最后說到她家住在常德路,很漂亮的一套老洋房。
這婚就算結了。
婚姻生活照亮了窮癟三的腔調、大小姐的脾氣。老板出生后,家里一百樣事情通通丟給男方。老伯伯不干了。我們只曉得她后來隨父母移民美國,老板留在上海全靠老伯伯養大。他的棄文經商,往油漆里摻水,應該就發生在這層背景下。至于離婚與否,沒人過問,他們也從未提及。
私底下,老伯伯不僅善言,還懂得欣賞兒子。老板在經商上的天賦——拿黑膠唱片做掛鐘,把“彩膠”理出來賣高價——當然歸結為遺傳。前年起,他拿下某國產黑膠唱機在華東區的總經銷。他的優勢是唱片唱機軟硬雙修,打包抬轎,于是,訂單遠赴新疆西藏內蒙古。他由此生了自創品牌的念想。“現在一點國產的唱機基本上全是空麻袋背米,你以為他們有生產線啊,狗屁,全部都是野雞廠家代工再貼牌。”他以五百元的入門款為例,零售一臺他賺一百,品牌賺兩百,高下立判。老板覺得上海人創業就該洋氣一些——“名字也想好了,叫奧菲厄斯,英文是Orpheus。”——還為自己的意大利品牌編了一串比樂符更動聽的緣起。“在翡冷翠長大的小男孩,從小就喜歡音樂,”老板難得開國語戲謔,“但是家境實在貧寒,所以只好在城里的唱片行、音響店浪蕩,趁別人試音的時候聽霸王餐。他立志長大后要當一名音響師,打造理想的器材——”說到這,說書人咯咯亂笑,提前慶功。
“哪里有這么便當!”老伯伯這冷水一澆,父子倆接著對咬。他看不慣父親在外人面前不給自己面子,父親見不得他在客戶面前夸耀,這樣會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這家唱片店會一直開下去。他只有使手段倒翹邊。于是,但凡老板因故外出,老伯伯就打烊拒客,營業時間亦如此。“店要關了,老板馬上要出國了。”這是最常見的一招。還有一手留給我們這些熟客:“今朝回不來了。”他受不了黑膠的霉味,把自己關在店外,對著馬路抽煙。我們若是糾纏,他就編排諸多緣由,建議下次聯絡好了再來。
偶爾,我們也會思忖:老板真去美國了,對他有啥好處?一個人孤苦伶仃守在上海,拌嘴掐架都沒方向,往后誰來服侍?他的老爹有那么多小孩照樣攤上養老難,虧得有套房子,子女不放心,輪流照顧。他呢?難道真就如他所言,賣掉安順路,住到松江去?他在九亭有一套小兩室,總夸那里空氣好,心心念念想去養老。
所有郁結,今天有些能解通,有些仍舊稱奇。
局面后來失控得突然。老板的貨源在日本,二手唱片店淘汰的庫存,垃圾站回收,處理到廣州沿海鄉鎮的料廠,道道過濾,層層扒皮,最后派分到祖國大好河山。2012年海關禁止洋垃圾入境,貨源斷了,舉國碟荒。起初,他覺得這是上天在幫他鞏固地盤。他盤算囤在九亭的幾噸貨,加上安順路的庫存,預計能撐到2014年春節。對手的彈盡糧絕,在生意人眼里永遠比自己的豐衣足食更銷魂。顧客不管這些,餓狼一般撲向老板的阿里旺旺,關禁卻絲毫沒有好轉的跡象。他有點慌了。新貨以前是三天開一批,一批八箱,現在八天動不了一次,一次四箱。價格也有調整,和當時連綿的酷暑一樣讓人不想出門。多少晚上,我們蝸在家里刷Amazon和Juno,阿里旺旺上聊天,老板很少搭我們的腔,感覺上,他在忙一件大事。等我們知曉,老伯伯已經進了醫院。
回憶最后一次與老伯伯的會面,真正沒什么新鮮。當日他一如既往地蹲在門口,要說難忘,就是牢騷多了一點,胃口不錯。他吃完第二根鹽水棒冰,還是抱怨熱。我們沒啥收獲,出門道別也是老橋段:
“再會噢,老伯伯。”
“噢!再會。”
我們可以在各自的想像中,在回程的閑聊中,在聯絡的電話中為老板辯護。我們覺得他和父親的情感遠比我們與聞的復雜,但是,當這份感情赤裸裸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誰又能夠預見呢?
三周后的禮拜六,老板叫我們五點到店里,說有新貨。剛巧那天家淳有事。他先要去接好友嘉杰,幫他運一架手工拼制的木馬。那是嘉杰給兒子訂的玩具。嘉杰面子大,還驚動了禁淘多年的胖兄。大家難得碰頭,約好了,先淘碟后聚餐。我們停好車,發覺店門沒開,便聯系老板。他和車子堵在五角場的高架上。說是這樣說,經驗告訴我們,有的好等了。一行人于是進了附近的茶餐廳。點完飲料,四個人圍著手機欣賞小鬼頭騎木馬的視頻。餐廳一角的電視正在播送“黑色星期五”美國人搶購超市的新聞。說是搶購,搶劫也不過如此。我們想起當年的大自鳴鐘,周六早上搶開頭箱的盛況,碟在飛,血在流,與新聞里的混亂相比,僅僅少了警察拘捕的鏡頭。大家當時還是學生,過早感受了社會的殘酷,可是談笑各自的碟友生涯,無不覺得那是最最美好的辰光。
“我幫家淳兩個人老早禮拜六好兜一天的片子。”嘉杰講起當年的淘碟地圖,一個個已經消失的據點,覆蓋大半個市區。自從葉家宅頹敗后,他就基本不淘碟了,和胖兄一樣轉戰海購,在英美日德的網絡唱片店留下了上海人的腔調。兩人還有一點交集是不碰黑膠,所以去安順路赴的都是處子秀。
六點敲過,老板音信全無,我們決定先過去,如果不在就必須改期。畢竟嘉杰還要回家帶小孩,聚餐不能太晚,盡管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話要講。好在店里亮著燈。隔著沉沉的霧霾(那天的PM2.5達到274)能望見老板的魁梧身量,弓背埋頭,像是在打包。我們興奮地推門,剛想說今天介紹兩個大戶給你認識,卻聽見嗚咽的哭腔,發自那個顫抖的大身體。
封箱后來是嘉杰代工,胖兄幫忙填快遞單,收件的見了這陣勢也懵了。我們圍著老板安慰他,了解老伯伯的情況,手里捏了多少餐巾紙,鼻涕眼淚還是來不及擦。原來人已經進了ICU重癥監護,醫生的意思,左右就是這幾天的事情。
我們需要大量的破折號和省略號(會出現比Harold Pinter的劇本更多的“停頓”標示)來還原當時的語境——他的哀慟,他的悔恨。這對我們對讀者都將是莫大的折磨。最好的證明就是那頓變了味的聚餐,還有某天夜里做的夢。事后,我們甚至害怕去安順路,拒絕上阿里旺旺,只是為了逃避記憶。所以我們無法給出老伯伯的具體忌日。但可以肯定的是,老板的母親在這期間回了上海。
圣誕前夕,老板的一通電話把我們召回陌生的過去。他強調這將是庫存的最后幾箱,希望我們周日過去。老板比我們想的要豁達。他母親也沒有老伯伯說的那么兇悍,她的淳樸著裝更吸引眼球,完全看不出紐約長島人士的風采,倒像是剛從長興島過來。我們也不好意思打聽,光顧著聊外面的動態:現代電子城關了,刀疤眉有十多箱黑膠打算出手;葉家宅到了一批日版中古CD,據說海關開了。
“是開了,來了五百噸CD。”老板說他的線人摸了半天一張黑膠都沒有。這也加劇了老板對未來的悲觀。他懷疑往后即使到了黑膠,下面的饑餓也足以一口吞掉,一根骨頭都不剩。事實也正是如此。熬過了幾個月的空白,老板下了決心去美國。臨行之前,他請我們吃了一頓飯。又是一次不堪回首的聚餐,唯一的積極意義是給我們留了一張合影。老板的幾處房產和車子處理得很妥帖。我們也是舍不得,家淳就提出想送他一程。
送別的那天艷陽高照。在奔赴浦東機場的高速公路上,汽車音響放的是Oil On Canvas的CD。Japan的這套現場專輯,初版黑膠是非常挺括的雙碟Gatefold,我們在安順路有印象的第一張尖貨;有趣的是,最后一張尖貨是Mick Karn的Dreams Of Reason Produce Monsters,Japan的這位傳奇樂手此后還發過一些專輯,但是只出CD版。Mick Karn過世已經三年半了。
看著老板拖著行李的影子越拉越長,我和家淳只是緘默,因為彼此都很清楚,我倆并肩作戰的機會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