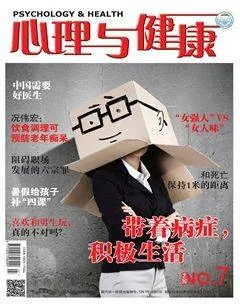妙語亦回春
韓鳳平
《太平廣記》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唐朝京城有位名醫,醫術很高明。一少婦隨丈夫外出,途中進食曾誤食一蟲,即疑心蟲在腹內食其臟腑,自此憂慮成疾。經數次治療都未能奏效,最后請到這位京城名醫。名醫聽到病因,便微微笑了。隨即叫來病人的貼身仆人,悄悄對她說:“我今天用藥使你們夫人吐瀉,你拿盤盂接時,就說有一小蝦樣東西吐了出來,事后不要泄露天機。”醫生施藥時,讓病人閉眼安坐,仆人遵從醫生的吩咐行事。之后,這位婦女的病就好了。這婦人為何聽說有蝦樣東西吐出,病就好了呢?這是因為少婦成病在于“心疑”,若去得疑,就不存在什么病了。正是疑心落地,身體通透,寬心平氣,病便退去。
疑病如此,那急病怒癥又是怎么“診治”的?且看《儀真縣志》:李瞻,以眼科著名。曾有一人眼睛紅腫疼痛,心焦如焚,急火中燒,藥而不效。李瞻了解病情后,稍事沉吟,對病人說:“治你眼睛并不難,只需將邪毒流注股部,十日內邪毒將自股部溢發。”病人把注意力都轉到股部,只等股部發毒。到第三天,李瞻用一味藥就把他的眼病治好了。十天過去了,股部也未發毒。李瞻事后解釋說,性急者患眼疾,愈思之愈難好。觀其情態,宜用“調虎離山”之計將病氣移開,此病者火毒攻及雙目,故移其意—以憂股下出毒,病癥好醫矣。
憂能生疾,也可治病。又有一醫書記載:某人新考上了狀元,喜出望外,告假返鄉,因歡喜過甚染病病倒。請一位名醫診視,醫生看后說:“你的病治不好了,七天內就要死去,快趕路吧,抓緊點可以回家看一看。”狀元好不喪氣,日夜兼程趕回家中,誰知七天后身體竟好起來了,好不憎恨那霉氣的醫生。一日,他的仆人進來說:“有位醫生有信致公子,特囑我交與您。”狀元拆開信,正是那位名醫寫來的,信中講,“公自及第后,大喜傷心,非藥力所能愈,故以死恐之,所以治病也,今無妨矣。”
那郁悶之病又如何醫治呢?古時名醫李建昂,為一儒生診治郁病。李建昂診畢,出來向家人要了這儒生昔日所讀之文,進屋就亂念狂念,儒生叱問何人狂囂、半點文句不通,李醫不管叱問,卻繼續不止,聲音愈高。儒生最煩人糟蹋斯文,一怒之下郁悶得泄,誰想病便不治自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