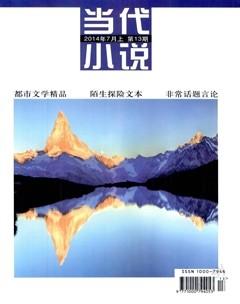月光陰謀
史鑫
A
我騎著單車遠遠地跟在他后面,死死地咬住他,前面一百多米遠的那個男子也騎著單車。他拐彎,我也拐彎;他加速,我也加速。他蹲坐在路邊抽煙之際,我則懷著興奮忐忑的心情在路邊的草叢前小便。小便的時候。我抬頭望天,月上柳梢頭,今晚月色不錯——但我不想贊美它了,這陽奉陰違的家伙,我對它徹底失望了,甚至對它充滿了無窮的恨意。
經過逍遙橋的時候,他不得不從車上下來。我知道,他那一坨肉實在太重了,不足一米七的個頭,居然有一百八十斤重,上橋的時候,估計他喘氣如拉風匣,發出呼哧呼哧的喘息聲。這逍遙橋是三孔石拱橋,亂石鋪基。條石鋪面,橋長約六十米,說不定這家伙還喝了酒,我甚至隱隱約約聞到了一絲二鍋頭的味道。飽暖思淫欲,飲酒更是亂性。這樣想來,更增加了我的興奮感。等到我過逍遙橋時,根本不用下車,直沖而上,動作輕盈,不費吹灰之力。
那天晚上幾乎沒風。因此,他呼出的酒氣也停滯在空中。一個失明的人,仍可順著那股酒味,輕而易舉把他找到。除此之外,在他的作用下,腳踏板每轉一輪,車鏈條都會摩擦護罩一下,金屬相接。形成有節奏的“瞠啷”聲,估計鏈條松了,或者護罩的螺絲松了,讓護罩發生偏移,與鏈條短兵相接,因此發出響聲。因此,即便在伸手不見五指的晚上,僅憑著有節奏的“瞠啷”聲,也會把你帶到他的目的地。
過了逍遙橋,右轉,前行二百米,轉左,先后經過左邊的人民醫院與右邊的王府商場,過一個紅綠燈路口,直行,約五百米,T型路口,轉左,約一百五十米,經過一條荒廢了的鐵路,然后二百米后轉左,五十米后繼續轉左。二十五米后還是轉左,眼前一條兩米寬的小胡同,里面三戶人家,最里邊的兩間小平房,就是我租住的房子了。
房子里邊肯定有人。年輕女子,貌美如花。她在等人。
她倚在小院的藤椅上,有時抬頭望月,有時低頭玩手指,想著冤家。這是中秋的月夜啊,該是舉杯對飲的時光,可那冤家還沒回來。她左右的手指纏繞,又白又細,像白蟲子面前舞蹈,這樣又無聊又期待的時候,門口處響起了沉重的叩門聲。
誰?她的聲音有些慌亂。
我,王大剛。
她猶豫了一下,把小鐵門的門閂一抽,還是把門打開了。先是酒氣撲面,然后王大剛推車進門,把破車往墻根上一靠,問張緩怎么還沒回來?余小林一邊關門一邊說過節吧。他的燒烤生意應該不錯。嗯,有沒有酒?日,還有花生米。于是,余小林搬出小方桌、兩只矮凳,端出一碟花生米。又拿出一瓶二鍋頭和三只酒盅。他們一邊喝一邊等張緩。王大剛仰脖飲酒的一霎,看見了空中的一輪滿月,他情不自禁地說:
今晚月色真好啊。
是啊,真好。余小林旁邊附和著,聲音很小。在余小林起身給王大剛斟酒的空當兒,王大剛一把將余小林攬在懷里,一個嬌小的身軀墜在一個肥大的懷抱里,像一只受驚的小獸。她掙脫著。口里說著別別別……忽然。她停止了輕聲呼喊。手中的酒瓶子“瞠啷”一聲跌落地面,他的舌頭鉆了進來,如蛇入口,搜索著,攪著,抽動著,那么有力,她幾乎要窒息過去了,開始階段,她的小拳頭還捶打著他的肩頭,后來,就軟了下來,衣衫凌亂地吊在王大剛的懷里,再也不能自控了。最后,王大剛站起身,抱著余小林向屋內走去,腳步有些踉蹌。
我眼睜睜地,看著他們上演一出淫樂大戲……
我站在東村二街3號懦弱的院子里,邋遢的想象場面無法收拾,我咬牙切齒,淚流滿面,無助,無力,像一個戰敗的匹夫。這一回,余小林徹底把我拋棄了。或者說,我再也找不回余小林了。
B
本來,傍晚時候余小林可以待在報社宿舍里,與幾個外省同事一起共度中秋的,可她整個下午都坐立不安,在房間里走來走去,也不說話。室友阿芳問她,你這是怎么啦?她想了想說,我想家想爸媽了。這下,阿芳的眼里便流露出想家的憂傷,阿芳來到余小林面前,兩手搭在她的肩上,說快了,再有三個多月,就可以放年假。就可以見爸媽了。余小林聽罷,默默點頭。
余小林想著張緩,一刻也不能停止。她要在晚間見到張緩。與他舉杯對飲,把憋了一肚子的話說出來。然后,再享受他粗獷的愛撫,然后做愛,最好,在想象中的火車經過時那一聲巨大汽笛聲中達到高潮。
余小林與張緩相識于夏日的小城街頭,轉眼間一年多了。那時,張緩還沒有下崗。王大剛還沒有考上公務員。他們在傍晚的街頭,懷抱吉他彈唱,唱完民謠唱搖滾。張緩一頭長發,剛大學畢業的王大剛則意氣風發,他倆吸引了不少路人駐足,也讓余小林停止行走。當二人彈唱結束。余小林走了過去:
你們唱得不錯啊。在下余小林。
余小林跟張緩、王大剛一一握手,張緩的手掌踏實溫暖。王大剛的手掌滑膩膩的,大概是肥胖汗多的緣故吧。面對這個突然出現的嬌小精致的家伙,他倆顯得非常興奮。張緩提出喝兩杯去,走啊,沒料想余小林爽快地答應了。旁邊的王大剛小眼睛滴溜溜轉,一聲不吭。
他們來到河濱大排檔。落座后,經過詳細介紹。余小林才知道張緩是一名工廠詩人,他現場朗誦的詩句中帶著初中畢業后便參加工作的十年滄桑,而一旁的王大剛正準備著公務員考試,這位北京名牌大學畢業的高材生。明顯點綴著飛升的光環,而張緩則是陷落:對工作厭倦。并且面臨著下崗的危險。
既然這樣,今后你給我們投稿吧。我跟副刊編輯關系不錯。余小林對著滿臉通紅的張緩說。
他早些年就在外省的大刊上發表組詩了。王大剛插進話來,這家伙酒量不錯,面不改色。
呵呵,那是以前的事情了。咱們好漢不提當年勇啊。張緩臉上的笑容閃了一下,端起面前的啤酒一飲而盡。
他們一直喝到河濱大排檔打烊,才起身離開。三個人都騎著單車,馬路上傳來吱吱呀呀的單車運轉聲。張緩明顯喝多了,蛇行的騎法讓人擔心。王大剛和余小林把他擋在人行道的外側。經過逍遙橋時,他們都從車上下來,推車過橋,當抵達橋中部時,張緩停靠在橋欄桿上,把一串嘔吐物拋入河中,似乎舒服點兒了。騎車繼續前行。到了光明路口,張緩與他們道別。拐到另外的路上,由王大剛護送余小林回宿舍。在路上,余小林想著張緩,她問王大剛:
張緩結婚了嗎?
結了,有一個女孩。王大剛停頓了一下,不過,他們夫妻現在分居。
啊,為什么?
性格不合,加上家庭糾紛,詩人嘛,也比較隨性,對了,你呢?有男朋友嗎?王大剛側臉問黑暗中的余小林。
C
與余小林認識的當年年底,王大剛就考上公務員了,分配到了縣文明辦,他一下子變成一個積極的人,吉他也不彈了,掛在宿舍墻上,落滿灰塵,再后來,為了打消心底那份閑情逸致,他干脆把吉他送給余小林。但傳授吉他技藝的活兒則落在張緩身上。這對于余小林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她可以近距離、頻繁地接觸這位有文藝范兒的漢子。除了唱和之外。還可以切磋詩歌。還別說,在余小林的撮合之下,張緩真的重操舊業。寫起久違的詩歌,并在余小林的那份報紙副刊上整版發表。頓時,張緩成為小城一顆冉冉升起的文學新星:只不過,大家對張緩缺失了解,讓他的詩歌在一段時間內蒙塵,現在,又被余小林給擦亮了。
任何事物,只要時間久了,感情自然發生。對于余小林與張緩來說,也不例外。他倆這么一來二去。眉來眼去,就情投意合、耳鬢廝磨起來。當然,這事瞞不過王大剛,雖然他轉身成為一名積極分子。但那時尚未與張緩斷絕聯系,偶爾也會跟張緩、余小林見面。有時是三人一起,有時是與余小林二人。在王大剛看來,余小林就是一匹愛意泛濫的母獸,隨意拋撒柔情。王大剛清楚這點。也未急于求成。而是將他的野心包裹起來,隱藏起來,要等待一個適當的時間。是的,要等待。否則,小不忍則亂大謀。
最終,中秋節來了,在王大剛的期待之中,順著一條氣喘吁吁的道路,在酒精的作用下,在月光的氛圍里。喚醒了二人內心深處的欲望之神,這老人家幾乎是破門而出,伸著火紅的小舌頭,在中秋之夜,在月光下酣暢淋漓。一發而不可收了。
王大剛站起身,抱著余小林向屋內走去,感覺余小林身體很輕,也很燙,像個小火爐,末了,發現余小林更像一只注射了麻醉藥劑的小獸。在王大剛的懷抱里癱軟了。抽搐著,醉眼惺忪的樣子,面部緋紅,朱唇微啟,簡直就是一顆熟透了的葡萄,王大剛饞涎欲滴,恨不得一口就把余小林吞食下去。
親吻愛撫的環節在小院里已經進行過了,到了床上,王大剛想直奔主題,但遭遇障礙,他在余小林的褲襠部位摸索了半天,愣是沒找到余小林防護私處的紐扣與拉鏈,他有些懊惱,覺得自己沒用,最后,在余小林手把手的牽引下,王大剛才在余小林緊身褲的右邊外側找到突破口。王大剛不禁暗自叫絕:設計得真好,真夠聰明,應該大力推廣才行。障礙解除之后,才輪到王大剛像剝蔥一樣,把余小林的衣服一件件從她身上剝離下來,直到面前的余小林赤條條地裸露在床上。那晚沒有開燈,月光穿過窗欞照射進來,照在余小林身上,用什么比喻好呢?就叫玉體橫陳吧。在剝余小林衣服的時候,王大剛也把自己剝了個精光,那衣服幾乎是扯下來的,某些部位肯定受到了損傷。就在王大剛打算采用傳教士姿勢進入余小林體內時。外面忽然傳來“啪啪”兩下敲門聲。二人大驚,抖抖索索尋找衣服往身上按。在整理了一下情緒之后,余小林用她不太純正的略帶沙啞的山東口音問道:
誰呀?
白晃是的院子外,居然無人應答。
D
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
余小林和王大剛先后問起過我。回答卻有所不同。是的,那晚我去哪里了?現在想來,連我自己都有點模糊不清了。那晚。我像一匹迷途的野馬,帶著憤怒與憂傷。馬不停蹄,去了不少地方。開始,確實把燒烤攤給擺出來了,而且先自個灌下兩瓶啤酒。燒烤攤擺在河濱大排檔的隔壁。這個地方我覬覦已久了,沒下崗的時候我就瞅著這里,但下崗這鳥事來得沒想象中的早,捱過了一個冬季和一個春季,在漸漸燥熱起來的初夏時節才耷拉著臉到來。我并不是非選擇這燒烤檔不可,關鍵我喜歡喝啤酒,酒量雖不大,但就愛這一口,那么在解決我喝酒下酒菜的同時,也把再就業這事兒給解決了。豈不兩全其美。當然,還隱藏著一個理由,河濱大排檔是我跟余小林初識的地方,我可以每晚對著它回憶一遍懷念一遍,有時還會對著那些嘻嘻哈哈吃我燒烤的妙齡女郎進行一番對比,個子、身段、臉蛋、嘴巴、發型、穿著等,找出她們踉余小林的差異,找出一百個余小林勝出的理由;雖然這數字日后逐漸減少,雖然那美貌那回憶像漸漸暗淡下去的火炭。
那天晚上你到哪里去了?余小林說這話的時候,是中秋節次日下午。她到來的時候,我還在蒙頭睡大覺,她的到來讓我很不爽,她嘟嘟嚷嚷坐在床邊,揪頭發、撓腳心、扒眼睛,我照舊不理,直到她問起這話的時候,我才恢復一點清醒,一下子爬了起來,靠在床頭,掏出一根煙點上:
我擺攤去了啊,我能去哪兒?
那后來呢?怎么沒回來?
生意不好,早早撤攤了,連個人都沒有,最后才知道是中秋節,他娘的,估計我是中國最后一個知道這節日的傻逼。
撤攤后你去了哪里?
到了家里一趟,跟老爸吵了一架,又出來了。
怎么又吵了?
問個鳥兒,就是吵了,很煩啊,別瞎雞巴問了,你以為是采訪啊?我扭過頭去,透過玻璃窗,幾只麻雀在梧桐樹上撒野。
你是不是有了其他女人?想不到,這廝突然冒出這么一句,簡直把我氣炸了。
你他媽的,神經病是吧!
肯定有外遇了,不然為什么沒回來。余小林揪著不放。
是啊,我有外遇了,人家貌美如花,對我緊追不舍。
哇的一聲,余小林就哭了,緊接著,帶著哭聲跑了出去,推單車的聲音,開門聲,以及瞬間消失的哭聲。我的耳朵跟隨著,冷不丁的,聽到_個三十歲男子的抽泣聲。
兩天后,見到王大剛,這回是在胖妞餃子館,他抽著煙,左手食指在杯口上繞來繞去。
你跟余小林吵架了吧?聽說你有了外遇?
她的話你也信?她純粹是沒事找事,自找沒趣。
好好待人家,她挺不容易的。
這年頭,誰容易啊?
呵呵,也是。還寫詩吧?
寫,一直沒斷。
哦。難得啊!對了,中秋節晚上你去哪了?王大剛抬起眉頭,一雙黑洞洞的小眼睛里藏著狡黠。
E
中秋節晚上,張緩真的回了趟老家。這還得感謝河濱大排檔何老板的提醒,他說小張你怎么不在家中秋賞月。還出來賺錢啊?張緩這下才如夢方醒,怪不得沒客人光顧呢。這豬腦子。他一邊埋怨著自己一邊忙不迭地收攤,將雜物寄存在何老板那里,然后,提上兩瓶玲瓏春外加兩包隆升酥,在月色中,他騎著單車,從西向東,穿過整個縣城抵達爸媽的住所。他們正在觀賞中秋晚會呢,老父親拍著大腿罵罵咧咧的,這是一條經常噴火的老烈龍,對諸多事物看不慣,以至于讓發火成為一種習慣。
吃了嗎?老龍停止憤怒,把目光轉移到兒子身上。
吃了。
今晚還擺攤嗎?
擺,一會兒就去。媽媽聽罷,把張緩拉到一邊,老是不吃飯,怎么不早來個電話?那邊沒有電話亭。嗯,廚房里有飯菜,我給你溫一下。不了,媽,我這就走了。說完,張緩轉身而去。瞬間,感覺一股幽怨的目光投射過來,當然,還有一束若無其事的目光,片刻地停留后,又回到電視晚會上。
從爸媽家出來,張緩居然覺得無處可去了。心里面涌起一股深深的挫敗感。打小在爸爸的巴掌與辱罵下長大,高中輟學就參加工作,本想當一輩子的工人,不料。這想法被該死的下崗打破了。至于婚姻。更是一言難盡,話不投機,心猿意馬,到頭來,他提出分居,隨即被爸爸從家里趕出來,只得將身家暫且安置在出租屋里。至于余小林的出現。則是給張緩愛情路上的一個驚喜,可惜好景不長,張緩產生巨大的危機感,總擔心著丟失、分離;并且,他隱隱察覺到了跟余小林做愛時她那叫床聲與所謂性高潮的虛假。
罷罷罷,不如打馬歸去。張緩騎著單車,在月光照耀的秘境里穿行。他突然想象出王大剛此時正前往他居所的途中,看見他吸煙、喘息,聞到他濃重的酒氣,聽見他胯下單車鏈條“瞠啷”擊打護罩的聲音。張緩看得真真切切,他要追究下去,于是,加快了騎車的速度。
到了東村二街巷子口,張緩遲疑了一下,把單車架在附近的一棵楊樹上,懷著異樣的心情徒步向家門口走去。他掀開鐵門上的小蓋板,里面門未鎖,有兩輛單車一橫一豎呈交叉狀擺在院子里,很明顯,一輛是余小林的。一輛是王大剛的,除此之外,地面上的酒瓶子,小方桌上的酒盅、花生米都在,人卻消失了。這是不正常的。張緩急了,并不開門進去,而是舉起手掌對著鐵門“啪啪”兩下。
誰呀?
從臥室方向傳來余小林尖細、沙啞混雜在一起的詢問聲。張緩有點后悔了。不該敲門,何必呢?強摘的瓜果不甜,君子成人之美,不該是你的就不是你的,隨他們去吧。想到這兒,張緩掉頭而去。在經過廢棄的鐵道口時,他看見了空中一輪滿月。月光真好啊。可惜它是別人的。于張緩而言,那月亮是孤獨的,清冷的,像一個注定要形單影只的女人,或是一個居心叵測、行為詭異的大胖子。
F
中秋之夜的縣城火車站候車大廳內乘客稀少,多是一些異鄉客和無處可去的人,張緩買了一張開往省城的車票,連夜趕往那里的目的。無非是暫時離開這傷心之地:當然,也不排除另外的因素。
兩個小時后。張緩抵達省城,然后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館辦理了入住手續,半個小時后,一個行色匆匆的穿著時髦的女人敲響了張緩的房門。
你怎么突然來了?
沒事。就是想來看看你們,張弛呢?
我媽摟著他睡了。
好久沒見他了。說完,張緩低下頭去,大顆的眼淚流出來。
到底怎么了?張緩坐在床沿上,女人走過去緩緩摟住他的頭。
這是張緩與妻子小川分居兩年以來第二次重逢,雖然隔了兩個小時的路程,但就像兩個國度的人。時間在消磨他們的思念和憂傷。想當初,與小川婚姻的起始源自于性饑渴,與小川婚姻的危機則來自于性冷淡,三年的婚姻生活恍若從熱帶叢林走到冬季沙漠,冥冥之中,兒子張弛維持著這場婚姻的平衡。不至于那么快就發生崩盤。
那一晚。其實就只剩半個晚上了。小川沒有回家,被張緩留下了。開始,兩人相擁而臥,后來,張緩躁動起來,伸手打算褪去小川橘黃色的小內褲,卻被小川阻止了,我來例假了。張緩一下子變得不好意思起來,感覺自己很卑鄙無恥。似乎自己掌握著生殺大權,決定著定罪與赦免。往日里。他對面前的女人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對愛恨任意揮霍,一會兒像貪婪的暴君,一會兒又像委屈的孩子。當時他蜷縮在小川的懷抱里,是一條伺機躍起攻擊善良人的蛇。回想至此,張緩禁不住嗚嗚大哭起來,把小川弄得好不焦灼,對她懷里的男人哄了又哄,撫慰復撫慰,直到沉重的夢魘襲擊了他們。
早上,張緩醒來的時候,小川已經離開了。張緩明白,她要回去負責跟老人家解釋,要安撫孩子早上醒來對于媽媽丟失而造成的驚慌,還要重新整理心情,面對未來撲朔迷離的生活。
折騰了一晚。張緩徹底無力了,但也平靜下來了。
他能夠像往常一樣,能夠面對一個黎明的到來,他意識到愛恨情仇生死別離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他洗漱完畢,走出房間,辦理退房手續,然后吃了三根油條喝了一碗豆漿,這才坐上開往縣城的列車。
正午時分。張緩拎著兩瓶啤酒回到東村二街3號,天氣若明若暗,時隱時現的太陽照著這個破敗灰暗的小院子,單車不見了,小方桌連同桌上的雜物不見了,地面似乎還清掃了一下。打開房門,一股潮濕沉悶的氣味撞了過來,這讓張緩稍稍有些不快,走進臥室,床上的被褥收拾得整整齊齊,看不出任何掙扎搖擺的痕跡。嘿嘿,張緩干笑了兩聲。緊接著走出來,把兩瓶啤酒快速灌下,然后。衣服也未除下,把自己摔到床上,這樣,在酒氣的掩護下。就聞不到任何蛛絲馬跡了。就這樣,半夢半醒的輾轉在床上,直到余小林的到來。
在余小林到來之前,張緩腦子里反復浮現一系列關鍵詞:不忠,鬼混,虛假,菜刀,毒藥,勒索,籌備,下手,誹謗,質疑,出走,逃離,自首,歸案,從良,生活,真實……
G
兩年之后。某天,我去了一趟醫院,醫生建議我,多休息,不要有任何心理壓力。我覺得他的話純粹是瞎扯淡,我才不管什么病呢。不過,我喜歡獨處是真的,經常憂傷,記憶力下降,也敏感多疑,。雜志社的領導也建議我回家休養治療,基于我在創作上的成就,還給我留了退路:等你康復后可以再回來。對此,我雖說不上感激涕零。心里面也在默念阿彌陀佛了。這是一個多么好的時代啊。再說,我也想家了,順便可以回家看看他們。在一個陽光和煦的上午,我告別了南方這座繁華都市,坐上領導給安排的軟臥打道回府。在列車上,我給自己制定了頗為詳盡的生活計劃與行為指南。
首先,我要跟小川復婚,把她跟張弛接回縣城,與老爸言歸于好。最好來個大大的擁抱,最終,讓我們這三口之家生活在爸媽身邊。伺候二老頤養天年,讓小川重新獲得愛意,陪伴張弛成長,讓他獲得良好的教育,讓他品嘗到父愛與家的味道,而我,則像海子所寫的詩中那樣——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游世界……
其次,跟遠方的余小林通一個電話,向她表達我的歉意,跟她提及我的病情(作為一種懲罰吧),告訴她當年我絕情的種種,逼得她遠走他鄉,把我對那段時光的美好回憶與無限眷戀也告訴她,給予她祝福,祝她早日找到白馬王子,早生貴子,祝他們幸福和睦,祝她生活的那個所在像天堂一樣。
再次,我要和王大剛見面,進行一次長談,我對他當年為了“創文”而拆除河濱大排檔以及禁止我擺燒烤攤的做法既往不咎。然后。將那個“中秋風波”擺在桌面上,問問他到底有沒有睡過余小林,如果我們和解了,那么就有可能醉一場,大醉,不醉不歸。
……可事到如今,我被四周白色的墻壁圍繞,空氣里充滿了消毒水的味道,醫生與護士在我面前穿梭來去,我陷入巨大的驚恐與不安之中。
根據我此時的記憶,爸媽確實把我從車站接回家的,老龍突然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媽媽在旁邊攙扶著我。爸爸拎著重物,秋風把他禿頂上的一圈銀發吹得搖
搖晃晃,我們走在落葉翻滾的大街上,仿佛壯士歸來。
回家當日,我用爸媽的電話撥通了小川的手機號碼,電話里她正在喘息,聲音也柔軟得稀里嘩啦,喂!張緩,有事嗎?我說沒事,我回來了。哦哦,那好,抽空來我們家做客,先掛了啊。噢……電話尾音里,傳來小川那熟悉的床上呻吟。我看了看掛鐘,時針正指向十三點。看來,小川擁有了嶄新的愛情或是婚姻生活了。
致電余小林沒有成功,電話里傳來:您好,您撥打的電話是空號,請核對后再撥。我意識到與余小林失去聯系了。這讓我有點措手不及,沒事先做好心理準備。我壓抑著自己不去胡思亂想,不讓思維走上邪路,心里想著:她在遠方應該是好的,憑她年輕貌美,又不乏文采。肯定能獲得高富帥們的垂青。
王大剛得知我回來后,次日便趕了過來,眼睛還是那么小,但身體卻胖了一圈,他笑瞇瞇地前來,提著禮物,似乎又回到了當年。我恭喜他升遷,對此他避而不談,倒是同我聊起那些陳年往事。
對了,問你一件事情,兩年前的中秋夜,你是不是到出租屋來找我了?
怎么會?那天晚上單位組織中秋匯演呢,縣電視臺有直播。
啊!不會吧?我記得那晚的月光很好。
嘻嘻。兄弟你記錯了吧,那晚陰天呢,我用手電筒護送一位女同事回的家。咳咳,媽媽在旁邊咳嗽了兩聲,王大剛馬上噤聲了,我則沉入無邊的虛幻。
甚至,此時。我感覺到面前的病室也是虛構的,包括窗外的天空,有可能是一張巨大的背景畫,偶爾飛過的鳥兒,也可能是某個少年手中放飛的一只紙鳶……
責任編輯:段玉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