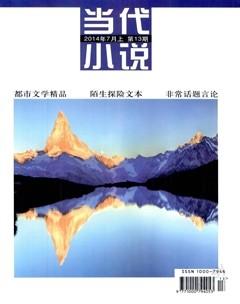截殺
王健 王菡
解放前。從內(nèi)蒙古包頭市經(jīng)過鄂爾多斯、烏審旗到寧夏的陶樂、平羅一帶有一條商旅大道,叫做“蒙邊道”;中間經(jīng)過內(nèi)蒙、陜北和寧夏三省交界的地方,叫三段地。這里往東80里是內(nèi)蒙的鄂托克前旗。往西50里就進了內(nèi)長城,到了寧夏地界,往南60里又到了著名的陜北三邊之一靖邊縣。前清年間。康熙皇帝親征葛爾丹叛亂。三次打仗,兩次從這里出兵,出鎮(zhèn)二里有余,大路旁坐落著當時清軍的糧草場,號稱老營盤:當年康熙爺御筆親題“一騎踏三省,王師鎮(zhèn)九邊”指的就是這里,別看地方不大,可確實是個要害地段。咱們要說的故事就發(fā)生在這里。
1949年1月,我在綏寧工委保衛(wèi)部擔任偵察科長,一個寒冷的夜晚,保衛(wèi)部首長緊急召集我和偵察隊長馬三喜開會。部長和政委向我們交代:剛接到邊區(qū)保衛(wèi)部通知,隨著平津戰(zhàn)役結(jié)束,敵人正在做失敗前的最后掙扎,派出一批高級特務(wù),陸續(xù)向西北各省滲透。根據(jù)內(nèi)線情報,一個叫王冬的軍統(tǒng)中校,帶著電臺和密碼,五天前已化裝從包頭出發(fā)前往寧夏,準備長期潛伏,伺機破壞。上級給我們的任務(wù),就是在中途活捉他,繳獲電臺和密碼。但我們除了他一個名字,其它都不知道,更沒人見過他。怎么查找?怎么捉拿?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經(jīng)過大半夜商議,保衛(wèi)部決定派出一個精干的偵察小組。化裝前往三段地,在這個寧蒙之間的必經(jīng)之路截殺他。
第二天上午,朔風(fēng)凜冽,天冷得能把人耳朵凍掉:一支駝隊出現(xiàn)在荒漠里,駝鈴丁當丁當?shù)仨懼N液婉R三喜、劉黑娃騎著馬走在前頭,我變身成一個富商,高筒皮帽黑墨鏡,身穿價格不菲的二毛皮袍。馬三喜是駝隊頭,小劉是小伙計,后面三個都是駝駝客(駝夫)裝束。我們每人一支短槍,一把匕首,再就是人人一身好功夫。我和馬三喜都是自幼習(xí)武,經(jīng)歷多年的戰(zhàn)火熏陶,格斗中三四條大漢近不了身。劉黑娃雖才17歲,卻有一身好輕功,隨身還帶上了一根兩頭包鐵的打狗棍。后面拉駝的白音寶格圖和巴特爾是兩個蒙古壯漢,是保衛(wèi)部最棒的摔跤手。金盛財則是個出色的“刀客”,一把宰羊刀耍得出神入化。我們一邊走一邊商量。按我們的推算,當時的蒙邊道上不是戈壁就是草灘,荒無人煙,這時節(jié)天寒地凍寸草不生,土匪刀客出沒無常。那個特務(wù)王冬只有沿這條大道走才比較安全,還能住店吃飯得到接濟。按他出發(fā)的時間,明天就應(yīng)該到三段地了,一旦碰面必是一場生死相搏。我們必須提前趕到,在那“恭候”他。
暮云四合,我們趕到了三段地,穿過熱鬧的集鎮(zhèn),直奔“老營盤”。“老營盤”歷經(jīng)滄桑,早就破敗了,后被人購得修成了客棧。成了這一帶最大的“豪華酒家”,大號三義盛客棧。這客棧還真是名不虛傳。高高的土墻圍了個足有三十幾畝地的大院子,院中是一個高大的中庭,康熙爺御筆親題的金字牌匾就掛在正堂上,周邊是一排排大房子。客房、倉庫、廚房、牲口棚、草料場一應(yīng)俱全,都是厚重的大土坯壘成的平房,還保留著當年那威風(fēng)凜凜的軍營氣勢。我們被兩個伙計讓進了中庭,剛收拾停當。一陣丁丁當當?shù)鸟勨徲蛇h而近,又是一隊駝隊走進了大院,為首的是一個肥壯的黑大漢,體重足有200斤,光禿禿的腦袋,趴鼻子,頜下一副絡(luò)腮胡子,滿面煞氣。另一個是個黃臉漢子,寡皮精瘦,一臉煙容,兩只三角眼滴溜溜亂轉(zhuǎn)。后邊也跟著一個伙計三個駝駝客。這伙人剛進中庭坐定,后面一陣響動,緊跟著一個公鴨嗓子嬌嗲嗲的傳了過來。“哎喲喲,我說怎么一大早就聽著喜鵲叫,原來是來了老客親爺們……”話音未落,一個年近六旬的老嫗冒了出來,此人頭肥身短沒脖子,一個碩大的腦袋直接栽到了肉球似的身子上。兩條胳膊比水桶還要粗些,滿頭亂發(fā)直豎,臉上抹得像個白面團,上嘴前突,下嘴縮進,活像一只狐貍,嘴旁兩道深深的紋路更凸顯出她的潑悍。蒙邊道上口口相傳的三義盛大掌柜孫佩花“孫寡婦”。竟然是這樣一個又老又丑的怪物,不禁讓人啞然失笑。
吃罷晚飯。我西他東。兩伙人被伙計送往中庭兩側(cè)的客房安歇。那客房是一溜五大間,,屋里是連鋪大炕,炕前擺著條桌長凳,墻上是上下開合的木格子大窗。一燈如豆,我們緊張地商議著。一是我們選在這里守株待兔對不對?--是今晚來的是伙什么人?正小聲議論著,突然,門邊放哨的小劉做了個噤聲手勢,一指窗外,馬三喜噗的一聲吹滅燈火,老白和老巴滑下炕去,悄無聲息掀起上窗探出身去,一個伸出兩只大手捂嘴掐脖子,另一個抓住來人衣服,“嗨”的一聲,竟把那個貓著腰躲在窗外偷聽的人,硬生生提了進來。老金的刀子緊緊跟上。在他脖子上不輕不重比劃了一下。一見血那人立時癱了。
“饒……饒……饒命。”
“說!”
“說,說,我全說,別……別殺我。”
我打著火一看,原來是酒店的大伙計……
經(jīng)過審訊,我們弄清了情況,一是孫寡婦開的是個黑店,這里就是蒙邊道上走私販毒、銷贓贖票、拐賣人口的交易場所和中轉(zhuǎn)站。二是今天來的是伙歹徒。那黑大漢就是盤踞在麻黃山的大土匪張武,江湖道上有名的賊武子。跟隨的伙計就是他的保鏢。那黃臉漢和他的同伙是道上有名的一群“土客”(大煙販子)。這次是黑大漢帶著搶來的財物到包頭,通過黃臉漢四處銷贓,換成了煙土、槍支和紅傷藥,護送他們返回匪巢。三是這伙毒販看著我們馬好駝肥,貨物沉重,竟起了歹心,想趁夜深人靜把我們“做了”(暗殺),再干個肥票。晚飯后黃臉漢去找老窩主孫寡婦商議。于是孫寡婦派這個笨蛋來偷聽我們談話,要摸清我們底細。
情勢險惡,只能先下手為強。我們略作布置,押著那伙計,悄悄摸出房去……
到了“土客”房前,刀子一頂,那伙計哆嗦著叫開門。我們一擁而進。“都別動!誰敢動我崩了他!”馬三喜舉起了手槍。屋里煙霧繚繞,臭氣熏得人一個跟頭,炕頭上,黑大漢和黃臉漢正躺著吞云吐霧燒大煙,剩下四個人正脫了光膀子,圍著地下一個小火盆捉虱子烤裹腳布。見我們沖入,雖驚不亂,顯然早就見識過這等場面。黃臉漢一骨碌跳下炕,瘦臉硬擠出一絲絲笑紋,“別誤會,兄弟是包頭蔡云記老板蔡生禮,有話好說。好說。”“蔡蟲子,你賣大煙都從河?xùn)|賣到我們河西來了?”一揭了他韻老底,他頓時愣住了,“長官,你們是……?”我掏出繳獲的國民黨證件一晃,“說出來嚇你一哆嗦,老子是河西保安司令部偵緝隊的。今天撞上了,算咱兄弟們有緣,現(xiàn)在各位的安全就由我們負責。當然,各位的貨也都交給我們。”黃臉漢頓時急了,“使不得,這可使不得,這貨都是……”他頓了頓,斜眼看著黑大漢。我作勢一拱手,“武子哥,幸會。”那土匪頭惡狠狠盯著我,臉色越發(fā)猙獰。我揮揮手,“把那倆摁住,帶其他人起貨。”幾個人一聲答應(yīng),上前就要動手。“慢著,你們真是偵緝隊的?”角落里突地站出一個駝駝客來,三十六七年紀,精悍健壯,目光陰冷。我故作輕蔑:“嗬,誰他媽的褲襠破了,咋冒出這么個(song)貨?”那漢子勃然大怒,“混蛋,他媽的見了長官還敢放肆……”他突然意識到失言,立時住嘴。踏破鐵鞋無覓處,沒想到這“獵物”居然自露馬腳,我們不由心頭一陣狂喜。“長官,我們就是來接你的,”小劉一躍而出,竄向那漢子,那漢子驟然臉色大變,抬腿猛一蹬,他面前一張厚重的條桌斜飛過來。小劉一個旱地拔蔥,跳上桌面,順勢一棍砸下,那漢子一閃躲過,抄起條長凳橫掄在小劉腿上,小劉大叫一聲,栽在地下。我一聲怒吼,抓起一個沉重的銅臉盆砸了過去,那漢子躲閃不及,霎時頭破血流。我順勢一撐桌子,一個側(cè)空翻跳了過去,落地剎那雙腿齊出,把他狠狠蹬倒在地,就勢擰住他一條胳膊。身后忽地一陣勁風(fēng),一條硬物狠狠砸在我后背上,我眼前一黑,“噗”的一口鮮血噴了出來,接著頭頂一聲沉悶的槍響,一個壯碩的軀體重重砸倒在我身上……原來剛才是那黑大漢抄起長凳想要結(jié)果我,被馬三喜一槍打爆了腦袋。同時黑大漢的保鏢也撲過來,一刀扎進了馬三喜的右臂,鮮血噴涌而出。那保鏢舉刀又扎,被倒在地上的小劉一棍打碎腳踝骨,兩個斷腿的人又倒在地下扭成一團。這邊廂那黃臉漢抄起馬鞭,對著老白迎頭一鞭,老白雙手一抄,舉起那個被抓住的客棧伙計迎了上去,一鞭竟把那伙計打得慘叫一聲背過氣去。與此同時,金盛財?shù)牡蹲右餐边M了黃臉漢的后腰。黃臉漢那幾個同伙這會兒也回過味來,沖上來和巴特爾廝打;幾分鐘時間,屋里所有能動的東西都飛了起來,所有能砸爛的東西都砸了個稀爛,連結(jié)實的房門也被硬撞下來一扇。
屋里敵人拼命掙扎,要說那特務(wù)的中校肩章還真不是塞錢塞出來的,他精通格斗,身手了得,又急于脫身突圍。所以拳腳齊出,招招致命,以一對二,像瘋狗一樣和我們玩了命,我和馬三喜都帶著傷,力不從心,一時間根本制服不了他,危機關(guān)頭,只能舍命一搏;趁那特務(wù)往前猛撲,我往后一挫身子,借著勁一下跳起來,整個人在空中橫過來向那特務(wù)猛撞過去,把他撞得連翻幾個跟斗。馬三喜大步跟進,伸手就抓他的咽喉;沒承想那家伙忽地一個鯉魚打挺又蹦了起來,手里還多了一支“掌心雷”(短管左輪槍)對著馬三喜就是一槍。“嗖”的一聲,趕過來的金盛財把刀子猛擲過來,正砸在槍上,子彈砰的一聲射上房頂。我們緊跟著一人一腳,把他踹倒在炕上。他就地一滾,一個魚躍前滾翻,競撞爛大木窗。滾落到院里爬起來跑了。我剛要跟著跳下,被老巴一把拉住,“別追,他跑不了。”果然,院里立刻傳來群狗狂吠撕咬和救命的慘叫。原來蒙地的大狗晚上都散在院里防賊防狼,只要發(fā)現(xiàn)陌生人,一群狗立刻撲上去亂撕亂咬。那特務(wù)不知蒙地的習(xí)俗,只想著跳窗逃命,沒承想一下落到了惡狗嘴里。老巴和老白抄起打狗棍沖了出去,不一會兒就把那個渾身是血被咬得半死的家伙拖了進來。
后來的事情就有些戲劇性。天還沒亮,孫寡婦就溜過來打探消息。看到那一地狼藉和尸體,立刻呼天搶地大鬧起來,口口聲聲讓我們賠償她的損失。還嚷嚷著要去報官。我們告訴她,如果她把“土客”存放的貨物交出來,就留給她千斤重的一馱貨做補償。原以為這個老江湖還要講點黑道上的義氣死不開口呢,沒想到她連眼皮都沒眨一下就帶著我們?nèi)チ怂牡亟选T谀抢镂覀冋业搅舜鬅煛屩Ш筒卦谒幤防锏碾娕_,但怎么也找不到密碼本……
天色大亮,我們知道這里還是敵占區(qū),不宜久留;準備留下老白繼續(xù)查找,其余押著捆好的俘虜先撤。孫寡婦又奔過來了,口口聲聲要求我們把她兒子留下。“你兒子?”這會兒我們可真蒙了,孫寡婦一指王冬,“我昨天晚上才認得干兒子,他還答應(yīng)送我30塊大洋呢,你把他抓走了,我找誰要錢去?”孫寡婦兩手拉住我的馬韁,往地下一倒,兩腿亂蹬。一臉鼻涕眼淚的放聲干嚎。面對這個“滾刀肉”,我突然意識到什么,怒喝道:“孫寡婦,他給你錢,是讓你給他藏東西吧?”孫寡婦的干嚎戛然而止,翻著兩只肉泡眼一聲不吭。老白往地下狠狠抽了一鞭,“說!”她吞吞吐吐。“就……就給……了一個……小包。”在我們的“威逼”下,她終于從腰里掏出一個裹得嚴嚴的油布包,打開一看。里邊正是一個小巧精致的皮面本……趁我們?nèi)褙炞⒌胤疵艽a本,旁邊的孫寡婦竟偷偷拉上我們一峰最壯的駱駝悄然不見了蹤影……
后來,王冬交代了前后經(jīng)過。他出發(fā)時,包頭的軍統(tǒng)通過關(guān)系找到了那群“土客”,把他假扮成駝夫塞了進去,那群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到了客棧。他很快就看出我們是群假扮的商人。為防萬一,他許以重金,把最要緊的密碼本轉(zhuǎn)移給孫寡婦保管一夜。后來我們那一番“黑吃黑”的表演讓他信以為真,正要出來“認親”,卻猛然意識到不對,他潛伏的任務(wù)是絕密的,并沒通知寧夏的軍統(tǒng),對方怎么會派人出來接他?小劉一說話,就更證實了他的判斷,于是只好跟我們拼個魚死網(wǎng)破……他哀嘆道,在軍統(tǒng)闖蕩了20年從未失過手,沒想到機關(guān)算盡,卻栽在我們這幾個土八路的手里……
責任編輯:李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