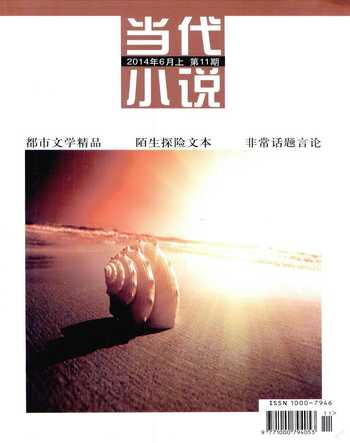郝莊那人
程相崧
1
程富淵沒有個兒子,這新近讓他愁得不行。
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兒了,要愁,早就該愁。可大閨女小玲都已經嫁了人,二閨女小惠也長到十八九了。這些年里,他從來沒有為這事兒這樣愁過。這些天,他卻忽然日怪地愁起來了。他的理由是,從前自個兒活蹦亂跳的,用不著為這事兒操心,也沒閑心為這事兒操心。現在突然地病下來了,一病下,就有工夫好好想想這件事兒了。
他不知道得的病叫啥名兒,卻能感覺到這病勁兒大得很,牛性得很。沖過來一下子就把他撂倒了。他覺得自己就像個正站在石板路上看光景的人,冷不防一下讓他摔在地上,“當啷”一聲,腦袋就啃了地,渾身也散了架子。他眼冒金花,站都站不起來了。那病卻還不肯放過他,撂倒之后還坐在他身上,拿腚暾他,暾得他喘都喘不過氣兒來。程富淵得病是在農歷的四月間,正是將要收獲大蒜(這里年年、家家都要種蒜)的季節。程富淵心想,沒料想的,眼看著就要收大蒜了,俺卻病下了。俺的個娘親,這可咋整哩?立夏就要拔蒜薹,小滿就要挖蒜頭兒,就這樣死豬一樣躺在床上,咋能行喲?
不行又有啥辦法?他一開始是想好好看的。他盤算著,看好了,還有好多事兒等著人做哩。可是。金鄉縣人民醫院的專家卻跟他說,你這就是個慢病,只要靜心養著,沒啥事,吃好喝好,一時半會兒就算想死還死不了。死不了是死不了,可想跟從前一樣拾起來身子。再到地里去做活兒,那是想也別想了。你得的這是個富貴病。以后一輩子都不用再干活了。他聽醫生說完這些話,心想,住不住院也沒大意思,便讓女人抓了些藥,用地板車把他拉回家里來了。回來之后,一天到晚被女人跟二閨女小惠伺候著。程富淵有時候就想,若不是半個身子木木的沒有感覺。若不是一張嘴歪歪扭扭地說不清個囫圇話,這日子恣意得也賽過神仙了。在床上躺了幾天,女人就又給他買了把躺椅,竹子的,能折疊和放開的那種。吃完飯女人就把那躺椅放在院子里或者院門口,把他架上去。他覺得躺在躺椅上比躺在床上強多了,至少不知道的人遠遠地看過來,看不出他是個病人,還以為他是躺在那兒恣兒哩。可恣兒哪有這樣恣兒的?一躺下就沒個頭兒啦。他覺得。再好的事兒一天到晚弄也就沒意思了。別的不說,就說跟女人做的那個事兒吧,一天到晚弄也是個夠,更別提一天到晚總在椅子上坐著。
從前地里的活計,都是他操心出力來弄,現在躺在椅子上,自然還是想著地里的事兒。他女人黑女雖然這些年地里的啥活兒也跟著干,可每一件都是他事先計劃好安排好的。啥時候犁地,啥時候澆水,啥時候種蒜,啥時候打藥,啥時候拔蒜薹,啥時候挖蒜頭,她不需要動腦筋,也從來沒有操過心,跟著他干就行了。他從來沒想到過自己會有一天做不動了。會有一天連句話也說不清白。現在他不行了,讓女人一個人謀劃,他還真是擔心她會想不周全。二閨女小惠哩?就更不用提了。這女娃兒一年前才從中學下學回來,農田里的活兒她還任啥不會哩。
太突然了。這病來得太突然了。
這時候,似乎才顯出一個男娃娃兒在家里的重要來了。想想,他家里女娃兒倒有兩個,大的小玲嫁出去了,婆家在五里外的郝莊;二的小惠呢,連媒還沒有說就。家里缺的就是個男娃兒嘛。如果家里有個男娃——假如小玲是個男娃吧。一個已經娶了媳婦成家立業的男人——自然能頂起來一個家。退一步講,就算小玲是個女的,換成小惠是個男娃兒,十八九的半大孩子,也一準能把自己肩上的這條擔子接過去了。可惜的是,倆人都不是男娃。
女人黑女不想給他心里添愁煩。哭也到地里沒人的旮旯去哭。從地里回來,臉上還帶著隱隱的笑影兒。她說,地里的活計不用你來擔心,雖然不會計劃,不會安排。好在跟人家一樣種的都是大蒜,人家啥時候干啥,咱也跟著干啥。話雖這么說,他知道女人只不過寬他的心罷了。有些活計雖然可以計劃到,卻未必能干得來。就拿給地澆水來說吧,百十斤的水泵,就不是女人能弄動的。拿著老虎鉗子接電,膽小的女人也有些做不來。幸好,這年該澆地的時候,小惠去郝莊把那人叫來了。那人來家幫著忙活了兩天,才把拔蒜薹前的那一遍水澆了。
說實在的,一開始程富淵簡直把郝莊那人給忘了。為啥會這樣哩?他想,莫非自個兒是打心里把他當成了外人?要說,那個人也不算外人——可不算外人。又該算啥人哩?他有些說不清。郝莊那人是他的大女婿,是農田里的一把好手,干啥有個啥樣子。這年,蒜薹沒有老在地里,蒜頭也并沒有爛在地里,說起來全是郝莊那人的功勞哩。其實,他大女婿有名有姓,他不知道這些年家里人為啥從不叫他的名字。而用“郝莊那人”來代替。仿佛給農藥取名666,給麥種取名4531,都是個代號。過去從來沒想過這個問題,現在想想,許是那人來相親那天。二閨女從街上跑回來報信兒,一邊跑一邊喊著:“郝莊那人來了,郝莊那人來了”,便讓他有了這么個奇怪的外號兒。說實在的,頭一次見面,他對這個未來的女婿卻并不怎么中意。二十來歲的半大孩子,卻蓄了一臉的胡子。瞅上去比他還要老成一些。他第一眼就沒看中。媒人領著孩子走了之后,他沒有明確說不行,但態度總有些消極。沒想到的是,小玲卻非常滿意。明里暗里地交往了幾回,一來二去,非要嫁給他不可。女大不中留,嫁就嫁了吧。結婚之后,這絡腮胡子在干活兒上倒沒讓他失望,并不是他原來想象中的懶漢二流子。
今年的蒜季,多虧了郝莊那人的幫忙。一提這個事兒,黑女就一個勁兒地贊嘆,說這個女婿真是比兒子還強。不但女人這樣說,村里人也這樣說。平素里,村里人吃了飯都要在程富淵家院門口的那棵大榕花樹下涼快。村里人在那兒乘涼,程富淵也躺在那里聽他們說話。大家都贊嘆說:黑女(富淵癱瘓之后,村人提到這個家時,一家之長也不知不覺變成了黑女),你命真好,攤上了個勤快又能干的好女婿。
程富淵坐在那里不說話,心里卻是美的。
如果村里人都說這樣的話。這事兒也就沒了。程富淵心里也就沒啥煩惱了。可巧是那天,村里一臉皺巴皮兒又總是在喪禮上問些事兒的那個老人f他是村里的大老知,即主持安排喪葬婚禮等事兒的人)卻說了一句話,說得程富淵心里怪不痛快。那老人說啥哩?那老人說:
“女婿再好,有時候總不頂兒子的用。”
程富淵心里一動,沒有說話。
“咋說?”村里有人似乎沒有聽清白,又似乎聽清白了,卻并不贊同那話,所以打問道。
皺巴臉皮仿佛覺著這問題不屑回答,咳出一口痰吐在地上,才不緊不慢地說:“譬如說吧,老人走了,啟坑打穴的時候。第一锨的血土,又有誰能替兒子挖的?出殯的時候,要摔老盆子了。又有誰能替兒子摔的?”
人們緘默了。
“這事兒在別的村,也都不成個問題。懂規矩的人少,沒這些講究。可咱們程莊咋能跟他們一樣哩?咱是宋朝大儒程顥、程頤的后人,跟別的村兒一樣,那多讓人笑話?村里建著供奉兩位夫子的祠堂,那本自北宋一直延續下來的家譜。就在村里的二程祠里擺放著,足足幾十卷,每一卷比方磚還要厚。過年的時候,你們不也,都去看過哩?如果在那部家譜里你后繼無人,你咋有臉入土見自己的祖宗哩?”
人們聽了皺巴臉皮這一番似乎乘勝追擊的話,都低著頭到一邊兒思索去了。
從那天開始,程富淵就覺得。有些從前認為眼下根本不用想的事兒,現在該好好地想一下了。
是的。地里的活兒郝莊那人是能幫著做不少,可女婿畢竟只是女婿,有些地方就是代替不了兒子。
村里的那個大老知那天說得對,人死了之后,選好了墳地,都是要讓兒子來踏踏血地。挖上一锨頭血土的。在程莊,如果沒個兒子,那抔血土誰來給你挖哩?
2
這件事兒也并不是沒有解決辦法的。
按照程莊老輩人的說法,如果沒有子嗣,想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還不止一條。其中之一就是過繼一個兒子。這個方法很簡單,在同宗里找一個侄子,兄弟家的可以。叔輩兄弟家的也可以。約集齊對方的父母跟族里有威望的老人,說好在你百年之后他給你挖血土,給你摔老盆。你撇下的家產遺物呢,也都歸他所有。當然,除此之外。在老人健在的時候,雙方還有如同親生父子般的撫養及贍養義務。雙方簽字畫押,見證人也按上手印,這事兒便算談妥。談妥之后,一千人便到家祠給二程先祖磕頭。舉行儀式,打開家譜,在你名下寫上過繼的這孩子的名字,就算是你兒子了。這個情況雖然普遍,但更適合那些沒兒沒女的老光棍兒。如果沒有兒子,卻有女兒,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招養老女婿,也即入贅。
這個事體,程富淵打心里早就盤算過,這兩個辦法,只要拿到一處一比較,就能輕易分出好壞。過繼一個,不是自己的孩娃兒,卻要在死后把財產分給他,總沒有招一個劃算。那樣的話,家產等于說是給了閨女家,并沒有跑到外面去。他從前是沒怎么認真地考慮過這個問題,若不然,當初把郝莊那人入贅過來,又會過日子,又能干活兒,倒是一件挺美的事兒。當然,現在說這都晚了,眼下可以考慮的就剩下小惠。
從那天開始,程富淵跟黑女就開始張羅著請媒人來給女兒小惠提親。這里的慣俗,在兒女的婚事兒上,總是女方家里矜持些,男方家里積極些。都是男方請了媒人到女方提親。富淵兩口子為了給小惠及早找個合適的人兒,就表現得有些積極,把這習慣反了過來。他們找了好幾個媒人,媒人也的確盡心盡力地給張羅了幾個半大孩子。有些孩子一聽說要入贅,就散鳥尿了,見也不見。有些孩子雖然一開始愿意見見,可一聽說未來的老丈人是個癱子,是個花錢如流水的藥罐子。就覺著以后一準沒啥好日子過,也就借故推脫了。再后來,終于介紹成了一個。男娃兒十九歲,人很老實。在見面兒之前,媒人跟他說結了婚要到女方家里來過活。他也同意。這樣交往了一二十天,富淵跟黑女兩口子覺得差不多了,就拾掇了些飯菜,把那孩子叫到家里來。族里幾個上歲數的也都請到場,一起吃了頓飯。吃完了飯,黑女跟小惠收拾干凈碗筷,端上茶來,幾個人陪新女婿喝著茶,說著話兒。
“你跟小惠成了親,你就是我們老程家的兒子。”村里一臉皺巴皮兒的那個老人先開口說。
“那是,那是。”那半大孩子說。
“富淵呢,是沒有男娃兒,等他百年之后,血土就讓你挖,老盆子,也讓你摔。”
那半大孩子又是點了點頭。
“有一條,你姓兒要跟我們的姓兒,姓程。”
這回,那半大孩子沒有點頭,而是不解意地盯著眾人。
這也難怪,入贅歸入贅,別的地方的入贅可都沒有改姓這一條兒。不但女婿不改姓,將來生出娃兒,也是跟爹娘誰的姓兒都可以。可程莊人覺得。宋朝理學大儒二程的后人,怎能跟別的村兒一樣?改是一定要改,不但要改,能讓他姓程,能讓他用這個“程”字,也已經是對他的恩典了。
“招到村里來,眼下最要緊的就是要跟咱的程姓嘛!”皺巴皮老人瞪著小黃眼睛說,“你沒聽清白?咱程家老祖宗是宋朝的二程,讓你姓程,多榮光哩。”
“是哩,是哩,咱的姓多好,”另一個村人說,“咱是一個程哩!成成成成成,不用說。這事兒一說也準‘成…。
那孩子愣了愣,仿佛并不知曉大家說的這個似乎頗為重要的“二程”是誰,也不知道這個“二程”跟他能扯上啥干系。一群人看那孩子不說話,都覺得這事兒約摸有門。越發七嘴八舌起勁兒地說起來。讓誰也沒想到的是,說著說著,那屁孩子竟然抽抽搭搭地哭開了。他邊哭還邊把兩手夾在褲襠里,緊緊地夾著。像是別個要拿刀割他的命根子一樣。
人們忽然不說話了,盯著孩子,半天才有一個人說:
“不愿意就不愿意,哭個尿哩。”
這樣的結果,是任誰也沒有想到的。讓他姓“程”,按說這是多好的事兒哩,卻并沒有辦成。這《百家姓》里,難不成還有比程更好的姓嗎?那孩娃兒回去第二天,就讓媒人捎來信兒,說要退婚,散茄子了。對于這件事兒,村里許多人都想不清白。幾個老人經歷事兒多,琢磨了半天。才開解說,這半大孩子雖然性子綿軟,心里頭卻是個倔驢子。嫁了這憨熊,日后準也沒個好過。姓程多好,咱程家祖上是宋朝的二程,大儒的后人,臉上多榮光哩。
不久之后,家里就又給小惠介紹了一個。這孩子五大三粗,雖然沒上回那個文靜,也沒上回那個好看,卻的確有把子力氣。那回小惠喊他來幫著拉糞車,糞車裝得都冒了尖兒,他還嚷嚷著讓裝哩。他拉著這大約也只有牲口能拉得動的幾百斤的糞車,還輕松地吹起口哨哩。這半大孩子來家里幫著干了幾天的活兒。家里人對他都很滿意。
這事兒都毀在幾個娘們兒身上。
那天,那半大孩子來幫小惠鋤地,跟小惠一前一后,扛著鋤頭走到半路。村里幾個女人就跟他鬧著玩兒。鬧著鬧著,一個女人就說,嫁到村里來,你就能姓程哩。這女人說這話的意思本是給他透露一個好消息。沒想到的是,這女人剛一提改姓的事兒。那孩子就惱了。
“站不改名。坐不改姓!”那半大孩子說。
“改個姓兒算啥?”女人拿眼瞅瞅小惠,“能有個女人晚上給暖被窩兒,讓我改啥姓我改啥姓。”
“啥女人不女人的?沒女人照樣弄得成!”那半大孩子說,“不日人日狗,省下錢喝酒。”
女人們聽這半大孩子的話,似乎有些二桿子的味道。
女人們還沒來得及弄太清白,沒想到那半大孩子說完這話,竟然就從肩膀上撂下鋤頭。撇下一群瞠目結舌的女人,轉過身一闖一闖地滾蛋去了。
這是啥人喲,這是他媽的啥人喲!
小惠回到家,捂著被子就哭了三天。
村里人都不解,說改個姓兒就能要他的命嗎?更何況改了后不是讓他姓別的啥。是讓他姓程哩!天底下人麻麻地跟螞蟻一般多,能有多少人有幸姓上這個程哩?大家滿肚子疑惑地把這荒誕事兒學給皺巴臉老人,老人聽了之后,抿了口茶水說:
“當個程家人,那是八輩子榮光的事兒哩。若不是老輩里積了陰德。這輩子咋能攤上這樣的好事體哩?這操蛋的毛孩子,真是不懂個尿!”
這幾日玉米地里的草長得膝蓋高,小惠兒原說好了讓那半大孩子幫著來割草。人家這一走,草就割不成了。
小惠就又去叫她的姐夫——郝莊那人。
3
程莊人弄不清白的是。雖然程姓甚好,雖然改成程姓也甚好,可那些半大孩子就是不依。一次不成兩次不成,小惠的婚事兒也就這樣擱下了。
農田里的活計是不等人的,挖完蒜之后,棉花、玉米一天天地往上躥個子。給玉米上肥料的時候,郝莊那人來過幾次,忙了幾天,給棉花打農藥的時候,郝莊那人又來過幾次。郝莊那人從前來家的時候,是有些拘謹的。讓他坐他就說不累,讓他喝水他就說不渴不渴。仿佛總是把自己當成了個客人。后來,郝莊那人來家勤了,也就不把自己當外人了。在地里干完活兒,回家來之后。接過小惠遞過來的洗臉盆子跟毛巾,扒光了膀子就蹲在那里洗。洗完了頭臉,還要洗胸毛,洗胳肢窩兒。這些都洗完之后,就旁若無人地坐在桌子前吃飯。也不推說不餓。也不客氣地說你們先吃,你們先吃。仿佛這里就是他的家一樣。有時候,程富淵看著看著,就感覺氣得不行。氣歸氣,氣完之后,連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仿佛為這事兒不該生氣似的。也是,有時候他就會想,如果這人是他的兒子。不就該是這個樣子嗎?可這畢竟不是兒子,他就覺得稍微有些別扭。
程富淵只是覺得別扭,而村里人呢,就漸漸覺出點兒什么其他的意思來了。天旱的時候,鄉灌電站里給農田電網送了電,各家就爭著占井澆地。有一家人清晨拉著水泵去地里早,回來之后就抵著頭兒跟鄰居小聲說一件有意思的事兒。這事兒說來也平常,那就是她看見小惠跟她姐夫在地頭澆水,小惠在畦埂子上蹲著。身上披著她姐夫的褂子。
這事兒仔細想想,其實也平常得很。郝莊那人自己也有地,也要在這幾天澆水,所以,白天就沒有工夫,晚上才有時間過來幫老丈人家澆。澆地的活兒一個人干不了,尤其是晚上,更需要個幫手,所以小惠就跟著幫幫忙兒,照照手電啥的。澆了一晚上地,累得不行,一早晨的時候,兩人就蹲在地頭休息。因為露水重,天氣冷,郝莊那人便說,我脫了褂子給你披吧。小惠推讓了幾次,看姐夫誠懇,便接過來披在了身上。如果說有啥不對的地方,也許他們為了防備別人的閑話,應該避避人。在有人可能看見的時候,把褂子脫下來還回去。當然,也許他們原本是避著人的,可是早晨霧氣重,遠處的小徑在霧中若隱若現,所以在看見人來的時候,就沒來得及。
可是呢,這事兒經那女人的講述,就有些不同尋常了。女人說。晚上冷成那個樣兒。光披個褂子哪行?白天就披個褂子,晚上還不得摟抱到一處?女人還說,她往前走著走著。就看見小惠踩在畦埂子上的白腳丫了。藍色涼鞋里露著粉嘟嘟的腳趾頭。那腳丫兒那個嫩樣兒,讓人恨不得放嘴里吮。郝莊那人能把持住?就算能,女人說她走過去的時候,還悄悄回頭瞅了一眼,瞅見小惠蹲在那里的兩個大腚盤兒,圓溜溜地像布口袋里裝著的兩個籃球哩!郝莊那人看不見?他眼瞎哩?
人們就說,倆人不能沒點兒啥事兒。
這話傳著傳著,就傳到了程富淵的耳朵里。程富淵躺在那里不能動,就有些英雄氣短的意思。他把個臉漲巴得通紅,眼珠子血呲呼啦地盯著他和她,嘴里唔哩哇啦地亂叫。他想,日你母,日你們的母!你咋能披著你姐夫的褂子哩?你咋能脫了褂子讓你小姨子披哩?富淵伸出那個稍微能活動的胳膊朝前狠狠地一抓,抓住了一股空氣。他恨恨地想,如果能夠著,我一準一把把那褂子給扯將下來,然后再往那不要臉的女子臉上劈臉扇兩個耳光。
那件事兒之后,人們都說,那狗熊是嘗到了腥頭兒哩。要不然,在拾棉花的時候,明明活兒不重,也沒見小惠去叫。郝莊那人竟然自己就來了哩。來了之后,就跟小惠一塊兒去地里拾棉花哩。郝莊那人用自行車馱著小惠下地,倆人有說有笑。不知道的人看上去還以為是小兩口哩。村里人仔細盯著,心想,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早晚讓我逮住。果不其然,有一次,就有人發現,他給小惠擠棉花包的時候,摟住她的腰,摟了好大會兒,才松開哩。日娘的,擠個棉花包用花那么長時間?
“狗日的,打我們老程家女人的主意哩!”村里許多人憤憤地說著。牙縫里濺出些酸水水。
人們就觀察得越發仔細了。
不久之后。果然,他們就又讓人給碰見了一回。那是掰玉米的時候,郝莊那人跟小惠從玉米地里一前一后地出來,當著小姨子的面兒,郝莊那人扛著滿登登一大袋子玉米棒兒。上半身卻布絲兒不掛,就赤著光光的脊梁哩。村里人看到這個場景,既生氣,又覺得不解氣。心想,若是他們真做了啥,這會兒也已經做完了,沒有能夠親見。日娘的,真是后悔沒有早來一步,沒有及早沖進玉米地里逮個正著。
村里人想要逮個正著,沒想到剛過幾天,就果真逮了個“現行”。那一日,幾個人在富淵家門口說話,郝莊那人也在。小惠是剛去馬廟集買了蘋果回來。一塑料袋的蘋果,紅紅的,饞得人淌口水。一圈兒的人,誰不想咬一口哩?可是,小惠她拿出來一個在壓水井前洗了洗,口里說吃哇吃哇,手上卻頭一個就遞給她姐夫哩。她難道不曉得避人?她是忘了情哩!日娘的,弄了一圈兒人一個個大長臉。
“可憐啊,富淵兄弟!”村人說。
“狗日的倒會趁火打劫哩。”村人又說。
“不怪人家!”另一個人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哩。”
“咱祖宗老早就說過‘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話,”又有人說,“咱程家門就沒出過這樣閨女。”
“程家歷代讀書識禮,出了這樣的。早該吊起來打死了。”
“切!”有人就這樣叫了一聲,不知是恨,還是在罵。
這樣說著說著,村里人仿佛覺得越來越過癮了。
村里的那個皺巴臉老人一開始是沉靜而安詳地捋著山羊胡子,捋著捋著,卻忽然大喊了一聲:
“殺!”
村人都讓皺巴臉嚇得不輕,半天沒有再說話。
4
程富淵聽了女兒跟女婿的這些風言風語,時時就想,這病既然好不了,還不如死了干凈哩。他這樣想著想著,沒過兩個月,果真就死了。也許,連他自己到死也沒弄清白,是因為他這樣想才死了呢。還是因為他要死了,才會生出這樣的想法。
相比之下。倒是村里人弄得更明了些。想得更清白些。村人都說,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富淵是讓小惠跟郝莊那人給氣死的哩!
程富淵的死讓村里人感覺有些突然。有些措手不及。那意思仿佛是,光顧著看郝莊那人跟小惠的熱鬧,沒想到富淵就嫌人冷落他了。就死尿了。
在程富淵死屎了之后,由皺巴臉牽頭兒,村里人張羅著給他踏墳打穴,料理后事的時候,才發現麻煩來了,到現今給富淵挖血土的人還沒有找下哩。村里幾個上歲數的老人,吃掉幾支煙之后,說這事兒也好辦。咱村里的輩分是“懷、玉、秀、淵、元、相、傳、大、千、年”,富淵是淵字輩兒,從村里元字輩里找下幾個年輕娃兒,給他叔挖血土摔盆子。
一會兒,幾個元字輩兒的娃兒都找來了,問了一陣,竟然一個都不肯。有的說,窮家爛舍的,誰給他挖血土摔盆子哩?圖個啥?有的說,就他家,除了個小惠,還有啥值錢的東西?——就這個小惠,也還是只能干看著過過眼癮。
“我給叔挖!”郝莊那人說。
村里幾個老人瞅了瞅他,在心里都畫了個問號。心想,眼下也只有讓他挖了。話說回來,郝莊那人是女婿,該不著這個。莫非,他是想借這個機會,接老丈人家的財產?
日娘的,野心不小!幾個老人一商量。說這如意算盤不能讓他打成。所以,他們很快合計出了拒絕他的理由一、二、三、四。然后推舉出一個能說會道的代表,去跟他談了。
“挖是可以,可你能不能繼承他家的財產,還得另說。”
“行!”郝莊那人一把鼻涕一把淚地說。
日尿的,沒想到竟這么容易。負責跟郝莊那人談話的老人愣了半天,才清白過來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他一邊回身一邊憤憤地嘟噥了一句:日娘的!一肚子的話都沒讓人說,一身的本事都沒用上。日娘的!那意思仿佛頗為委屈。
程富淵的葬禮,村人都仔細看著那女婿有啥表現,小玲有啥表現,還有小惠兒有啥表現。仿佛是,任誰有啥差池讓人看出來,等著好好收拾舅子的!沒想到的是,一連三天下來,他們始終也沒啥把柄落到人的手里。幸好的是,在第三天傍晚出殯下葬的時候,人們就在悄悄傳說著一個大秘密了。
這個秘密就是,剛才,據在禮賬屋里幫忙的人說,郝莊那人給丈人上禮竟然上了兩千哩!
兩千塊,一提到這個數兒,人們都有些驚異。按照程莊的規矩,別人家女婿給丈人上禮都是一千。他卻上了兩千,足足是別個的二倍哩。這樣琢磨著,許多人從心里都感覺有些慚愧了。心說,沒想到呀沒想到,沒想到這雜種競這樣有良心?沒想到這么久的時間,大家竟然錯怪了他!同時呢,村里別個有女婿的人家,也似乎都有些因為嫉妒而憤憤然了。
“兩千算啥,不還有小惠哩?”不一會兒。有人恍然大悟地道。
冷不丁的,像是炸響了一個大雷。嗩吶不響了,日頭也看不見了。人們都感覺身上的血一起往頭上涌。日娘的,剛才還以為他是個憨厚老實的人,原來狗日的貓膩藏在這里頭哩。這花花腸子繞繞得那個難受勁兒。村里許多男人清白過來之后都覺得有些憤憤不平了。心想,亂了綱常了!亂了綱常了!暗里弄也就算了。俺程家爺們也就忍了。你還這么光明正大地欺負起人來了。
這么晚才弄清白這小子的花樣,村里人覺得實在是讓他侮辱了智商,實在是羞臊得要死。
清白得很,這事兒清白得很哩!他竟然一個人交了兩個閨女的禮錢。真是太欺負人了!當程家門沒人了嗎?當程家門都死光了嗎?真是太氣人了!人們都覺得憋屈得要命,心說奶奶的,真是讓他辱沒了咱程家的老先人哩。
郝莊那人在那里跪著,忽然就有一個村人實在忍不過,沖過去一下子把他按倒了。
“打他!”
郝莊那人就被打倒在地了。
“干啥打他哩?”小玲跟小惠跪在那里,似乎還有些沒弄清白。
“在富淵叔的面前。狠狠收拾收拾這舅子!”村里人不理會她姐倆,只顧揪著那男的痛罵道。
小玲沒有弄清白為啥要打,但是她也不敢阻攔。因為老程家在喪事兒上有啥規矩,誰能說得準哩?難不成岳父的葬禮上就有女婿要挨打的風俗?那也說不定!在這幾天里,跟別個村里不同的風俗禮儀,他們是也領教了不少了。比如給老人穿壽衣前,至親都要先吃一口灰土;比如在起棺出殯前,晚輩無論男女都要解開懷趴在地上給爹娘“暖路”……小玲心里想,打就打吧,只要不打太狠。
郝莊那人是在完全沒有反應過來怎么回事兒的時候被一磚頭拍倒在地上的,接著就是鐵锨、棍棒……他一開始還叫喚,后來不叫了。
人們都累得氣喘吁吁,汗如雨下。
郝莊那人抱著腦袋,竟然又搖搖晃晃地站起來了。
“打是打,不要打頭!”小玲大喊一聲,用牙咬住了下嘴唇兒。
也許是因為聽到了小玲這話,有個人一棍子就狠狠照頭砸了下去,把郝莊那人一下子砸倒了。村里人都覺得,不怪別的,單單看那頭型像個掃帚頭兒。頭發也油光光的,就實在是該打!不打不解氣哩!郝莊那人跌在他老丈人的墳前,村人手里的鐵锨就往那人身上一陣亂拍。一邊拍一邊喘著粗氣叫道:
“日娘的,叫你拿兩千,叫你拿兩千!”
責任編輯:王方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