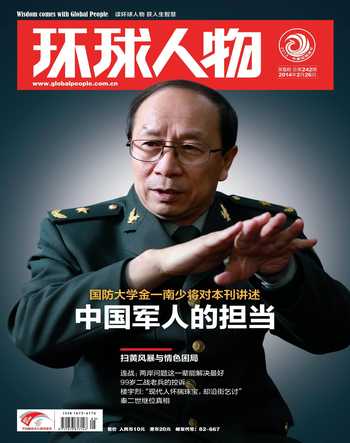吳曉波,從變革中解讀當下
趙敏

“如果不研究歷代經濟的變革,其實無法真正理解當前的中國。”這是寫在吳曉波新書《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封面上的一句話。
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說過:“人們可以用三種方式去研究經濟:通過理論、通過統計和通過歷史”。這些年,吳曉波正是通過研究企業史和經濟史的方式,來研究當下的經濟;通過研究官商博弈中歷史人物和國家的命運,來映射當今世界的潮起潮涌。
在這本書中,吳曉波由春秋時期的管仲變法開始,及至當代改革開放,敘述了2700多年的歷代經濟變革和工商變遷。
公元前7世紀管仲變法,實行“四民分業”和鹽鐵專營政策,使齊國成為當時實力最強大的國家,管仲的這種“尊重市場規律的國家干預主義”,被吳曉波稱為“古代的凱恩斯主義”;到漢武帝變法,獨尊儒術以達到全民思想控制,同時圍繞產業、流通和貨幣等進行的改革,吳曉波稱其為“頂層設計的集大成者”;隨后是王莽改制,那是第一個“社會主義者”的改革;及至盛唐,唐太宗以歷史上最小政府造就最強帝國;北宋后期王安石變法,算是帝制時期最后一次整體改革,東西方文明至此分道揚鑣。“在王安石時代,歐洲出現自由城市和自由大學,這具有分水嶺般的意義。自由城市催生自由的商業,自由的大學催生自由的思想,而自由的商業和自由的思想,又是人類文明走向現代社會的兩塊基石……相反,王安石變法卻空前強化了政府的管制能力。”讀到這里,似乎能聽到吳曉波發出一聲長嘆。
明清兩朝閉關鎖國,中國科技和經濟創新退化;洋務運動,中途夭折;之后的民國,經歷了一個極度自由的市場經濟運動和一個以“統制經濟”為名義的集權變革,但都以失敗告終。
1978年改革開放后,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體制上的羈絆又讓社會矛盾和經濟發展的前景充滿變數。吳曉波最后的結論認為: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經濟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場化為取向,維持“統一文化”為邊界,在民主法治與中央集權體制之間尋找平衡點的非西方式改革。而這次變革的時間長度很可能超過我們這一代人的生命。
看到這里,想必你已明白,這不是本單純的史書。在書的扉頁上,作者借托克維爾的話表達了本意:“我只能考慮當代主題。實際上公眾感興趣、我也感興趣的,只有我們這個時代的事。”
從歷史回到現實,一直是吳曉波寫作的初衷。也許他只是回望了一段不長的歷史,比如30年(《激蕩三十年》)、100年(《跌蕩一百年》),也可能是漫長的2000年(《浩蕩兩千年》),但他的目光總會回到當下。讀他的書,會讓糾結于現實的我們驀然驚醒——如果把當代社會放入歷史中考察,正發生的一切,似曾相識。每一次經濟變法,每一個繁華盛世,每一回改朝換代,都可進行前后印證和推導。
吳曉波曾多次在書中寫道:“中國需要向世界貢獻商業思想。”事實上,他的確為這個世界貢獻出了獨立而深邃的商業思想,他也被譽為這個時代最出色的財經作家。從2001年的《大敗局》,到2013年的《歷代經濟變革得失》,他證明了嚴肅的商業寫作也能夠躋身暢銷書行列。
吳曉波靠寫作擁有了財富,穩穩當當、自得其樂地與妻女棲居于杭州。他最讓人羨慕的正是真正擁有了知識分子的獨立。經濟上獨立自由,方才可人格上獨立自由。獨立后有選擇,有喜歡,有研究,有發現,還能傳播,對知識分子或追求成為獨立知識分子的人,可算是人生至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