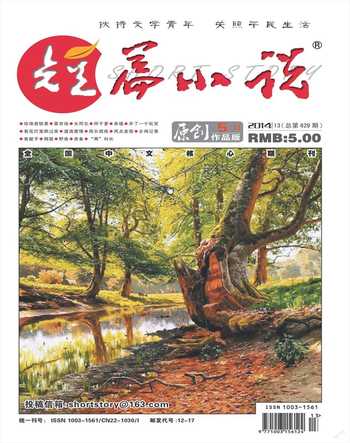從《秘訣》談尋根文學的精神影響
呂曉春
從20世紀初期開始,中國文學的發展是以現代化與民族化為中心的兩大方向,民族化是中國文學不斷追求的目標之一。就尋根文學而論,新時期追求民族化,將民族目的與意識體現得淋漓盡致,對民族化文學建設與發展影響深遠。本文淺析《秘訣》一文,從新時期文學的角度出發,研究當代小說中尋根文學的精神影響。
一
民族化目的與意識在新時期文學中有一個循序漸進的發展歷程。“文化大革命”的精神枷鎖被廢除以后,在起初的時間內,中國當代文學一直在歷史災難的反思與傷痕的揭露中徘徊不前,文學發展方向的確立也被擱淺。然而,一些作家在敏銳藝術感與強烈意識的驅使下,面對新時期的文學發展,很快適應并融入到了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發展當中,踏上了探索與思考現代化文學的道路。探索主要涵蓋兩個方面:其一,以馮驥才、高行健、茹志鵑、李陀、劉心武以及王萌等為代表的藝術家對西方藝術進行了研究,作為“偽現代派”的代表人物,希望通過實驗與借鑒表現手法的方式,在我國新時期文學中引入西方藝術,為當代文學拓展一片新的天地。其二,以林斤瀾、汪齊、鄧友梅以及劉紹棠等為代表的藝術家弘揚與回歸傳統文化,作為邊緣作家的代表,希望通過對民族化道路的探索,完成民族文學的現代化。
針對追求文化民族化,尋根作家做出了公開的表示,尋根作家將民族化作為對抗文化霸權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手段,韓少功認為中國不能建立“外國文學流派”,依靠模仿國外作品,應該建立具有特色的中國民族文學,在文化物質、文化藝術以及民族深層次的靈魂方面,我們的民族特色獨具一格,重鑄與鍍亮主要民族特色以及將現代觀念的熱能釋放出來是我們的職責所在。然而李杭育認為民族意識必須貫穿在中國文學當中。
然而,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進入21世紀后,當代小說的發展遇到了瓶頸,尤其是短篇小說,不知不覺進入到了一個較為尷尬的時期,在閱讀與寫作之間竟然出現了莫名其妙的齷齪。短篇小說乃至整個文學真實的寫照就是緘默。文學外部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制約,很顯然,在一定層面上對短篇小說產生了干擾,影響了短篇小說的生產活力,對短篇小說迅速捕捉畫面的力度、敏感度產生了制約。除此之外,由于在娛樂、物質、精神、文化迅猛轉型的數十年歷程中我們對自我生產狀態以及物質水準過于專注,自身新的文化標高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人們的興趣降低是由于閱讀興致與文化興趣的分割,這也是致使短篇小說市場下降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不奢求在時間上與空間上文學能夠立竿見影地改變和影響生活,至少要能夠在精神上舒緩壓力和凈化心靈,給我們一方心靈的凈土,一泓精神的甘泉。在這種緘默的樣態與困惑的情形下,我們發現這種文學正在孕育著新的生命。由于現如今作家寫作的審美視野與文學背景更為寬闊,我們發現,最具有素質的作家都在文學領域內堅持陣地,不斷寫作,以自己對文學的忠貞探索著磨難與困境,對生活中微妙的細節做著最為深刻的梳理。特別是短篇小說作家,在中國民族文學的歷史上用短篇小說留下了諸多不朽的業績。經典的短篇小說就如同數之不盡的紀念碑一般在文學之林屹立不倒。假如短篇小說作家清醒地發現這一點,就可以看到自己與大師之間的差距——在對世界與生活表達的境界與層面的差異。然而,在西方經典短篇小說中,中國當代作家對“物理”有著切身的體會與感受,這完全能夠表明在“世界文學”的譜系內中國當代作家有非常大的可能展開我們的寫作,是足以在世界短篇小說大師光環的影響下開拓一片新的土壤,創作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絢麗花朵。張煒曾經說,一個時代假若短篇小說不繁榮,那么這個時代必將會是浮躁的。作家的審美取向與創作定位在潛移默化中被時代價值觀所影響。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分散了讀者的興奮點,但是在整個社會中小說的分量已經遜于從前。
短篇小說的寫作在近代五六十年的光景中已經開拓了一片新的天地,已經呈現了美好的質地與諸多創新元素。在敘事方向上,諸多作家已經有了創新思路。當今文壇,提到羅恩·拉什、西蒙·范布伊、弗朗索瓦絲·薩岡、科爾姆·托賓、弗朗索瓦絲·薩岡等作家,都會讓人眼前一亮。在文學敘事上,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一個特點,就是對文本間的交叉互文不在沉湎,而是著重于文字與現實的糾纏。故事的虛構部分不再怪誕離奇,審視存在世界與生活的角度也不再輕率,進入存在世界與生活的觸覺也非常敏銳,以從容、自信的方式表達著自己的想法,將這個世界與生活中的質量、溫度、顏色以及氣味等表現得淋漓盡致,仿佛身臨其境。中國當代短篇小說同樣在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尋求著可能性。21世紀的到來使精神背景與文化背景都日趨開闊,我們發現,隨之而來也打開了作家的寫作視野,令人欣喜的是,給中國短篇小說帶來一個春天。作家們逐漸找到了與現實對話的方式,因此形成了形態各異的文學風格。作家們始終堅持在寫作的敘事上進行探索,所以諸多短篇小說在結構與構思上呈現出來非常巧妙的變化,將語言的可能性提升到了更深的層次。
六爺吃完后,抹抹嘴,丟下五塊錢,悄悄地
往門口走。
老五看見后,忙拿著錢,追到門口,把錢往
六爺口袋里一塞,說,六爺,拿著!你這樣不是
打我的臉嗎?
六爺推辭了一番,接過錢,朝老五笑笑,一
瘸一拐地走了。
老五的生意又慢慢地好了起來。
由此看出,一個作家進行寫作,其動機是由于不滿足于現實存在的世界。通過文字的形式,他要以思考或者對話方式進行重新建立。但是一個作家在敘述、文本以及形式上進行選擇策略時,通常就是他在感受現實生活的某種確證,或者是他們之間關系的象征、隱喻。在《秘訣》的作者葛昕旭的筆下,老五在給六爺端豆花的時候,對豆花、蘸碟等具體事物的刻畫以及老五與六爺的面部表情描寫,可以說是惟妙惟肖,卻又蘊涵著濃郁的生活氣息。當你的敘述不斷貼近生活,甚至于沉醉在生活中,在表達的時候孜孜不倦時,卻恍然發現這個空間竟然充滿了幽暗與朦朧。六爺給錢的時候,老五每次都是追到門口推脫一番,此時作者對兒子的反映進行了描述,非常貼近生活。然而短篇小說的敘述就是在前行中如此的義無反顧,有中生無或無中生有互相交替,才能使敘事成為藝術沖動,成為一個個動人的章節。《秘訣》通過描寫老五與兒子做生意的不同態度反映出來的結果簡單卻有著深刻的韻味,最終成為一個簡潔卻有著故事情節的事實。這些方式與途徑的實現必然可以讓作家自己的想象沿著地面飛翔。如蘇童所說,作家們眼中的世界就是沉重的一具軀體,小說家為了捕捉每個細節不停地圍著它奔跑,乃至于它的夢境也吸引了小說家們樂此不疲的敘述。但是對于虛構,人們有著各自的理解,有的作家果斷,有的作家則一籌莫展、扼腕嘆息。
六爺喝酒很慢,一頓飯要吃一個多小時。但
老五從不催六爺。六爺吃完后,抹抹嘴,丟下五塊錢,悄悄地往門口走。
老五看見后,忙拿著錢,追到門口,把錢往六爺口袋里一塞,說,六爺,拿著!你這樣不是打我的臉嗎?
六爺推辭了一番,最后搖搖頭,背著手,一瘸一拐地走了。
從這里可以看出,小說是文學敘述的根本所在,是一種語言的藝術。然而文體是通過語言的方式講述小說的整個敘事,是更為復雜的一個綜合性小說元素,是心靈集結后的外化,涵蓋了敘述方式以及結構的許多方面。文本可以將作家的個性風格和整體藝術彰顯出來。可以這樣理解,評價小說的好壞可以把文本與語言作為標準。以短篇小說的寫作方法與意義為出發點,從一定程度上講,我們可能將東西由外在變為內在,將探索心靈變為表達審美。短篇小說優秀作品的創作是作家精神、心性以及心智坐標系在存在世界或現實的一次靈動,是機緣般的宿命,在短篇小說中貫穿著作家的藝術感知力、空間感、情感、經歷、經驗,激情以及所有的虔誠,當他將故事與人物賦予自己的一切的時候,猶如宿命般的,有關世界將建立起一種全新的結構,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是文體變化與精神境界的集大成。一部短篇小說在作家筆下的誕生是既有寫作慣性以及小說觀念的一次顛覆、一個更新,像雷蒙·卡佛、西蒙,范布伊、博爾赫斯那樣,甚至完全可以說是在短篇小說中不斷開創新紀元。他們影響了“小說觀”在世界范圍的迅猛變化,并且發展為依照存在世界或者省份已有的生態,是由虛構故事、重情節轉變過去的,巧合而真實,敘事自然,精妙絕倫,情緒和節奏渾然天成。進而,短篇小說的結構從戲劇化向散文化發展,充分彰顯了短篇小說真正具有現代意義。
尋根文學有一點是需要得到充分贊同的,那就是在民族文學的道路上尋根作家們上下求索的精神非常值得贊揚,并且他們付出努力,最終實現了現代化與民族化的掛鉤,使民族化成為現代化的一部分。就中國當代文學而言,是不朽的業績,更是一份警醒,中國當代文學應該預防發展的片面化。民族文化特色的濃厚在追求民族化的尋根文學中完成能夠體現出來,新時期的當代文學代表了民族化追求的不朽篇章。盡管尋根文學的終結代表著文學民族化的瓦解,但自此,民族化的意識在中國當代文學中生根立足,并內化為中國當代文學的血肉,是自然和自在的狀態呈現。
[參考文獻]
[1]劉忠.“尋根文學”的精神譜系與現代視野[J].河北學刊,2006(03).
[2]鄧楠.中國尋根文學研究述評[J].中國文學研究,2006(04).
[3]程光煒,重評“尋根文學”[J].文藝研究,2005(06).
[4]楊位儉,守望民間的詩性情懷——關于王光東的文學批評[J].當代作家評論,2007(04).
[5]陳思和.“歷史一家族”民間敘事模式的創新嘗試[J].當代作家評論,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