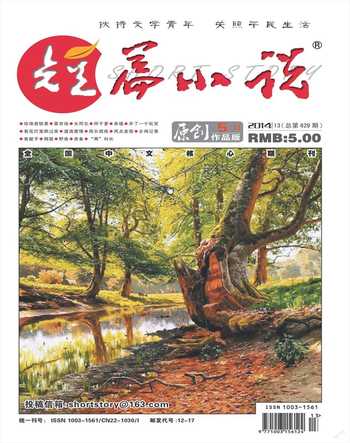余華小說的風格分析
王海艷
余華作為中國現當代小說的領軍人物之一,一度以《許三觀賣血記》贏得讀者和批評界的廣泛關注。但自1995年完成了這部作品之后,人們就沒有看到關于余華新作的消息,更多是他發表在《讀書》《收獲》上的隨筆,直到小說《兄弟》的誕生才讓讀者又將余華和長篇小說聯系在了一起。從1995年到2005年,余華從講述“許三觀賣血記”的殘酷社會終于轉到了“兄弟”之間的人性探討。他的小說創作究竟經歷了什么樣的變化?十年的砥礪對余華小說風格究竟有何影響?這都是筆者在本文中試圖解答的。
一、先鋒文學對余華文學風格的塑造
20世紀80年代,余華與馬原、蘇童、北村等人一起出現在中國當代文壇。他們為當時的文壇帶來了一股新風,以截然不同的表現對象和表現手法呈現了小說的新面貌,旋即引起了80年代文學改革的浪潮。當時的文學批評界曾對他們冠以名目繁多的稱謂,發展到現在,余華等人所掀起的文學浪潮已經成為中國當代文學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之一。我們應該認識到,任何一位作者在初登文壇之際都會嘗試著模仿某位或幾位作家的創作,力求從中獲得從事文學創作的不二法門。最終,人們意識到這一批作家的精神源頭來自于西方的先鋒文學,他們將先鋒的精神和先鋒的價值融入到中國文化的歷史背景,才最終孕育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先鋒文學。“只有在一種先鋒派已經不復存在,只有在它已經變成先鋒派的時候,只有在它已被‘大部隊的其他部隊趕上甚至超過的時候,人們才可能意識到曾經有過先鋒派。”
余華的文學創作正是中國早期先鋒派文學中極為重要的代表,從形式上而言,《十八歲出門運行》是余華嘗試先鋒寫作的開端。但是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之后,余華的創作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人們似乎很難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先鋒文學的蹤跡。取而代之的是《活著》《許三觀賣血記》《兄弟》等作品中涌動的人性元素,似乎余華的小說正在向傳統小說的模式回歸。我們應該努力從余華小說創作的本質層面進行分析,“余華這兩個階段的創作主要采用的都是主觀表現的方法以及抽象化、寓言化、陌生化的藝術手段,都放棄了對現實生活的模仿,竭力表達主觀上的真實,并一直不懈的拷問人性的本質,展現生存的困境”。
我們不能單純根據余華小說表現對象的差異就斷定他的創作風格發生了轉移,就本質層面而言,他依舊延續著先鋒派的創作思路。
在余華的筆下,對于現實世紀的描繪僅僅是他展現心靈世界思考的一種手段。當他逐漸意識到個體生命的經驗性獲得并不能真正理解客觀世界時,世界的“本質”就會被遮蓋起來。此時,我們必須努力回到每一個行為個體的內心深處,只有從那里去尋找獲得精神撫慰的力量才能幫助我們以更為真實的方式去感受世界,而這一切正好是余華小說一以貫之的奮斗目標。我們可以將余華的創作歸納到表現主義的范疇中加以考量,所不同的是他沒有遵循中國文學自五四運動之后的創作模式。在余華的作品中,我們往往找不到直觀可感的客觀描寫。他大膽地將心靈世界的刻畫與客觀現實的表現結合在一起,使得最終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文字在字里行間滲透著血的震撼。
中國讀者基本是在現實主義小說的氛圍中成長起來的,盡管現實遠比文學更為殘酷,但人們往往會忽視現實中存在的可怕一幕,更愿意相信文學塑造的恐怖景象。余華的小說就具有如此的審美效應。他在《許三觀賣血記》中對于賣血者、血頭的刻畫近乎血腥,的確是表現了中國社會真實,卻遠遠超越了人性的殘酷。從先鋒文學語境中走出來的余華學會了運用超越中國讀者的接受模式和理解范式的手段去展現人類的心靈世界。他在自己作品l中所表現的一切都是不能被當時的讀者和批評界所理解的,人們很容易將其定位為先鋒派。但究其本質而言,我們卻可以把余華的文學創作視為用表現主義的手段維系起來的客觀存在。
二、從川端康成到余華
中國的作家很多都是憑借著自己的勤奮、好學才取得今日的成就,他們往往不會將自己今日今時的地位歸結于天才的創造,這或許與中國的農耕文化創作有一定的關聯。在余華走向文學創作的漫長道路上,有兩個人曾先后對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們分別是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正如余華自己所說:“川端康成教會我寫作的基本方法。”
中國讀者對于川端康成的了解主要是從《雪國》開始的,在這樣一部滲透著日本文學傳統特征的作品中,川端康成獨有的婉約、傷感被中國讀者所認知,而這樣一種認真刻畫小說人物心靈世界的唯美主義表現方式卻是中國文學中少有的。在現實主義文學的時代浪潮中,中國的作家們更為熱衷于將自己筆下的世界與現實社會的波瀾壯闊聯系在一起。余華沒有按照這樣的模式去構筑自己的文學世界,我們可以在他早年的作品《星星》《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中感受到川端康成的痕跡。
余華對于琴聲的刻畫以及出現在他筆下的客觀自然界都是如此的靜謐、和諧、安寧。這一切都是中國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中沒有觸碰到的,他們似乎更多的是去追求一種現實生活在文學世界的延伸。這就為余華等作家從事先鋒文學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我們欣喜地看到,余華、馬原等人自由地馳騁在精神的原野之上。我們還可以在《月亮照著你,月亮照著我》中感受到久違的古典意味,在作者娓娓道來的緩慢節奏中,少女的心靈世界中極為細膩的情感被作者完全地表現了出來。少女的相思似乎讓人聯想起唐代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的靜謐。所不同的是,出現在余華筆下的世界抽離了時空的哲思,留下的僅僅是心靈世界的叩問而已。這就十分契合川端康成小說中一貫的審美原則。當然,我們并不是說余華的小說創作完全借鑒了川端康成的唯美式風格,作者本人也沒有將自己的創作等同川端康成在中國文學的延伸。
因此,從川端康成到余華,中國讀者感受到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壇最復雜的精神狀態。這是多種文藝思潮并存、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特殊時期,余華的小說和他同一時期的其他作家所創作的作品一樣,是帶著傷痕文學給予的淡淡的憂傷、反思文學創造的深刻的哲思、鄉土文學帶來的濃烈的愁思,將所有的一切融為一爐。此時我們就必須要承認余華的高明之處了,他沒有將自己混同于其他作家,而是適度地加入了新的審美元素。這就是前文提及的川端康成等外籍作家,異域文明帶給余華的不僅是他山之石的奇彩,更是運用他們“可以攻玉”的奇效。
三、早年的閱讀經歷與余華文學創作
余華的文學創作之路是如此的漫長、曲折,這與他本人早年的閱讀經歷密不可分。根據作者自己的講述,他自幼喜愛文學,曾經用較長的時間閱讀了數量十分龐大的作品,而且主要是外國作家的作品。在1982年開始嘗試文學創作之時,余華就很自然地將自己的創作與外國作家聯系在一起。沒有一位作家是可以完全憑借著自己的靈感完成文學創作的,在走上文學創作道路之前,必要的步驟之一就是大量地閱讀前人的作品。僅從這一點而言,余華的確是從川端康成的作品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
我們或許可以從余華本人的講述中去了解他從川端康成那里獲得的究竟是什么?
在川端康成作我導師的五、六年時間里,我學會了如何去表現細部,而且是用一種感受的方式去表現。感受,這非常重要,這樣的方式會使細部異常豐厚。……現在不管我小說的節奏有多快,我都不會忘了細部。
在他看來,最為重要并非是川端康成一貫被世人認定的婉約、唯美、感受的寫作風格,而是更為直接的細節描寫。當余華“學會了如何去表現細部”時,他是從方法論的層面從川端康成的手中獲得文學創作的真諦。正如余華自己所說:“他刻畫細部非常好,但是他是有距離的。你覺得他是用一種目光去注視,而不是用手去撫摸。”首先,他從川端康成的作品中獲得作家必須重視細部描畫的要領。這是一部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品必須做到的,缺乏了細部就無法構建起現實主義的文學大廈。但余華并沒有被現實主義文學的條條框框所束縛,他始終是以心靈的感受去描寫這一切。因此,他所描寫的事物帶上了濃厚的主觀主義色彩,不再是單純地將現實生活的內容呈現在自己的作品中。而這一點恰好是余華從川端康成的創作中獲得的另一種精神力量。
余華絕不是一位對川端康成亦步亦趨的文字堆砌者,他有著屬于自己的對于文學的理解方式。當他逐漸意識到屬于自己的創作更應是先鋒文學的模式之后,我們就能夠在他的作品中感受到唯美、憂郁的情感特質,那些似乎能夠將余華與川端康成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形式化元素逐漸從余華的作品中徹底淡化了出去。但留在他的作品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依舊得到了保留,這就是川端康成重視細節描寫的寫作手法。
我們可以在《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感受到柏油馬路的“起伏不止”,感受到馬路如同海浪的描寫,這幾乎是在其他的文學作品中很好涉及的細節刻畫。而余華在《現實一種》中對于肢解尸體的描寫往往被冠以血腥、殘酷的定位,使得他的細節描寫被人們所遺忘。從本質層面而言,余華是從川端康成的手中繼承了細節描寫的手法,并直接運用到自己的文學創作中,需要注意的是,他早期的作品往往也將川端康成的唯美、憂郁的審美特征凝聚在自己的作品中,使得讀者極易將二者聯系在一起,隨著余華的創作日漸成熟,他最終擺脫了川端康成的束縛,形成了余華式的先鋒風格。
[參考文獻]
[1][法]歐仁·尤奈斯庫.法國作家論文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568.
[2]周東升.余華小說創作風格研究[D].成都:西南交通大學,2003.
[3]余華.我能否相信自己[M].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8:252-253.
[4]余華.說話[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76.